論伯明翰學(xué)派文化觀的邏輯進(jìn)程
時間: 分類:文學(xué)論文 瀏覽次數(shù):
摘要:英國伯明翰學(xué)派是當(dāng)代文化研究領(lǐng)域的重要力量,其文化觀經(jīng)歷了三個顯著的發(fā)展階段:早期學(xué)派意在從文化維度反對階級消亡論,視文化為主體意識的直接表達(dá);中期借由結(jié)構(gòu)主義馬克思主義等理論,強(qiáng)調(diào)文化建構(gòu)于主體意識和社會結(jié)構(gòu)的矛盾沖突之上;20世紀(jì)80年代后在后現(xiàn)代主義等思潮影響下,指認(rèn)文化是主體借助商品消費(fèi)抵抗意識形態(tài)的具體展現(xiàn)。考察伯明翰學(xué)派文化觀的邏輯進(jìn)程及其理論價值和缺陷,可為我們研究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提供重要的參考資源。
關(guān)鍵詞:伯明翰學(xué)派;文化觀;意識;意識形態(tà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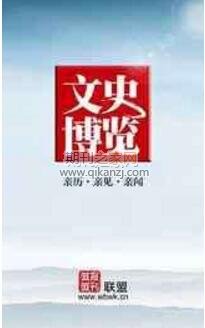
文學(xué)方向評職知識:發(fā)表文學(xué)論文的普刊
《文史博覽》Culture and History Vision(月刊)曾用刊名:湖南文史資料選輯;湖南文史資料;湖南文史,1960年創(chuàng)刊,是湖南省政協(xié)主辦,全省唯一的面向國內(nèi)外公開發(fā)行的省部級學(xué)術(shù)性刊物,湖南省一級期刊。為辦好刊物,我們需要一切致力于理論研究和關(guān)心中國經(jīng)濟(jì)社會發(fā)展的人們的支持和幫助。熱忱歡迎廣大專家、學(xué)者、理論研究人員和實(shí)際工作者踴躍投稿。
興起于20世紀(jì)50年代中后期的伯明翰學(xué)派,以1964年建立于英國伯明翰大學(xué)(UniversityofBirmingham)的當(dāng)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以下簡稱CCCS)為大本營,在馬克思主義傳統(tǒng)內(nèi)從階級、種族、性別等維度深入考察文化問題。學(xué)界普遍認(rèn)為,以伯明翰學(xué)派為代表的英國文化研究是從意識形態(tài)維度研究文化的一項學(xué)術(shù)工程。盡管該說法點(diǎn)明了伯明翰學(xué)派文化觀的突出特征,但這種過于籠統(tǒng)的概括一定程度上既掩蓋了伯明翰文化觀依賴的英國馬克思主義理論變遷語境,也將其文化觀的價值和不足單向化、靜態(tài)化了。
筆者認(rèn)為,我們更應(yīng)當(dāng)關(guān)注伯明翰學(xué)派文化觀不斷變更的聚焦點(diǎn),而非簡單強(qiáng)調(diào)哪一點(diǎn)足以概括其整體特色,正如其核心人物斯圖亞特·霍爾(StuartHall)所說:“文化研究有多重話語;有許多不同的歷史故事。它是一整套的構(gòu)型。”[1]本文試圖將伯明翰學(xué)派的文化觀置于英國馬克思主義發(fā)生的理論背景中,視其為一個“移動的譜系”,考察它在理論和實(shí)踐中的代際變遷和整體面貌,并嘗試分析其意義、價值和不足。
一、文化作為主體意識的再現(xiàn)
20世紀(jì)50年代中后期,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t)、E.P.湯普森(E.P.Thompson)、雷蒙·威廉斯(RaymondWilliams)、斯圖亞特·霍爾等人共同拉開了伯明翰學(xué)派文化研究的大幕。以他們?yōu)楹诵牡脑缙诓骱矊W(xué)派,在英國經(jīng)驗(yàn)主義傳統(tǒng)、美國社會學(xué)“民族志”方法、利維斯主義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下,對文化達(dá)成了基本共識,即將個人經(jīng)驗(yàn)置于優(yōu)先探尋的地位,相信主體具有的自由理性能力,視文化為主體意識的直接展現(xiàn)。該文化觀主要呈現(xiàn)三方面的特色。其一,打破精英文化/大眾文化的二元對立。從文化形式看,F(xiàn).R.利維斯(F.R.Levis)等人通過設(shè)定價值標(biāo)準(zhǔn),將工人階級文化貶低到毫無價值的地步,激起了廣大英國群眾的不滿。在反抗洪流中,霍加特扛起工人階級反擊戰(zhàn)大旗,宣稱“不要從不同藝術(shù)類型(高雅的、中等的、低級的或其他)的先驗(yàn)劃分開始,而應(yīng)從每個時代的起點(diǎn)開始”[2]。
他強(qiáng)調(diào)要從現(xiàn)實(shí)經(jīng)驗(yàn)出發(fā)理解文化。威廉斯則通過“文化”概念發(fā)展史的考察,駁斥了長期以來英國文學(xué)研究者將文化概念狹隘化的做法,指出根本不存在大眾,只有看待大眾的方式,令普通人的文化重新回歸“文化”概念。總之,早期伯明翰學(xué)派普遍堅信,文化不應(yīng)當(dāng)被先驗(yàn)地預(yù)設(shè)價值判斷,它只有形式不同而無地位高低。但與之相悖的是,不少研究者分析具體文化形式時,卻常常重復(fù)利維斯主義,“接受了經(jīng)典文本比當(dāng)代的大眾文化更能深化和拓展人的經(jīng)驗(yàn)的觀點(diǎn)”[3]。例如,霍加特在《文化的用途》(TheUsesofLiteracy,1957)一書中,一邊大力頌揚(yáng)二戰(zhàn)前工人階級文化的價值,一邊卻遺憾甚至憤怒地指責(zé)如今工人階級青年的“棉花糖式”(candyfloss)文化。霍爾在《流行藝術(shù)》(PopularArts,1964)中也指出,青少年雖然能夠自發(fā)地利用流行文化表達(dá)意識,但還是應(yīng)當(dāng)去學(xué)習(xí)“更優(yōu)秀”的文化。種種跡象表明,早期伯明翰學(xué)派文化觀呈現(xiàn)出理論與實(shí)踐的明顯斷裂。
從文化內(nèi)容看,早期伯明翰學(xué)派強(qiáng)調(diào)文化內(nèi)容的瑣碎性、日常性和平凡性,而較少甚至有意避開文化蘊(yùn)含的政治內(nèi)容。這主要源于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早期伯明翰學(xué)派形成于英國快速步入消費(fèi)主義的階段。如果說先前社會財富的巨大鴻溝使工人階級極易擁有明確的政治目標(biāo),那么現(xiàn)在高福利、高消費(fèi)的社會語境則令工人階級沉湎于物質(zhì)生活而在精神上日趨迷茫。其次,該學(xué)派出場于蘇共二十大等重大事件爆發(fā)不久,這使他們急于擺脫蘇聯(lián)馬克思主義那種將文化視為直接經(jīng)濟(jì)產(chǎn)物的教條觀點(diǎn)。再次,利維斯主義對于文化不應(yīng)涉及政治的基本立場也深刻影響了早期研究者。但湯普森不滿霍加特、威廉斯等人將政治與文化分離的做法,高呼文化應(yīng)作為整體性的斗爭方式而不僅僅是生活方式。就實(shí)際情況而言,湯普森倡導(dǎo)的文化立場在當(dāng)時學(xué)派內(nèi)的影響力較為有限。
其二,強(qiáng)調(diào)文化的階級性。早期伯明翰學(xué)派抨擊了之前將工人階級視為靜態(tài)被壓迫實(shí)體的觀點(diǎn),宣稱“工人階級擁有一種強(qiáng)大的自然能力,該能力使他們通過適應(yīng)或同化新的文化形式,使自己想要的東西留存下來”[4]。例如,在《世俗文化》(ProfaneCulture,1972)中,保羅·威利斯(PaulWillis)通過分析嬉皮士(hippie)等文化,肯定了工人階級青年團(tuán)體在文化生產(chǎn)中的強(qiáng)大力量,突出其顛覆資本主義文化的潛在意義。在此前提下,早期伯明翰學(xué)派將建構(gòu)一種新型民主社會主義文化作為旨?xì)w,正如霍加特所說:“把人只培養(yǎng)到掌握這些基本知識所需的水平,那你只是生產(chǎn)了一個能夠受愚弄的社會,不鼓勵人們具有批判意識,不給予人們一種批判性的文化知識。”[5]因此,不論是早期成員積極參與成人教育工作,還是其整體的理論面貌,都展現(xiàn)出努力將資產(chǎn)階級的文化教育機(jī)制“為我所有”,幫助工人階級建立反抗資本主義新型文化的政治訴求。
其三,強(qiáng)調(diào)文化對現(xiàn)實(shí)生活經(jīng)驗(yàn)的回應(yīng)。這種視角一方面來源于直觀經(jīng)驗(yàn)主義方法論,一方面是受到了包括湯普森、約翰·薩維爾(JohnSaville)、拉斐爾·薩繆爾(RaphaelSamuel)等英國早期馬克思主義史學(xué)家“自下而上”歷史觀的影響。他們一改之前“英雄歷史”的書寫方式,運(yùn)用史料力證廣大人民群眾對歷史的推動作用。在此視角下,早期伯明翰學(xué)派文化觀的基本特點(diǎn)便是相信文化是建立在經(jīng)驗(yàn)基礎(chǔ)上的自主性、能動性創(chuàng)造。在《文化的用途》中,霍加特肯定了工人階級創(chuàng)造自己文化的能力,認(rèn)為他們在日常生活中不斷創(chuàng)造著帶有自身特質(zhì)的文化形式。湯普森則在批判經(jīng)濟(jì)決定論的基礎(chǔ)上重點(diǎn)指出:“人們并非僅僅被動‘反映’經(jīng)歷,他們也思考經(jīng)歷,他們的思索會對行為產(chǎn)生影響,思考是人類創(chuàng)造性的一面。”[6]
早期伯明翰學(xué)派肯定了階級主體和階級斗爭的現(xiàn)實(shí)存在,并將文化看作維護(hù)工人階級內(nèi)聚力的重要紐帶。這種文化觀既改變了英國馬克思主義傳統(tǒng)中以克里斯托弗·考德威爾(ChristopherCaudwell)為代表的較機(jī)械地理解經(jīng)濟(jì)與文化關(guān)系的做法,也扭轉(zhuǎn)了彌漫于西方馬克思主義內(nèi)部濃厚的悲觀主義文化觀,奠定了伯明翰學(xué)派的學(xué)術(shù)底色,時至今日仍是其最重要的理論貢獻(xiàn)之一。但同時,早期學(xué)派并沒有看到文化不僅是個人的創(chuàng)造,更是社會結(jié)構(gòu)的產(chǎn)物,因此過于片面地強(qiáng)調(diào)了文化的獨(dú)立性,浪漫化了英國工人階級,以至于使工人階級似乎已經(jīng)成為脫離社會經(jīng)濟(jì)基礎(chǔ)的存在,或者借用伯明翰學(xué)派后起之秀托尼·本尼特(TonyBennet)的話說,這種文化觀可能一直有意無意地在“鼓吹一種大眾主義”[7]62。
同時,現(xiàn)實(shí)經(jīng)驗(yàn)畢竟具有個體性、偶然性和局限性等,過于相信經(jīng)驗(yàn)必然走向“見木不見林”的地步。雖然以上特點(diǎn)勾勒了伯明翰學(xué)派文化觀的基本面貌,但絕不是完全意義上的,比如威利斯在《什么是新聞》(WhatIsNews,1968)中就以發(fā)生在伯明翰大學(xué)的學(xué)生靜坐事件為例,指認(rèn)新聞為了支持統(tǒng)治階級世界觀捏造事件,從而強(qiáng)調(diào)了媒介文化在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顯著作用。威廉斯也明確指出意識形態(tài)對被統(tǒng)治階級的規(guī)訓(xùn)作用:“這種體制雖然會否認(rèn)它對人的控制,但它的確是頑固僵化的。首先,它很隱蔽,很難辨別;其次,正是通過其結(jié)構(gòu)和意識形態(tài),它似乎是要給人們提供一種自由感。”[8]這些零星的觀點(diǎn),已經(jīng)孕育了伯明翰學(xué)派文化觀轉(zhuǎn)變的萌芽。
二、文化作為意識和意識形態(tài)的交鋒
1968年,伯明翰學(xué)派的核心人物霍加特赴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任職,霍爾接替CCCS主任的職位,扛起文化研究大旗。盡管霍爾此前的研究基本采納了早期伯明翰學(xué)派的文化觀,但隨著英國馬克思主義的代際轉(zhuǎn)換,霍爾迅速接受了英國第二代新左派的理論主張,開始帶領(lǐng)伯明翰學(xué)派進(jìn)行范式轉(zhuǎn)向。
三、文化作為對抗意識形態(tài)的主體意識
20世紀(jì)80年代伯明翰學(xué)派作大規(guī)模葛蘭西轉(zhuǎn)向后,新的時代大潮接踵而至。政治領(lǐng)域,撒切爾夫人領(lǐng)導(dǎo)下的保守黨重新執(zhí)政,令英國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策略遭受重創(chuàng);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保守黨通過一系列措施成功扭轉(zhuǎn)了20世紀(jì)70年代的經(jīng)濟(jì)頹勢,使英國經(jīng)濟(jì)步入穩(wěn)定增長軌道;思想領(lǐng)域,后現(xiàn)代主義思潮對英國社會科學(xué)的沖擊與日俱增,這些都推動了伯明翰學(xué)派文化觀的再次轉(zhuǎn)型。
拉克勞、墨菲等人以后現(xiàn)代主義思想為依托,堅信當(dāng)前反對總體性、普遍性的必要性,創(chuàng)建了著名的“后馬克思主義”理論。該理論對阿爾都塞的個體身份理論進(jìn)行了重新闡釋,認(rèn)為主體身份并不如阿爾都塞所說是固定的,而是流動不居的。這樣一來,阿爾都塞的構(gòu)建被統(tǒng)治階級常識的“意識形態(tài)”粉碎了,取而代之的是不同的立場和話語。繼而,馬克思的階級理論也被消解了,多元化的社會斗爭(種族、年齡、性別等)順理成章地取代了馬克思主義作為推動歷史根本力量的階級斗爭。
該理論在20世紀(jì)80年代中期逐步影響到伯明翰學(xué)派的各項研究工作,帶來了兩方面的直接后果:一是開始從理論上相信工人階級文化絕非鐵板一塊,而是充滿了異質(zhì)性,糾正之前過于偏執(zhí)的文化總體性研究理路已經(jīng)刻不容緩;二是拋棄了之前普遍以階級為基本分析框架的文化研究方法。他們相信,既然階級成員可以因時因地自由流動,那么階級身份也不再是其固定身份。也就是說,學(xué)派開始否認(rèn)文化主體的實(shí)在性,代之以文化主體的流動性和破碎性。
在此基礎(chǔ)上,學(xué)派逐步建構(gòu)將文化與意識形態(tài)重新對立的文化觀。這雖然表面上與第一階段相似,但從本質(zhì)看完全不同:首先,這種文化觀沿襲了上一階段對文化的政治介入性的理論成果,突出了文化的政治性內(nèi)涵,認(rèn)為大眾文化是有意與統(tǒng)治階級對抗的一種文化,而不再像早期簡單無視或盲目排斥文化的政治性內(nèi)容。其次,這種文化觀也不再像早期將文化視為工人階級生產(chǎn)的文化產(chǎn)品,而是將大眾文化理解為建立在由統(tǒng)治階級生產(chǎn)的消費(fèi)產(chǎn)品的基礎(chǔ)上,就是說,文化問題由生產(chǎn)領(lǐng)域轉(zhuǎn)向了消費(fèi)領(lǐng)域。
結(jié)語
在伯明翰學(xué)派的發(fā)展歷程中,其文化觀大致經(jīng)歷了將文化視為主體意識的再現(xiàn),到將文化視為主體意識和意識形態(tài)交鋒,再到將文化視為對抗意識形態(tài)的主體意識的三個基本階段。第一階段,伯明翰學(xué)派的文化觀建立于經(jīng)驗(yàn)主義傳統(tǒng)之上,以對英國工人階級日常文化經(jīng)驗(yàn)的深度分析作為立論基點(diǎn),突出了工人階級主體能動性的力量,將文化視為不同階級獲得身份認(rèn)同的基本渠道。
第二階段,伯明翰學(xué)派與馬克思主義(尤其是結(jié)構(gòu)主義馬克思主義)有了更為緊密的聯(lián)系。學(xué)者在各自的研究中實(shí)踐著馬克思所說的“統(tǒng)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個時代都是占統(tǒng)治地位的思想”[22]的重要論述。他們指出被統(tǒng)治階級的文化雖然以統(tǒng)治階級意識形態(tài)為底色,卻依舊帶有主體自發(fā)的創(chuàng)造性,而這種文化創(chuàng)造雖然是為了抵抗統(tǒng)治階級的意識形態(tài),但最終被統(tǒng)治階級意識形態(tài)“收編”。至第三階段,伯明翰學(xué)派的文化觀已經(jīng)流露出鮮明的后現(xiàn)代主義色彩。它以文化消費(fèi)論替換了之前的文化生產(chǎn)論,意在指認(rèn)文化的流動性、差異性和無序性,傾向于分析大眾如何通過改造資本主義的消費(fèi)品來表達(dá)抵抗情緒,并相信此種情緒不僅“永遠(yuǎn)不會成為宰制力量的一部分”[18]53,而且也不斷推動著發(fā)達(dá)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化進(jìn)程。總體看,伯明翰學(xué)派文化觀的變遷反映了學(xué)派對如何理解及運(yùn)用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不斷探索的過程。
針對斯大林主義那種以“經(jīng)濟(jì)決定論”理解經(jīng)濟(jì)與文化關(guān)系的做法,他們從變化了的資本主義社會現(xiàn)實(shí)出發(fā),指認(rèn)文化在消費(fèi)主義社會絕非只是精神性的活動,而是社會的物質(zhì)性力量。從威廉斯將文化視作整體性的生活方式,到霍爾認(rèn)為文化是以“社會群體在其中發(fā)展出自己獨(dú)特的生活模式,并且把他們的社會和物質(zhì)生活經(jīng)驗(yàn)以一定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14]78,再到菲斯克定義文化是大眾的反抗意識“在社會中的生成與傳播”[14]2,可以看到,文化在伯明翰學(xué)派的理解和運(yùn)用中從來都不是被“基礎(chǔ)”單向度決定的“上層建筑”,而是與社會其他構(gòu)成要素間有著深層次的互動。
在此視域下,學(xué)派一方面深刻闡發(fā)了當(dāng)代資本主義如何通過意識形態(tài)維護(hù)和再生產(chǎn)統(tǒng)治秩序,不僅為當(dāng)代資本主義一直沒有爆發(fā)大規(guī)模工人革命給出了比較合理的解釋,也指明了當(dāng)代語境中不同階級間意識形態(tài)領(lǐng)導(dǎo)權(quán)斗爭的緊迫性和嚴(yán)峻性;另一方面則有力扭轉(zhuǎn)了之前西方馬克思主義一直彌漫的精英主義文化觀。雖然學(xué)派在不同階段對主體和結(jié)構(gòu)間的關(guān)系看法不同,但他們始終相信,“在一個社會的占統(tǒng)治地位的思想內(nèi)部也不只有一種趨勢在起作用。那些并不處在權(quán)力頂峰的群體和階級,仍然會在他們的文化當(dāng)中尋找表達(dá)和認(rèn)識他們的從屬地位和經(jīng)驗(yàn)的方法”[23]。
但是,伯明翰學(xué)派文化觀存在的重大不足也值得深思。盡管學(xué)派理論上承認(rèn)經(jīng)濟(jì)對文化的形成起著決定性作用,但縱觀各個階段的研究實(shí)踐,都甚少談及經(jīng)濟(jì)和文化間的關(guān)系,而是始終局限于探究上層建筑各要素間相互作用的藩籬之內(nèi),這使得他們無法從根本上分析文化現(xiàn)象不平等的根源,落入了文化決定論的窠臼。但值得注意的是,隨著學(xué)派內(nèi)外質(zhì)疑聲的不斷擴(kuò)大,當(dāng)代伯明翰學(xué)派的繼承者們已經(jīng)開始認(rèn)真反思研究路徑的重大不足,一定程度上使文化研究慢慢展露出回歸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的整體趨勢。
最新期刊論文咨詢
- 如何提高學(xué)生道德人格素養(yǎng)
2025-07-11瀏覽量:254
- 包裝設(shè)計理念形成整體化教學(xué)的方法
2025-07-10瀏覽量:399
- 包裝工程師發(fā)表論文在哪發(fā)
2025-07-10瀏覽量:294
- 交互設(shè)計提升理財類APP可用性研究
2025-07-09瀏覽量:335
- 農(nóng)業(yè)類核心科技期刊微信公眾號的運(yùn)營現(xiàn)狀及發(fā)展對策
2025-07-03瀏覽量:365
- 都勻毛尖茶旅游食品開發(fā)條件研究
2025-07-03瀏覽量:401
- 社會經(jīng)濟(jì)地位與老年健康不平等基于生命歷程視角的研究
2024-11-23瀏覽量:401
- 廣西仫佬族剪紙藝術(shù)題材演變及數(shù)字化展示設(shè)計研究
2024-11-23瀏覽量:551
- AI創(chuàng)作物可版權(quán)性及保護(hù)路徑再探討
2024-11-22瀏覽量:338
- 現(xiàn)代(后現(xiàn)代)美術(shù)理論與媚俗藝術(shù)
2024-11-22瀏覽量:269
中文核心期刊推薦
-

-
統(tǒng)計與決策
級別:北大核心,CSSCI,AMI擴(kuò)展
ISSN:1002-6487
刊期:進(jìn)入查看
格式:咨詢顧問
-

-
統(tǒng)計研究
級別:北大核心,JST,CSSCI,WJCI,AMI權(quán)威
ISSN:1002-4565
刊期:進(jìn)入查看
格式:咨詢顧問
-

-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huán)境
級別:北大核心,JST,CSCD,CSSCI,WJCI
ISSN:1002-2104
刊期:進(jìn)入查看
格式:咨詢顧問
-

-
中國法學(xué)雜志
級別:北大核心,CSSCI,AMI權(quán)威,社科基金資助期刊,
ISSN:1003-1707
刊期:進(jìn)入查看
格式:咨詢顧問
SCI核心期刊推薦
-

-
Scientific Reports
數(shù)據(jù)庫:SCI
ISSN:2045-2322
刊期:進(jìn)入查看
格式:咨詢顧問
-

-
ACTA RADIOLOGICA
數(shù)據(jù)庫:SCI
ISSN:0284-1851
刊期:進(jìn)入查看
格式:咨詢顧問
-

-
Materials Today Communications
數(shù)據(jù)庫:SCI
ISSN:2352-4928
刊期:進(jìn)入查看
格式:咨詢顧問
-

-
APPLIED SURFACE SCIENCE
數(shù)據(jù)庫:SCI
ISSN:0169-4332
刊期:進(jìn)入查看
格式:咨詢顧問
-

-
PLANT JOURNAL
數(shù)據(jù)庫:SCI
ISSN:0960-7412
刊期:進(jìn)入查看
格式:咨詢顧問
熱門學(xué)科SCI期刊目錄
熱門核心期刊目錄
期刊與論文專題
論文范文文獻(xiàn)合集
- 多媒體信息技術(shù)在化學(xué)教學(xué)應(yīng)用的論文范文2篇
- 高中化學(xué)實(shí)驗(yàn)教學(xué)的論文文獻(xiàn)2篇
- 初中化學(xué)教學(xué)論文論文范文3篇
- 輸電線路防雷的論文范文2篇
- 輸電線路除冰技術(shù)論文參考文獻(xiàn)2篇
- 文化遺產(chǎn)開發(fā)論文文獻(xiàn)2篇
- 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有關(guān)的論文文獻(xiàn)5篇
- 傳感器課堂教學(xué)論文范文2篇
- 初中地理教學(xué)3篇論文選題及范文參考
- 無機(jī)化學(xué)教學(xué)論文范文2篇
- 計算機(jī)技術(shù)對現(xiàn)代化作用的研究論文范文2篇
- 塑料食品包裝污染及危害論文范文2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