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書籍裝幀藝術的百年流變
時間: 分類:文學論文 瀏覽次數:
[摘要]當代中國書籍裝幀藝術的發展,經歷了幾次重大的歷史性轉折和流變。一是百年文化變革對書籍裝幀藝術的影響;二是科技進步對書籍裝幀藝術的影響。從辯證的角度看待中國裝幀藝術的發展歷程,可以使我們進一步了解中國現當代文化發展映射下裝幀藝術的繁榮與輝煌,使我們在新的歷史時期客觀地認識書籍裝幀藝術生存與發展的問題,從而把握現在,面對未來。探討文化與科技對書籍裝幀藝術的主導作用,并從歷史的角度出發,進一步探索和發現書籍裝幀藝術的歷史意義和當代價值。
[關鍵詞]文化變革;書籍裝幀藝術;信息技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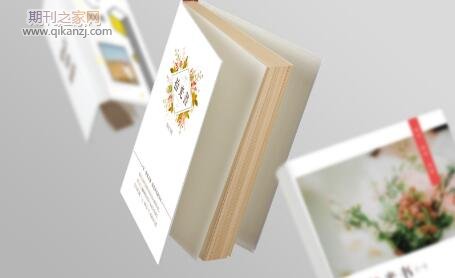
中國書籍裝幀藝術的發生、發展已經演繹了幾千年。書籍作為文化載體,它所呈現出來的藝術形式與各個歷史時期的文化現象密切相關,同時也折射出了不同時期的歷史、文化精髓。因此,在梳理中國現當代書籍裝幀藝術發展史的時候,應以求實的態度站在歷史的角度去探討裝幀藝術的發展規律及走向。在具體思路上,一是縱向上從歷史文化的角度觀其流變;二是橫向上從科技發展的角度把握當下。
一、從兩次文化變革看書籍裝幀藝術
兩次文化變革指的是20世紀民國初期的新文化運動和20世紀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新文化運動是從1915年開始的中國近現代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和啟蒙運動,它動搖了封建思想的統治地位,弘揚民主和科學,為藝術發展提供了新參考和新方向;“文化大革命”是從1966年開始的通過文化上的一場革命而掀起的一場全國性運動,以代表無產階級領導的文學藝術來反對和批判資產階級傳統文化思想,這就意味著這場文化革命本身就失去了以文化為核心促進文化領域健康發展的核心動力。
(一)新文化運動與民國時期裝幀藝術
1.新文化運動的積極意義
新文化運動提倡民主與科學,反對專制與迷信;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新文化運動崇尚科學,并且鼓勵大眾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科學思維方式。部分學者把新文化運動比作是“中國的文藝復興”。由新興民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學生組成的陣營,表明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態度,反對中國傳統文藝作品,提倡新文學,推廣白話文,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和藝術,造就并影響了大批的文學藝術社團。新文化運動是思想和文學藝術的一次革新,在西方文學藝術的影響下,文學藝術從封建枷鎖中解放出來,呈現出多元化的思想傾向和表現形態。新文化運動傳播新思想和新文化,同時也賦予了書籍新的使命和更大的發展空間。
書刊、雜志等出版物成為推動新文化運動的傳播手段。書籍裝幀藝術受新思想、新觀念的影響,呈現出繁榮景象,與當時的文化現象遙相呼應。在出版物的內容上是多種多樣的,有右翼的,也有左翼的。
2.新文化運動影響下的書籍裝幀藝術
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書籍裝幀發展是舊時期裝幀藝術向現代裝幀藝術發展演變的歷史轉折點,也是重要的過渡時期。這一時期的各界領袖人物逐漸開始重視書籍裝幀藝術,全新的書籍裝幀設計形式成為了一種流行風潮,隨著商業活動日漸熱絡,圖書市場的需求量猛增,出版業和印刷行業也迅速崛起,技術手段不斷更新。
陳瑞林在《中國現代藝術設計史》中介紹道:1913年商務印書館引進增置自動鑄造字爐;1915年又從歐洲購買添置膠版印刷機;1919年實現了上等宣紙15色套印……。多方因素使得書籍裝幀藝術在設計上有了很大的進步,印刷質量更加精良。
新文化運動之前書籍裝幀藝術的主要特色體現在裝幀形式上,而新文化運動時期更注重書籍設計,其主要特點體現為兩個方面:一是書籍設計的風格更多元化。處于新舊交替、承前啟后的新文化運動時期,當時的作家、藝術家既受傳統思想文化的影響又接受著西方思潮的沖擊,他們所受的教育有進步的,有封建或者西化的,藝術上出現了“中西合璧”“新舊交錯”的面貌。這一時期書籍裝幀界涌現出了大批優秀的人才,他們設計風格多樣。因此民國時期的書籍裝幀藝術形成了“百花齊放”的繁榮景象。
魯迅先生十分重視書籍裝幀設計和印刷,并且受西化的影響,他的設計思想注重傳統文化思想,同時融入西方現代文化元素。在制作工藝上也提出了自身的不足:“在中國,校對、制圖都不能令人滿意。例如圖畫,將中國版和日本版,日本版和英德諸國版一比較,便立刻知道一國不如一國。三色版,中國總算能做了,也只三兩家……”[1]
274二是書籍的插圖、版式設計突破傳統思想,融入外來文化。圖書的插圖設計也被當時的出版界和書籍裝幀界所重視,以魯迅為首的一批優秀裝幀藝術家開始重視插圖和書籍的版式設計,在裝幀藝術形式上開始融入外來書籍藝術形式及藝術思潮。
這一時期的書籍設計不再像以往那樣多以文字為主,而是通過選用與內容更貼切的字體設計和圖形、圖像等設計元素來詮釋內容。有的根據內容需要,嚴肅大方,有新鮮感,如《共產黨》月刊。有的活潑、強烈,用明確的形象來表現內容,如1920年5月1日的勞動節紀念號《新青年》,畫面以羅丹的勞工神圣紀念碑為主體,畫面主體紅色,對比強烈,構圖簡潔,既熱烈,又飽含革命氣氛。
(二)“文化大革命”與“文革”時期書籍裝幀藝術
1966年開始至1976年結束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教育界、藝術界、新聞出版等文化領域都受到了沖擊。出版界作為被“徹底批判”的“五界”之一,最早受到沖擊,沖擊范圍廣、程度深,在運動中遭到了極大的摧殘和破壞。
1.“文革”時期的文化導向
梁漱溟先生在《中國文化要義》中指出:“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意在指示人們,文化是極其實在的東西。文化之本義,應在經濟、政治,乃至一切無所不包”[2]6。“文革”時期的文化效應只重視文化的政治屬性,強調文化定位以政治為本,文化內容的使命和解釋模式都與社會革命相聯系。
因此在特殊時期政治思潮的影響下,形成了全盤否定傳統和現代的極端的、激進的文化立場。既排斥傳統文化又否定西方文化。觀察建國后至“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文代會,從中不難發現當時對于西方的文藝政策基本上是持批評,甚至是排斥態度的。與此同時,中國傳統文化中無論其所謂精髓還是糟粕,也都同時被打上了“封建的”“反面的”的烙印。
2.文藝政策對藝術發展的限制和扭曲
“文革”時期,在人們的思想觀念中,文學藝術是為工農兵服務的,這一歷史時期藝術的政治化傾向尤其明顯。只有符合意識形態和政治任務的文藝作品才被允許傳播和接受,不同聲音和形式的文藝創作被徹底、無情的批判和抹殺。此時的文藝作品體現出“革命”年代的特色,人物形象都是“高、大、全”。藝術表現形式單一化、模式化、內容樣板化。
今天看來,“一花獨放”的樣板戲作為一個歷史時期的經典,雖然藝術形式被模式化,但其藝術形式上的推陳出新是不可一概否定的,“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在當時的京劇和芭蕾舞劇中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體現。但是,以服務政治為核心價值的藝術,必然會導致藝術上的畸形發展,“一花獨放”完全違背了藝術發展的客觀規律。
而這一時期的藝術家必須站在“階級革命”的思想立場上,把文學藝術創作與黨和政府的中心工作結合起來,將藝術作為意識形態的宣傳工具,最大限度地為政治服務。從藝術作品來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藝政策已被消解。本土藝術已經剝離了其本質上的發展規律而成為服務政治的工具。
3.“文革”時期的書籍裝幀藝術
“文革”時期阻礙書籍裝幀藝術發展的消極因素體現為以下幾個方面:出版方面,全國出版機構被大量合并和撤銷,從業人員銳減。至1970年末,全國出版社數量由原來的87家減少為53家,減少了近半數;編輯人員由原來的4570人減少為1355人,相當于“文革”前編輯人數的29.6%,在文化中心首都北京從事出版工作的編輯人員僅63人①。
圖書方面,全國圖書出版數量斷崖式下降。1966年全國圖書出版的種數較1965年減少了近一半,1967年猛降到2925種。至1970年末,除了馬恩列斯著作、毛主席著作外,出版種數僅為2977種②。邱陵在《書籍裝幀藝術史》裝幀藝術的低谷期部分提及:“1966年的出書種數大約只及1956年的10%,十年中出書平均每年也只及1956年的27.5%。
這十年中的出版物,其內容的顛倒是非就不用說了,即使只從印刷、裝幀上看,也基本上是粗制濫造,重復浪費極其嚴重。文化專制主義導致的后果是各地書店的書架上一片‘紅海洋’,除馬、恩、列、斯著作,毛澤東著作外,絕大多數出版物實質上都是借用革命的辭藻和革命的色彩,在鼓吹和煽動反革命的暴力活動。這種形式下,裝幀設計處于停滯狀態。因為在那種形式下,設計者和生產者都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自然不可能有大膽的創造”[3]126。
“文革”時期大量的文學作品受到沖擊,書籍出版數量和種類驟減,為政治服務的特殊書籍被大量刊印,大多數書籍都是政治宣傳的工具。這一時期的出版行業和相關的從業人員受到嚴重打擊,數量較“文革”前大幅度減少,書籍裝幀藝術趨于停滯狀態。在“文革”時期,書籍裝幀藝術作為一種藝術表現形式,其自身價值已不復存在。
受當時政治形勢的影響,書籍裝幀在藝術上并不具備上升發展空間。這一時期從小說到官方刊物,每一類別的刊物都在題材和表現形式上雷同,書籍封面主要是“高、大、全”的人物形象,藝術形式與審美追求被忽略。思想的禁錮與束縛,使書籍設計遠離藝術規律和藝術本質,形成一種無序狀態。
書籍成為社會革命傳播的工具和武器,并成為書籍裝幀藝術的價值判斷的主要依據。因此,這一時期的書籍裝幀在藝術發展上是有阻滯的;裝幀藝術的發展空間是狹隘的;藝術形式是單調而一統的;傳統藝術的傳承出現了斷代。
二、從科技進步看書籍裝幀藝術的未來走向
科學技術解放了生產力,科學技術也同樣解構了生產力,工業革命使人們從農耕文明的體力勞動中解脫出來,從而進入到人類文明的新的起點。科技的進步促進人類文明的飛速發展,原有的、落后的生產生活方式不斷地被取締。現代生活中,手工產品越來越少,替代產品越來越多;自行車越來越少,汽車越來越多;電視的觀眾越來越少,手機的讀者越來越多;現金支付越來越少,網上支付越來越多……。
我們所處的時代正在發生著科學技術的巨變,科學技術的高度發達像一把雙刃劍,對于傳統文化領域來說,要么被催生,要么被顛覆。無論我們是否做好了心理準備,這場巨變自互聯網誕生之日起就已經開始了。
(一)科技發展與書籍裝幀藝術的繁榮
1978—2008年改革開放的30年,中國不但建立了市場經濟制度,快速躋身經濟全球化的大潮中,在政治和文化等領域,也積極推進了改革開放的步伐,使得中國的文化、藝術需求激增,文化產業快速發展,其中書籍裝幀行業通過機構組織、經濟政策、科學技術等各種形式快速復原并蓬勃發展。
1.印刷技術的進步和印裝質量的提升
印刷技術的每一次進步,都給書籍裝幀和發行帶來巨大的影響,印刷技術從鉛印印刷發展到今天的數字印刷,在技術和設備上不斷地創新、改造,直接推動了書籍裝幀藝術水平的快速提升。20世紀80年代以前主要以鉛印為主,膠印的印刷方式已經出現但是還沒有普及,傳統的鉛字排版,周期長、形式單一,圖片顏色和細節表現力有限,再加上印刷材料和工藝的單調,無法滿足讀者對書籍功能與審美的多重需求。
80年代初期,北京大學王選教授帶領團隊成功研發出了中文激光照排系統,極大地提高了排版的周期時間和印刷質量,是印前排版領域一次突破性的革命。同時期,膠印印刷的發展也已經形成規模。與鉛印印刷相比,膠印印刷的效果有了極大的提升,印刷的工藝流程短,色彩還原度高,裝幀設計作品更加精良。
思想的解禁和開放同時也極大地促進出版行業的復蘇,“1984年全國圖書出版近三萬種,比1978年增加2倍,比1966年增長4倍多”[4]86-88。1992年王選教授成功研發了世界首套中文彩色照排系統,90年代中后期桌面出版系統,電腦數字分色技術逐漸普及,中國進入了數字化排版、設計、印刷、高速裝訂的裝幀蓬勃發展時期。高新技術的應用使印刷質量大大提高,印前技術從模擬技術走向數字化。這一時期可以被稱為中國的第二次印刷技術革命時期。改革開放的30年是書籍裝幀藝術趨向成熟的重要時期。書籍裝幀藝術呈現的繁榮景象與政治、經濟、裝幀工作者和印刷技術等息息相關。
2.紙張質量和裝訂技術的整體發展
紙張是文化和信息得以傳承的重要載體。書籍紙張的選用與諸多因素相關,如:印刷方式和印刷工藝、書籍類別和內容以及大眾的審美對書籍的需求等。改革開放以后,圖書出版領域在紙張上的質量和類型上也發生了突飛猛進的變化。這一時期除了傳統工藝所常使用的銅版紙、新聞紙、凸版紙、膠版紙外,還出現了各種類型的進口銅版紙、特種紙等。同時,對制版印刷設備的引進、改造、升級使國內裝幀藝術形式得到了長足的發展。裝訂是書籍印刷制作的過程中用時最長、手工作業量最大的環節。現如今書籍裝訂已經是機械自動化的流水線操作。裝訂工序和技術手段正向數字化、自動化、科技化的國際先進行列邁進。
(二)信息時代裝幀藝術面臨的問題
1.互聯網時代對傳統行業的沖擊和顛覆
國家圖書館研究院根據2018年4月18日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發布的《第十五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成果發布》內容做出以下總結:“2017年成年國民綜合閱讀率為80.3%,較2016年上升0.4個百分點;數字化閱讀方式接觸率為73.0%,較2016年上升4.8個百分點;圖書閱讀率為59.1%,較2016年上升0.3個百分點。超過半數成年國民傾向于數字化閱讀方式,其中49周歲以下中青年群體是數字化閱讀行為的主要人群。
有聲閱讀成為國民閱讀新的增長點,成年國民的聽書率為22.8%,移動有聲APP平臺成為聽書的主流選擇。”[5]3-38由此可見,人們的閱讀方式已經從傳統的紙質書籍慢慢地轉變為更多元化的電子媒介,紙質書籍的讀者年齡也逐步老齡化,紙質書籍應做好充分的準備,以紙質書為載體的書籍裝幀藝術在新時期將面臨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戰。
2.人工智能與裝幀藝術群體的競爭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認為:“人工智能就是研究如何使計算機去做過去只有人才能做的智能工作。”也就是說人工智能主要任務是替代人類的一部分智力工作。從書籍裝幀藝術的未來發展來看,人工智能能夠完成之前需要人力勞動完成的調研、策劃,生成有針對性的書籍設計方案。但人工智能始終是工具,可以利用其強大的運算分析能力在需要精準性、耐久性的工作中極大提高效率,但短時間取代不了人類獨有的情感表達、審美能力和創造能力。
這些無法用精確的數據來衡量,人工智能還無法處理復雜的審美感知活動。人工智能是一種手段,輔助設計師對書籍設計的要素圖形、文字、色彩進行全面掌控和個性化調整。在可預見的未來社會生活中,人工智能的出現雖然減輕了書籍裝幀工作者的腦力和體力付出,但同時在技術和技能方面也替代了多數職業設計師和專業設計人員的就業崗位,專業技術人員面臨著轉行和失業的可能性。而人工智能領域的高速發展,迫使我們在宏觀上放棄原有的、狹隘的、單一的知識結構與行為模式,從傳統觀念中解脫出來,對信息時代人機分工進行再認識。
結語
從文化的角度透視裝幀藝術,我們發現經歷了20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和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的裝幀藝術,具有以下特點:
一是兩場文化運動都是以反傳統文化為前提的,不同的是新文化運動強調引進西方文化并削弱或取締傳統文化中消極的、不符合時代發展潮流的因素,比如八股文在當時就受到了強烈的抵制,白話文替代了文言文等;而“文化大革命”在抵制傳統文化的同時也排斥和否定西方文化思想,是出于政治的需要,而不是文化需要,“文革”時期對傳統文化中封建的思想觀念予以批判,同時對西方文化包括當時的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意識形態領域的抵制和批判,批判對象統稱為封資修。
二是兩次文化運動在針對傳統文化和外來文化的態度上是有差異的,一個在文化上主張消解傳統,全盤西化;一個在文化上力圖否定傳統,閉關自守。三是就裝幀藝術而言,新文化運動對于裝幀藝術的發展具有一定的積極推動作用,而“文化大革命”由于最終轉變為一場政治運動,最終導致那一歷史時期的裝幀藝術趨于停滯狀態。
從科技的角度看待裝幀藝術,我們在經歷了改革開放后的科技蓬勃發展時期,書籍的出版印刷質量得到了跨越式的發展,近年來已經達到國際發達國家的水平,政治經濟的良好環境使裝幀藝術得到了空前的繁榮。然而,書籍裝幀藝術作為一種藝術形態受到來自互聯網和人工智能的沖擊,裝幀作為一種藝術形式或形態,是以書籍為載體的,而書籍是以商品形態出現在社會生活當中的,商品受供求關系的影響和制約,人們生活習慣和閱讀習慣的改變直接影響到書籍的生存空間,進而決定書籍裝幀藝術是否能夠繼續存在。
現當代書籍裝幀藝術經歷了百年來兩次文化革命的沖擊和兩次科技發展的巨變,書籍裝幀藝術一方面呈現出蓬勃發展的繁榮景象,另一方面也受信息技術的影響而面臨著再次抉擇。也許有一天,裝幀藝術將完成它的歷史使命,紙質圖書將被電子書所替代,裝幀藝術可能成為歷史,可能融合、演變成電子書籍設計、信息設計或產品設計等諸多形式,但是裝幀藝術的歷史價值是不可磨滅的,裝幀藝術作為中國傳統文化藝術的一個組成部分,在歷史的長河里仍顯現著它特有的審美價值和時代風范。
書籍方向論文范文閱讀:高職院校圖書館英語書籍管理系統
摘要:文章試圖從英語教學內容入手,根據教學需求和讀者需求,探索改進圖書館英語圖書的管理系統提供方法。使圖書館改變傳統的圖書管理模式,積極主動地為讀者提供他們需要的和老師需要的教學資源,優化圖書館的服務功能,跟上信息時代發展的步伐,將圖書館管理理論與實踐結合,成為學院教學科研的堅實后盾。
最新期刊論文咨詢
- 如何提高學生道德人格素養
2025-07-11瀏覽量:254
- 包裝設計理念形成整體化教學的方法
2025-07-10瀏覽量:399
- 包裝工程師發表論文在哪發
2025-07-10瀏覽量:294
- 交互設計提升理財類APP可用性研究
2025-07-09瀏覽量:335
- 農業類核心科技期刊微信公眾號的運營現狀及發展對策
2025-07-03瀏覽量:365
- 都勻毛尖茶旅游食品開發條件研究
2025-07-03瀏覽量:401
- 社會經濟地位與老年健康不平等基于生命歷程視角的研究
2024-11-23瀏覽量:401
- 廣西仫佬族剪紙藝術題材演變及數字化展示設計研究
2024-11-23瀏覽量:551
- AI創作物可版權性及保護路徑再探討
2024-11-22瀏覽量:338
- 現代(后現代)美術理論與媚俗藝術
2024-11-22瀏覽量:269
中文核心期刊推薦
-

-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級別:北大核心,JST,CSCD,CSSCI,WJCI
ISSN:1002-2104
刊期:進入查看
格式:咨詢顧問
SCI核心期刊推薦
-

-
Scientific Reports
數據庫:SCI
ISSN:2045-2322
刊期:進入查看
格式:咨詢顧問
-

-
ACTA RADIOLOGICA
數據庫:SCI
ISSN:0284-1851
刊期:進入查看
格式:咨詢顧問
-

-
Materials Today Communications
數據庫:SCI
ISSN:2352-4928
刊期:進入查看
格式:咨詢顧問
-

-
APPLIED SURFACE SCIENCE
數據庫:SCI
ISSN:0169-4332
刊期:進入查看
格式:咨詢顧問
-

-
PLANT JOURNAL
數據庫:SCI
ISSN:0960-7412
刊期:進入查看
格式:咨詢顧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