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沉浮與重生
時間: 分類:文學論文 瀏覽次數(shù):
中國何以歷經千年(苦難)而屹立不倒?個中原因當然很多,這也是一個見仁見智的話題,但宗法禮制、語言文字、天道信仰等等方面的統(tǒng)一與傳承,大概是各家在理解“何為中國”時都共同認可的重要因素,而儒家思想在其中就起到了文化骨架的決定性作用。因此,理解中國,首先就需要理解儒家。系統(tǒng)反思儒家的歷史功過已有數(shù)個世紀之久,甚至從儒家誕生之日起,對儒家的考較就已經開始,不絕如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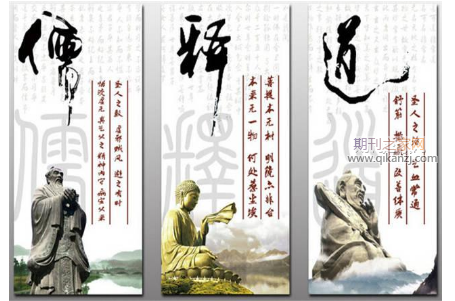
而到了天下危亡之時,比如明末清初以及清末民初,儒家的是非功過更成為人們觀察現(xiàn)實、反思傳統(tǒng)、展望未來的一個重要參照系,相關文獻可謂塞屋充棟。近代不少著名學者都有“原儒”之作,直接考鏡儒家的起源、發(fā)展與流變,已取得豐碩的成果。
梁啟超晚年正處在儒家生存狀態(tài)最為黑暗的時期,但他勇敢站出來為儒家思想辯護,認為“研究儒家哲學,就是研究中國文化”,其理由在于:誠然儒家以外,還有其他各家。儒家哲學,不算中國文化全體;但是若把儒家抽出去,中國文化,恐怕沒有多少東西了。中國民族之所以存在,因為中國文化存在。而中國文化,離不了儒家。如果要專打孔家店,要把線裝書拋在茅坑里三千年,除非認過去現(xiàn)在的中國人完全沒有受過文化的洗禮。
儒家論文范例:儒家教育思想對中學語文教學有何重要作用
這話我們肯甘心嗎?①梁啟超雖然曾師從儒家最后一個圣人康有為,但他本人并不是一個只認信儒家的學者,他對墨家和法家亦不乏同情甚至贊賞,后世學術史也沒有把梁啟超看成是現(xiàn)代新儒家的一員。梁任公的思想也許談不上有多高的“原創(chuàng)性”,但比那些被熱血沖昏頭腦的信徒和自封的思想家遠為廣博和清醒,因而他能夠在充分批判儒家局限的前提下,深刻認識到儒家之于中國文化的根本意義,殊為難得,至少在這一點上,他比西化派和本土派都顯得更有見識。
在他看來,無論怎樣好的學說,經過若干時代以后,總會變質,攙雜許多凝滯腐敗的成分在里頭。譬諸人身血管變成硬化,漸漸與健康有妨礙。因此,須有些大黃芒硝一類瞑眩之藥瀉他一瀉。①儒家當然是很好的學說,這一點乃是給儒家并進而給整個中國古代文化定性的根本前提。儒家是中國文化的主體,更是中國精神的支柱,事實與歷史俱在,本來無需討論,但許許多多不肖子孫把后世甚至自己的無能(或錯誤對待儒家)歸諉在祖先身上,讓滋養(yǎng)中國數(shù)千年的儒家來承擔近代突然到來的重大災難之罪責——這已經不是梁啟超所說的“甘心不甘心”的事情,而是我輩“虧心不虧心”的大節(jié)問題!
不可否認,儒家思想后來多多少少有些“變質”,在一定程度上走向了體系化、制度化(科層化)、結晶化、利祿化、內化(道德化)、胡化、玄學化、空心化和單極化,也就是走向了固化和僵化,但若無儒家思想數(shù)千年的貢獻以及數(shù)以萬計“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的儒生,且不說中國會“萬古長如夜”②或“萬世如聾聵”③,至少遠遠無法成就“中國”這個美好而偉大的名稱。
當然,九流十家的其他學派貢獻亦甚巨,正是先秦各家各派的相互砥礪,才鑄就了中華文明穩(wěn)固的基石。我們之所以更加看重儒家的歷史意義,就在于“儒家”早在戰(zhàn)國末年就已經不是一個封閉的體系,而是吸納了先秦各家學說之精華,比如荀子這位儒學大師就不是“純儒”——唐宋以來的心性儒學對荀子的這種批判其實恰好表明他被嚴重低估了,因為荀子身上體現(xiàn)出來的駁雜不純(吸收了稷下的道家、法家和墨家的思想),正絕佳地展示了儒家的開放和包容。我們現(xiàn)在習慣于談論“原始儒家”,這其實是一個很難兌現(xiàn)的思想考古計劃。這個無法成立的概念雖然有一點點思想史劃分的意義,可以把先秦儒家與宋明新儒家以及現(xiàn)代新儒家區(qū)分開來,但這種“泥古”和“追遠”尤其“求純”(以及所謂“原生性”)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種自我固化、窄化和僵化的狹隘之舉。
在中國歷史上,道家和佛學的影響當然不可小覷,比如魏晉風流主要是“新道家”之功,而中國文化在唐宋時期能夠有堪稱巔峰的表現(xiàn),佛學同樣功不可沒。但正如我們對先秦儒家的定位一樣,任何時代的“儒家”,(本來)都不是單一的“家法”概念,而是在更大范圍內表達中國文化的精神氣質——可惜今天很多儒生畫地為牢而不知自家的偉大遠不在“一家”而已,所爭的“意氣”其實太小家子氣。我們絲毫沒有夸耀儒家的意思(儒家已有豐功偉績,不需要誰去“封神”或“頌圣”),而是說儒家從一開始就在不斷吸收和兼并其他學派的思想,有如滾雪球,看上去是“一家獨大”,實際上已經集中國幾乎所有流派的思想于一身。“儒家”只是一個方便的名號而已,知我罪我,都在這里了,因為它早已不是某個學派的專利。
就算在先秦儒墨并稱顯學的時期,雙方的碰撞和相互影響也有跡可循,比如儒家的大同理想很難說沒有受到墨家的直接刺激。西漢可謂去古未遠,但嚴格說來,董仲舒的儒家立場其實已經很不“純潔”了,他接過公羊學的路數(shù)而把先秦不被特別看好的陰陽家和道家思想納入自己的體系中(道家思想固然重要,甚至可能是儒家的老師,但在先秦傳播不廣)。而宋儒尤其北宋五子中的周敦頤和張載,以無極、太極、陰陽、五行等本屬道家和陰陽家的概念來建立完備的儒家形而上學體系,亦是儒家兼收并蓄的明證。無論后世如何看待儒家的功過,都無法否認這樣的事實:儒家乃是中國文化的主流、主干或主心骨。
我們完全無法想象,離開了儒家經典,中國還如何可能是中國。而堯、舜、文王、周公、孔、孟、二程、朱熹、王陽明等人與其說是“儒家”的圣賢,不如說是中國人的驕傲,他們乃是中華文明的“作者”和傳承者。即便這些圣人(尤其晚出的儒家學者)并非沒有可以批評的地方,但也絲毫無損于他們的偉大。就我們的主旨來說,對于儒家乃至整個中國傳統(tǒng)文化,“愛而知其惡”才是正道——而這種態(tài)度本身就是儒家的教導。我們現(xiàn)今急需的惕勵自省,不是只看到儒家的“不是”,而是要通過客觀清醒的分析找到自己的現(xiàn)實定位,以史為鑒,勾畫未來。任何一種思想在初期階段都顯得較為零散,后來會借助某種理論加以系統(tǒng)化,以利于自身的穩(wěn)定和推廣,但也不可避免會因為穩(wěn)定的形式而逐漸形式化和僵化。
因此,一般而言,僵化不完全是儒家的責任(當然脫不了干系),而是整個中國思想的問題,也是每一種文明形態(tài)無法擺脫的宿命,更是所有存在者的必然結局。只不過有些存在者自身帶有“更化”的能力,因而能夠在相對僵化的時候通過不斷自我調適,吸收外在的能量,重新組織自身的結構和表現(xiàn)形式,即便不能長生或永恒,也至少可以極大地推遲衰老乃至死亡的到來,更有可能以脫胎換骨來重獲新生。
中華文明能夠延續(xù)數(shù)千年時間,而且在外來文明的沖擊下不斷取得新的輝煌,不僅是西方所認為的地理阻隔、文化孤島所造成的結果①,也不僅僅是20世紀學者們所總結出的“超穩(wěn)定結構”,即整體上的儒釋道互補,文化上的內圣外王互開,政治上的陽儒陰法,等等,而在于包括儒家文化在內的中華文明本身就特別注重自我的不斷升級改造。換言之,我們的文化基因中本來就帶有強大的自我修復功能。當然,這種“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內在更新能力也有其自身的限度。與西方文明相比,我們不是特別在意“永恒”,不刻意追求超越性的存在,而是要在變易與不易、恒常與流變之間尋找恰當?shù)钠胶饧?ldquo;中庸”或“中道”。
盡管后世誤把儒家思想當作千古不變的教條,但儒家思想并非自以為是且故步自封的既定理論,而是通過不斷的自我修正才獲得了崇高的歷史地位,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儒家哲學也不是后世那種書齋學問和官方意識形態(tài),而是以修齊治平為鴻鵠之志,因而就必須隨時遷化、與時偕行——“時”這個概念遠不是西方那種形而上學的對象,而是活潑實在、生生不息、具體而微的命理機制,因而儒家乃至整個中華文明總能在“時”的要求下不斷重生。
作者:程志敏
最新期刊論文咨詢
- 如何提高學生道德人格素養(yǎng)
2025-07-11瀏覽量:254
- 包裝設計理念形成整體化教學的方法
2025-07-10瀏覽量:399
- 包裝工程師發(fā)表論文在哪發(fā)
2025-07-10瀏覽量:294
- 交互設計提升理財類APP可用性研究
2025-07-09瀏覽量:335
- 農業(yè)類核心科技期刊微信公眾號的運營現(xiàn)狀及發(fā)展對策
2025-07-03瀏覽量:365
- 都勻毛尖茶旅游食品開發(fā)條件研究
2025-07-03瀏覽量:401
- 社會經濟地位與老年健康不平等基于生命歷程視角的研究
2024-11-23瀏覽量:401
- 廣西仫佬族剪紙藝術題材演變及數(shù)字化展示設計研究
2024-11-23瀏覽量:551
- AI創(chuàng)作物可版權性及保護路徑再探討
2024-11-22瀏覽量:338
- 現(xiàn)代(后現(xiàn)代)美術理論與媚俗藝術
2024-11-22瀏覽量:269
中文核心期刊推薦
-

-
統(tǒng)計與決策
級別:北大核心,CSSCI,AMI擴展
ISSN:1002-6487
刊期:進入查看
格式:咨詢顧問
-

-
統(tǒng)計研究
級別:北大核心,JST,CSSCI,WJCI,AMI權威
ISSN:1002-4565
刊期:進入查看
格式:咨詢顧問
-

-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huán)境
級別:北大核心,JST,CSCD,CSSCI,WJCI
ISSN:1002-2104
刊期:進入查看
格式:咨詢顧問
SCI核心期刊推薦
-

-
Scientific Reports
數(shù)據(jù)庫:SCI
ISSN:2045-2322
刊期:進入查看
格式:咨詢顧問
-

-
ACTA RADIOLOGICA
數(shù)據(jù)庫:SCI
ISSN:0284-1851
刊期:進入查看
格式:咨詢顧問
-

-
Materials Today Communications
數(shù)據(jù)庫:SCI
ISSN:2352-4928
刊期:進入查看
格式:咨詢顧問
-

-
APPLIED SURFACE SCIENCE
數(shù)據(jù)庫:SCI
ISSN:0169-4332
刊期:進入查看
格式:咨詢顧問
-

-
PLANT JOURNAL
數(shù)據(jù)庫:SCI
ISSN:0960-7412
刊期:進入查看
格式:咨詢顧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