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xi��ng)���Ї��ı����c������
�r�g�� ����r(n��ng)�I(y��)Փ�� �g�[�Δ�(sh��)��
������Փ���У��W(xu��)�߄�����ָ��“ֻ�Ю�(d��ng)?sh��)����˱����Լ��������ĕr�ŕ��������ĵӣ�һ�е�֮��͏ĵӳ������ѽ�(j��ng)�[Ó�˵ӵ��˶���ʧ�˱����ӵ���������鱻������ζ����ʹ�ú����ã���ʹ���������������Ҳ��ʹ�õӁ��C�������ڵӵĖ|������?q��)��������`�^(q��)”��

�������@�N���oƫ������һ���̶������f���˵ӰY�Y(ji��)�����u���о���ֻ�ßo�γ��J(r��n)��“�҂��l��߀���ܘ��^���f��‘��’�ѽ�(j��ng)���˱����Լ���������”�����P(gu��n)��“��”�������|(zh��)�ɡ�������(d��ng)�������uՓ��2008���4�������ƺ��o������“����”�Įa(ch��n)���ϲ���ǣ������һ�N�ɱ��Q֮���r(n��ng)��DŮ“�ڵ�”�ĬF(xi��n)��������Ȼ���������ij��F(xi��n)���H�������@�N���u��ħ�䣬���Ї��ČW(xu��)ʷ�ϵ�һ���������F(xi��n)��“�l(xi��ng)���ˌ��l(xi��ng)����”���l(xi��ng)���Ї����ұ��_(d��)�Ķ�����Ը��߀�ɴ˻ؑ�(y��ng)���l(xi��ng)���Ї���α����c���������l(xi��ng)����(j��ng)��c“���g”�����ȵ�Փ���е�ijЩδ�M���}��
����һ��Ů�r(n��ng)��“�ڵ�”���d��
����“�ڵ�”�������l(xi��ng)�����֮�⣬“�ڵ�”�l(xi��ng)���������r(n��ng)��DŮ���l(xi��ng)���Ї����l(f��)���I(y��)�ࡢԭ��(chu��ng)�ԕ���������������ڏV����r(n��ng)�壬�����w���ڄ��B(y��ng)�Һ��ڣ����@�˵������r(n��ng)æ֮���Գ֣��������o(j��)�l(xi��ng)�������ṩ���y�õ�“��������”��ԭ���B(t��i)�YԴ����Ҫ���߰��������������A���ܴ��m�����ϵ�ʯ�緼�����ĵ��R�۾꣬����Ľ��m�����V�|�����ԣ��Ĵ����θ���ȡ�
���������w���f��“�ڵ�”�߲�ͬ���ڳ�����ݚ�D(zhu��n)�����Ĵ��ČW(xu��)���ߣ�������ģ�M���˿��ǻ�ҕ�ǵČ��I(y��)���ң�������������������ͬ�ı�����һ����ס���������h(yu��n)�x���е�ƫƧ��կ���Ԅ�(w��)�r(n��ng)���ɽ�������(d��ng)��ķ���_С��ȷ����˵ĵӄڄ��\�����Ļ��̶��^�ͣ������]�����^��W(xu��)���L�r�g�Գ�͵͵����Ҫ�L�ڽ�(j��ng)���܇��˸�������ҕ������ijЩ�eԭ������l(f��)ý�w�P(gu��n)ע(��֮��“�X�cԊ��”�������A)�⣬��ʹ����Ʒ�l(f��)�������棬Ҳδ���������ĉ������P(gu��n)ע��
������(n��i)���ϣ����������IJ�����ģʽ����“�l(xi��ng)�����M(j��n)��”�Ĺ��£������Ƕ��С����顢���á���Խ����ͻ�ͨ���ČW(xu��)N�������ČW(xu��)ʷ�������Ї������ČW(xu��)���ģ�����Ŀǰ�ČW(xu��)��D������Щ�������l(xi��ng)���Ї��������ˑB(t��i)�ϣ�“�ڵ�”�������н�(j��ng)�����Փ��“�l(xi��ng)���ˌ��l(xi��ng)����”�����H�v�ԡ��w�ʽ��ʽ�����l(xi��ng)������@�cŮ�����x����ģ�M�l(xi��ng)���˿����M(j��n)�е�“���”(���ְס��DŮ�e��䛡�)����֪�RŮ���Բ��L���{(di��o)�С����ؿ�������ֶ��н��l(xi��ng)����“����”(���������Ї������f��)��̫һ�ӡ����w�ΑB(t��i)�ϣ�“�ڵ�”������������Ұ�L���l(xi��ng)���������ʽ���С����w���ޣ�С�f��Ԋ�衢ɢ�ĵȸ����w���У�Ҋ�C�����r(n��ng)��DŮ�܉�һ�����z�^��һ���ü��P�������o(j��)�¾��^��
�������ɷ��J(r��n)���c���������Գ��F(xi��n)���ČW(xu��)����ȣ�“�ڵ�”��Ů�r(n��ng)�����g��ƫ������ʮ�q�߾Ӷ࣬�@���c������Ҫ�˷��N�N�������ص��L�ڷe�����P(gu��n)�ģ����@Ҳ��������l(xi��ng)����(j��ng)�(�@��������Ψһ�������w�)�ĝ������“�������ǂ��������˶����﹡�ϣ�һ߅����߶߶�غ���߀�]�ɻ��Ů���s�o�ɻһ߅ק�����I(l��ng)�ړ����Լ��İ�߅Ę……”���@�������g���^�֙C���R�۾�P�µ�һ�����棬�o���R�ֵĴ���x��@ٝ“���ľ����҂��ɻ�Ĉ���”�����Ļ���DŮ�R�۾꣺��“Ĵָ�ČW(xu��)”ӛ�����ّB(t��i)�����^�r(n��ng)�����������ԭ���B(t��i)���������m�����P(gu��n)�r(n��ng)��DŮ������ͥ������С�f���隑��Ҳֱ��Դ���Լ����^�� �^���H�������^�ļұ��¼��������H���c�˲����r(n��ng)��DŮ�S��(qu��n)��ӡ��ܴ��m���۲���Ĵ������t���H�����r(n��ng)���˵�ʹ���c�g����߀���Լ���ԭ�͌��������ČW(xu��)�ۺ��ߵ�Ů���˹�20��������l(xi��ng)������^��ʷ��ʯ�緼�ġ�ɽŮ�����������꡷����ֱ�Ӂ�Դ���Լ���1985�굽2003���85����ӛ��
�����@Щ�r(n��ng)��DŮ��“�ڵ�”�����l(f��)�`���ˏ�������(j��ng)���l(f��)��������Ҳ�w�F(xi��n)�ˌ��l(xi��ng)������Ķ����Ա��_(d��)��������бȺݶ��K�Ŀ��y�O�˻��������ˣ���������l(xi��ng)���п����������ճ�����^�����R�۾꡶�ͽ⡷���l(xi��ng)��ĸŮ�g�ě_ͻ�c���ĺͽ⡣��̓��(g��u)“���l(xi��ng)�Pӛ”�����еČ��l(xi��ng)���ֵĸЇ@Ҳ�����@�����^���_(d��)�^���l(xi��ng)���đB(t��i)�˸е����l(xi��ng)���ů��һ�棬��“�L(f��ng)ɳ�ҟo̎��ȥ���چʵ���ֻ���Ų��������L(f��ng)�У��D(zhu��n)�^һ�l�ֵ���һ�l�֕r����ǰͻȻһ�F(tu��n)�ۼt����Ȼ��һ��ʢ�_���һ�……”(�R�۾꡶�����ڴ�����L(f��ng)�)Ů�����x�ЛQ�^���Ԅe������w���ˣ��ڱ��_(d��)������y֮����Ȼ���А�����c������������P(gu��n)���w������ʯ�緼��ɽŮ�����������꡷��С��������c�ώ��ļ�����鱻������Ⱦ�����Ք�������������ĬĬ����ף����ˇ�g(sh��)�ַ��ϳ��ˬF(xi��n)�����xġ����߀����һ���F(xi��n)�����x���W(xu��)�A����l(xi��ng)���^�գ���“��ꎲ���ƽ��������ô���ֲ���ȡ/��һ�^ţ��ȡ����ˮ��������ӷ�ȡ/��һ�����քݷ�ȡ/ͬ�r��Ҳ���ҷ�ȡ//���÷�ȡ�Ĺ�ꎜ����˰�݅��/ĸ�H���@Щ���霐����һ�^�װl(f��)/ֻ���f��g�v/——�����֜�����һ������”(�����A���M�������硷)��
��������“�ڵ�”���f�Ŀ����c����
�����r(n��ng)���Լ����f�Լ����Ї��ČW(xu��)ʷ������һ�N�����̖�١�1938�꣬ë�ɖ|���Ӱ���Ѹˇ�g(sh��)�W(xu��)Ժ��������ϰl(f��)�ԕr�f����“�l(xi��ng)�g���r(n��ng)��……�����κε�ʣ��v�Ĺ�� s�����ӣ����oҲ���������@Щ�r(n��ng)�H�Ǻܺõ�ɢ�ļң������Ǻܺõ�Ԋ��”��20���o(j��)50��������Ї����������Z�Z���ҵ�������\�ӣ��M���������΄ӆT����������ķ�ʽ��Ԋ��“���S�M(j��n)”�`������ˇ��(chu��ng)��Ҏ(gu��)�ɶ�����ʧ�����������r(n��ng)����l(xi��ng)�������Ї�������ˇ˼����һֱ�]���Д��^���r(n��ng)��DŮ“�ڵ�”���^��һ�Ό��F(xi��n)���ČW(xu��)ʷ�ϵ��@һ������Ը��
�����@һ�ČW(xu��)�F(xi��n)��Ă��e�r(n��ng)��DŮ�����DŽ�(chu��ng)�����ɳ���֮�ݣ��������γɵ�ԭ���Ƕ��ġ������߱��˲���á����g���Բ����Ŭ�����ČW(xu��)���Ă���Ʒ�|(zh��)(���m���I�������ͨ�^ �����C����Ļ����B(y��ng)���ܴ��m�ڏU���ČW(xu��)�����I(y��)���ϣ�ʯ�緼���ꮋ�����θ���ʡ���N�]Ʊ���X�c���ь��Ž���)�⣬߀�c�����o(j��)�ԁ�V�����ҕ�����ǻ�(li��n)�W(w��ng)���g(sh��)���r(n��ng)��^(q��)�İl(f��)չ�c�ռ��ȴ�ý�w���P(gu��n)�����罪�m������ �V����߀ͨ�^���Լ�����Ʒ�Ľo��_���ū@������İl(f��)��;��;���Q��“Ĵָ����”���R�۾��ڹ��������֙C��6����É���7���֙C��40�f�֣�ͨ�^QQ�c�x�߽���;�����A�tͨ�^�_ͨ���˲��Ͱl(f��)����Ԋ����Ʒ��Ŀǰ�����L��������Ӌ400���f�˴Σ��ஔ(d��ng)������Ʒ��ԭ��(chu��ng)�W(w��ng)�j(lu��)�l(f��)��ƽ�_��
�������y(t��ng)�ČW(xu��)���a(ch��n)�C���c���������C��Ҳ��“�ڵ�”���˺ܴ�ĹĄ�������á��挦��ý�w�ČW(xu��)���Ј����ČW(xu��)�ě_�����ЌW(xu��)�˲��o���^���A(y��)�ԣ�“�ČW(xu��)�ڿ������g����Ȧ�ӻ���߅����”��“‘���I(y��)—�I(y��)��’�����w�ƽ��w”��“���y(t��ng)�ČW(xu��)���a(ch��n)�C�Ƶ�Σ�C�����͙C�Ƶ�����”��������������y(t��ng)�ČW(xu��)���a(ch��n)�C�Ƶ�Σ�C�����͙C�Ƶ����ɡ�������ˇ���Q��2009���12�ڡ����^�������l(xi��ng)���r(n��ng)��“�ڵ�”���£����y(t��ng)�ČW(xu��)�w�Ʋ��H�]��ʧЧ��߀�����P(gu��n)�I�����ã�����y(t��ng)�ČW(xu��)�ڿ����S���ČW(xu��)����˷�����l(f��)���R�۾���Ʒ���������ČW(xu��)���l(f��)���ܴ��m��Ʒ���o������Ī��ĹĄ��c֧�֣�����Ԋ���s־��Ԋ�����������A������������Ҫ���á�
�������f(xi��)ϵ�y(t��ng)�ĸ���֪�Ҵ�����¶�^�ǵ��r(n��ng)��DŮ“�ڵ�”���������Ʋ����������ã���ʯ�緼�ī@����ʡ���f(xi��)�LƪС�f��Ʒ���̃�(y��u)����Ʒ�����ܴ��m���x����ʡ���f(xi��)“�r(n��ng)�����ҷ���Ӌ��”�����m����Ʒ���Ĵ�ʡ���f(xi��)�����Y����ֹ��_���档���I(y��)���һ�?q��)W�ߎ����I(y��)���ߵă�(y��u)�����y(t��ng)Ҳ�l(f��)�]�˺ܴ�����ã���V�|�_������(li��n)���TՈ���I(y��)���Ҟ����Ըĸ壬���������W(xu��)�����c�ܴ��m“�Y(ji��)����”���ĸ�ȡ�����������ƄӸ���ʹ�@һ�ČW(xu��)�F(xi��n)��@���������y�ԱȔM�������YԴ�����θ���ġ������Ҹ���Ů�ˡ��������������k������������(li��n)���e�k��“��λ�r(n��ng)�����ҡ��ٲ��r(n��ng)����Ʒ”�������Ѝ�¶�^�ǵģ����Եġ��{����Y(ji��)�������Ƹ����˴��I(l��ng)��(d��o)���^����ģ���������M�ȡ������늴���W(xu��)�T�����⣬�@ЩŮ�r(n��ng)���߾��ڮ�(d��ng)?sh��)ث@���˸��N�����s�u�Q̖���������x����ʡ���l(xi��ng)�(zh��n)�������ȵ�“���˼t����”������߀��“���Ї��ČW(xu��)ʷ�ϣ���һλ���LƪС�f�@����ȫ���ڄ�ģ���Q̖”��
������(d��ng)Ȼ����Ȼ�Ƿ��I(y��)�ĘI(y��)�࣬�������ڴ��Ļ��c�����Ļ������Ƅ��®a(ch��n)�����ČW(xu��)�F(xi��n)������Ҳ�y����ڶ�N���}�����缼�ɡ��Z�������o���������ֲڣ���ʹ�l(f��)����Ҳ�㲻�þ��A��֮�������ܴ��m���m������“С����������~������������N�ӣ�������ײ���ҵ��ģ��l(f��)���H�I�Ļ�”��“������~”���滯�����˻���“����������N��”��ֱ̫�ס���Ӳ������һ����һ���`�У���δ�a(ch��n)��̫���ČW(xu��)�����o�����У��l(xi��ng)������ͬ�ߕ�1980����ġ�ꐊJ���ϳǡ�����һ�����x��
����߀�����W(xu��)�^����^������θ��㡶���Ҹ���Ů�ˡ�����һ�B���`�����ɺϡ��������������Ĵ�������£�������Ѫ�}�����������x������ʹ����e���I���Ȼ����Ǹ���͵��������ҕ�̄���ˇ�g(sh��)�Ա��^�ֲ�;�������������߅^(q��)�鱳������Ʒ����ů���������W(xu��)�^�������^������������һ��څ�ڱ��صĂ��y(t��ng)Ȥζ;ʯ�緼���ܴ��m���r(n��ng)��Ů�ČW(xu��)��������˹����Ԃ��w����(chu��ng)����ּ�ϲ�������ͬ�A���y(t��ng)�F(xi��n)�����x�ַ���������һ���c���I(y��)Ů���ҵ��Ԃ��ԕ��������W(xu��)���_(d��)���в���ͬ�ն��Z�����u���Ϸ��f�^��“���g�Ļ��������l(f��)�ģ�С�͵ģ��ֲڵģ������Եģ�����H�H̎�ڴ��Ļ���߅��”���Ϸ��������c���Ļ��������|�όW(xu��)�g(sh��)��2007���5�ڡ��r(n��ng)��DŮ��“�ڵ�”���w���f��߀�y��Ó�xˇ�g(sh��)��ģ�¡��^�������f���ַ��φ�һ�ȵ��ČW(xu��)��(x��)�����E��
�������в�ͬ���������A��Ԋ�脓(chu��ng)�����@����ý�w�N��“�X�cԊ��”��(bi��o)��һ�ȟ᳴���r(n��ng)�����ߣ����������DŮ���l(xi��ng)��?x��)�����ˇ�g(sh��)�^��������ͻ�ƣ����䡶���B(y��ng)�Ĺ�����С�ס����Ґ��㡷��Ԋ���Ѳ����Æ�һ�ĬF(xi��n)�����xˇ�g(sh��)�ַ����l(xi��ng)������Ҳ��������“�ڵ�”Ů�����ǘӺ��Ρ����������ʣ�����һ�硶�翯�����������f��“��Ѭ���ǣ���ɳ���£����c��֮�g߀�����@��Ѫ��”�����䲻�H��һ���F(xi��n)�����x���|(zh��)��Ҳ��Ů�����x������“һԺ�ӵ����װ����Ƕ�ô�Ը�……�Ҵ���?sh��)ذ�����������˵���ֳ���٣��Ұ��������w���������߰������ȱ⣬�]���l����ҳɞ�һ��Ů��”�ȣ����r(n��ng)��DŮ�l(xi��ng)��?x��)�����������һ���^�ߵ�ˇ�g(sh��)ˮƽ���M��Ԋ�����u���挦�����AԊ��r����“����”��“ý��”�ȵIJ�ͬ���}���O��s���������AԊ���c�ČW(xu��)“�¼���”�������Ϸ��ĉ���2015���3�ڡ�
�������������AԊ������һ���Ј���Ȥζ�ģ����^��낀�Ї�ȥ˯�㡷�������c“��(bi��o)�}�h”�A��ȣ������DZ��ô���֮�����ƺ��D(zhu��n)�����܉����ཛ(j��ng)��(j��)����Ĵ��Ļ������������u�����s����Į��“�e����ô�x����ο����DŽe�˵����飬�c�қ]��ʲô�P(gu��n)ϵ”������һ�c����ഺ�ČW(xu��)“�����Ј������l”��ƫ�M�c����֮�⡣�@�c�ܴ��m�����Եȫ@���������w�Ǝ���֮��ĸж�������w�γ����r���Č��ȣ��w�F(xi��n)���r(n��ng)��DŮ“�ڵ�”ͬ�����ČW(xu��)����һ��Ҳ�Ѓ�(n��i)���IJ�c�ֻ��������f���@һ�ČW(xu��)�F(xi��n)��һ���̶����w�F(xi��n)�ˌ��������R�ΑB(t��i)�c��Ȥζ���S���@Ҳ���҂���Ҫע��Ć��}����һ����
���������l(xi��ng)�������c���������l(xi��ng)��
�����ĺ�ֳ��Ů�����x��˹Ƥ�߿�“�������fԒ��”�İl(f��)�������_�x���ڡ��|���W(xu��)���Ќ��R��˼��һ��Ԓ(“�����o�������Լ���������횱��e�˱���”)ӡ����퓣��D(zhu��n)�����Ϸ�������N������63퓣��Ϻ�����(f��)����W(xu��)�����磬2007���W(xu��)���һ���Փ֮̎����һ����������x���l(f��)������������ͨ��������һ�������ƺ����ø��N��Փ�C���l(xi��ng)���o���l(f��)����“����һ���]���������_(d��)�Լ�����Մ�����аl(f��)�ԙ�(qu��n)��Ⱥ�w��ȥ�f����‘��ʲô’����վ��������‘����’�fԒ�Ǜ]�����x�ģ����������ʲô�ā������i……�������DZ�������‘����’���������ق���Ҳ��һ�NŤ��������������?n��i)�Ȼ�]�г��F(xi��n)”��
�����������ܷ�[Ó�����������\���������ġ�2004���2�ڡ���ʹ����ijЩ��������“�ӌ���”���ČW(xu��)�F(xi��n)�W(xu��)��߀���m�Y(ji��)��“�܉��M(j��n)�����ֱ��_(d��)�ĵ�߀�Dz��������ĵ�”�Ă������������A�����Ї���Ԋ�衷�����u��“�����(sh��)��Ʒ������һ���[���ĽǶ�չ�_�ģ����Լ���վ��һ�����е��ˡ�һ���c�����������‘�Ϸ���ס��(qu��n)’���˵ĽǶȁ������Ԇ��ģ��@Ҳ��(y��ng)ԓ��������‘֪�R������’����һ�w�F(xi��n)”�������A����“������”�c�҂��r����Ԋ�肐����������ˇ���Q��2005���3�ڡ����@һ�c�ϣ��r(n��ng)��DŮ��“�ڵ�”�ƺ���Ψһ���Ó�(d��n)�ġ������|(zh��)�ɵ�“�ӌ���”֮�����������A��ÿ���I(l��ng)ȡ60Ԫ�ͱ��ȝ�(j��)����r(n��ng)�嚈����;�ܴ��m�I�������“һ��8ë�X���]Ʊ����Ҫ�����}������۳���”������÷��ҧ���I���_“�rֵ3180Ԫ����X���ஔ(d��ng)��ȫ�ҽ�һ���������”�ȡ����͵��f���˼ң���ȫ���r(n��ng)���ƽ������ˮƽ���ԣ�����Ҳ���r(n��ng)���еĵӣ��������l(f��)�О錦“���ܷ����ұ���”�ČW(xu��)���Ɇ��o��һ�����������ش�
������(d��ng)Ȼ���Y(ji��)�������r(n��ng)��DŮ�l(xi��ng)������ͬ�����@�����W(xu��)�����ԣ��҂�Ҳ���ܷ��J(r��n)���}����һ���棺“�ڵ�”���ݾ��ܱ��C�����l(xi��ng)���Ї����ᣬ�r(n��ng)���}�Ą�(chu��ng)��һ����Ҫ���_��“�ӌ���”��?�@Ȼ�����l(xi��ng)���Ї�ԭ���B(t��i)�������^���ڴ��c���뻯�A(y��)�O(sh��)ֻ����֪�R�W(xu��)�˵�һ����Ը�����R˹·�֠������ԣ�“һ�Ї�(y��n)�C����Ʒ�f���ױ�Ȼ�����Ԃ����|(zh��)�ģ�����һ����Ҫ�넓(chu��ng)����һ�������挍�rֵ�Ė|���������ʹ���Լ������е��ز��c��(j��ng)�v��”���������R˹·�֠���һ��С�f�Ĺ��¡�����24퓣��S��ʯ�g���Ϻ����Ϻ���(li��n)���꣬1991��
�������ǣ��@�N��(j��ng)�����Փ���ܱ����ε������ֻ�������r(n��ng)���“������”�r(n��ng)����ܕ�����“������”�l(xi��ng)���ČW(xu��)������@��һ�N�Cе��������x�^������f�ߟoՓ��ʲô�}�ģ�����횄����Լ��挍�������w���ⲿ����Ͷ���������Ԕ���������f�С����w���l(xi��ng)�������}�����߿��ܷ�“�ڵ�”�ߣ����@��(y��ng)ԓ�����K���l(xi��ng)��?x��)������P(gu��n)�I��������������������“�ڵ�”����������{(di��o)���Լ�ȫ���������w��c��(chu��ng)���������Ļ�������“�ڵ�”�����@һ�c�ϣ���(d��ng)���ĉ�������ij�N�����̽���������ְġ��DŮ�e��䛡����@��һ�����˸�׃�Լ���ˇ�g(sh��)���ԣ������l(xi��ng)���ı����D(zhu��n)����ģ�M�l(xi��ng)�����ұ�����“�M‘�ڵ�’����”֮�������邀�˻����������ְ��ڌ��l(xi��ng)��������û�ɫ���㡢�u�w�����������|(zh��)�е�ˇ�g(sh��)�������棬������“�ڵ�”�ߵ�ˮƽ���w�F(xi��n)�ˌ��I(y��)�������������Լ������L�Ă��˻���߅����ҕ�DZ����l(xi��ng)�����磬�������c�r(n��ng)��DŮ��“�ڵ�”������ͬ���l(xi��ng)�����磬�@�������䂀�˵�������Ȥζ�ڰl(f��)�]���á����@����Ʒ�����W(xu��)��һ�㌢����x��“����ͬ�ڴֲ������”��ԭ���B(t��i)չʾ���@�͌��l(xi��ng)��������һЩ����ӴεĂ��톖�}�ڱ��ˡ�
����߀���̓��(g��u)�е��l(xi��ng)���������������ġ��Ї������f�����M�����Ի��l(xi��ng)���L�ķ�ʽʮ�ֽӵؚ⣬�����L��Щ�ˣ�����Щ�˵���Փ���M(j��n)�ı��K������������(d��o)���������������猍����������ͨ�^���F(xi��n)���f˼���Ї��F(xi��n)�������\�ĺ��(g��u)�룬��һ�N���͵�֪�R����˼�S�������@��������}���R�ѱ����еČW(xu��)�����l(f��)�F(xi��n)������W(xu��)���ڵĔ�����ͬ�����J(r��n)֪֮�g�о��x������������ע֪�R�����������o�ɺ�ǣ��ɞ�ʲô����Ҫ���LՄ��“���Մ����ϣ�����↢�����xҕ��”?������̓��(g��u)�c�����Ї��l(xi��ng)���ķ�����——�ԡ��DŮ�e��䛡������f��������������ˇ�о���2016���6�ڡ�߀����~�ġ��w��ӛ�������ӛ�������о��߰l(f��)�F(xi��n)������վ���˞����\˽������ռ�������w����l(xi��ng)��“ռ����”�����ϣ�“����˽������Ĵ������ߵ��˹�������ķ���”��Ҳ�ߵ��������ԁ��Թ�ƽ���x����ĵ�֪�R���ӆ��ɂ��y(t��ng)�ķ��棬�����İl(f��)�ԣ�Ҋ����ȣ����ؽ��ČW(xu��)���������——“��̓��(g��u)”�c�҂��ĕr����������ˇ?y��n)�Փ�c���u��2016���4�ڡ��@����һ�Nʲô���x�ϵ��l(xi��ng)������?�oՓ��Σ��@Щ֪�RŮ�Ե��l(xi��ng)�����£�ͬ�r(n��ng)��DŮ“�ڵ�”�l(xi��ng)�������������R�ΑB(t��i)����Ļ�Ȥζ���Sһ�����ڲ�ͬ����϶�ʹ���l(xi��ng)���Ї��ı����c���������}׃�ø��ӏ�(f��)�s������
�����ġ�“���g”�����c�ؽ��l(xi��ng)��������
��������һ�N�����l(xi��ng)����߅���������r(n��ng)��DŮ��“�ڵ�”�����l(f��)���I(y��)�ࡢԭ��(chu��ng)���c����ʾ�˵��܉����Ұl(f��)�ĕr���¾��^�������cŮ�����l(xi��ng)���D(zhu��n)���֮�g����ķ���s��¶���l(xi��ng)���F(xi��n)���c֪�R��“���g”����֮�g������϶��
�����ڮ�(d��ng)���W(xu��)�g(sh��)Ԓ�Z�У��l(xi��ng)�������g��(j��ng)���������˻��ã��ƺ������Dz��ĸ�������H�϶��߲���һ�¡��l(xi��ng)�����r(n��ng)�塢���ء��l(xi��ng)Ұ����ָ��������V��^(q��)��Č��w�ԡ����^�Ը�����g�t��һ�����Ļ�ϵ�y(t��ng)�б�����(g��u)�ĸ�����Ļ��о��ߵ����⣬�����Ї�ȱ�����������ǘ�������/���g���������ʥ/�ڽ�����Ă��y(t��ng)��ͬ�rҲ�����������R�ΑB(t��i)�ď���“���g����һ����������Ҏ(gu��)���Č��w������һ���r�r�c�ٷ����ּȷּȺ��P(gu��n)ϵ�ărֵ”�����g�������ڱ���ϵ�y(t��ng)�г��F(xi��n)������������ͬ�w��“���g����������@�Ă��y(t��ng)̥ӛ��������g������ǂ��y(t��ng)���w��һ���M�ɲ���������(g��u)�ɗl��”���ޅ��������g�������е�����������Ļ��о�����1����162��163퓣�����������ƌW(xu��)Ժ�����磬2000��
���������g����ϵ�y(t��ng)���@�N�U��cǰ���r(n��ng)��DŮ�l(xi��ng)������r������һ�µģ��M��“�ڵ�”����(n��i)��Ҳ��һ���ֻ��������ā��f���ܻ��������o(j��)�Ї������Ą����r(n��ng)���Ļ����O(sh��)�ĸ�����ߣ���һ���̶����Ԍ������Ļ����Sԏ����@�N�ٷ�/���g�������е��P(gu��n)ϵ�����⣬ǰ��Փ���������o�������ֲڡ����W(xu��)Ȥζ���������ء��ַ���������һ��ˇ�g(sh��)���Ȇ��}��Ҳ����“���y(t��ng)̥ӛ”��һ�N�w�F(xi��n)����ʹ������c���Ļ���(li��n)ϵ���������˴��Ļ���һ���֡�����ԭ�����c���ڸ������|(zh��)����l���Ľ�(j��ng)��(j��)�����⣬�P�߿���Ҳ�c���_·���R���ڡ��������ߵĽ����W(xu��)�������ᵽ�ĵ��������ܵ������w�Ƶę�(qu��n)��“Ҏ(gu��)Ӗ(x��n)”���Ļ�“ԃ��”���P(gu��n)���_������“��ū�Y(ji��)��(g��u)”�c“�Ӱl(f��)”——�ı��_·���R����Ѹ��������(d��ng)�������uՓ��2004���5�ڡ������^������̎��ƫ�h(yu��n)�l(xi��ng)�����˂��������|�����������Ļ��c���Ļ���������֪�R�����Ļ���
����“���g”���ČW(xu��)�о���t���˸����Uጡ��˼�ͽ����ڡ��Ї���(d��ng)���ČW(xu��)ʷ�̡̳��Ќ�“���g”���x��“�ڇ��ҙ�(qu��n)���������������ĵط��a(ch��n)�����������������ɻ����ʽ;��������������������L(f��ng)��;�����Եľ��A�c�⽨�Ե����ɽ�����һ��”���˼�����������Ї���(d��ng)���ČW(xu��)ʷ�̡̳�����12퓣��Ϻ�����(f��)����W(xu��)�����磬1999���@��һ���������^���Ķ��x�����^�ھ��w�\�õĕr�����������g/�ٷ���ԪՓ�Ŀ����ʹ���@һ����ģ����{(di��o)��“���g�Ļ��ΑB(t��i)”“���g�[�νY(ji��)��(g��u)”���۵صֿ�����һ�w����������R�ΑB(t��i)�Q�ƣ�ͻ������“���g”���ɡ����ڵĬF(xi��n)���Ծ�������һ������ϣ��A����Ҳ���{����“���g”����֮�У���1930����a���ڡ����g�ČW(xu��)���f�����J(r��n)��“���g�ČW(xu��)�nj��ڟo���R�A�ӡ��o�a(ch��n)�A��ƽ����ČW(xu��)�����c���R�A�ӡ��Y�a(ch��n)�A���F����ČW(xu��)������”��
�������������������ë�ɖ|��ˇ�^�����L�^���У����g��ͬ�ڄ������w���ڄ��ߡ����r(n��ng)��(li��n)ϵ��һ�𣬏��{(di��o)�������ԃ�(n��i)���������A�ӷֻ����P(gu��n)ע�����������o(j��)�Z�����M(j��n)һ���ܻ���������о����@�ӣ�������־��������С��P(gu��n)������Ⱥ�w�ȃ�(y��u)��Ʒ����“���g”�@������R��һ�ã����x��W(xu��)�Ҍ�“���g”�Ľ���(g��u)�Խ��x�s�ƺ�Խ��Խ�h(yu��n)�������nj��w��“���g”�����е��l(xi��ng)������F(xi��n)��——���y(t��ng)Ȥζ���c�ٷ��ȷּȺϵărֵ�����^�ղ��㡣�硶�Ї���(d��ng)���ČW(xu��)ʷ�̡̳��M���ᵽ�����g“�����Եľ��A�c�⽨�Ե����ɽ�����һ��”�IJ��ۼ{�����|(zh��)�����ھ��w�ı���������������(c��)����“�����Ծ��A”�����������R�ΑB(t��i)��һ�棬����“�⽨������”һ��Փ�������ࡣ
�����l(xi��ng)���F(xi��n)���c���l(xi��ng)���D(zhu��n)����“���g”��������x����֮�g��ì�ܣ�������һ�w������У���Ҫ���F(xi��n)������֪�R���ӿ���ͨ�^��Ʒ�е�“���g”�������۵ر��_(d��)���^�ָ߉����������εķ��������F(xi��n)����“���r(n��ng)���W(xu��)��(x��)”��֪�R���Ӆs�����ˇ�g(sh��)�|(zh��)���»������ԉ���Ť���Ŀ�����������ڮ�(d��ng)ǰ���Ї�������@һì�܄t�w�F(xi��n)���l(xi��ng)���ČW(xu��)��(chu��ng)���е��T���Փ��һ��������Փ�ϴ������A �����l(xi��ng)������������һ����t���F(xi��n)�����r(n��ng)��DŮ“�ڵ�”���r(n��ng)��ԭ��(chu��ng)�ČW(xu��)�P(gu��n)ע�����ɴ�ҕ����Ҋ;һ����Ą�l(xi��ng)������N�����N��������������“���g”�����Y(ji��)����һ����s����߲��룬Ҳ�o�������Լ��Ą�(chu��ng)�����Զ�ʹ�@�N“���g”�J(r��n)ͬ����ۿۡ���“���g����”�ď�(f��)�s���Uጣ��Ʌ�Ҋ�����ѣ���Փ�Zƽ��С�f���O�����еĔ�������������̶��W(xu��)�W(xu��)��(�܌W(xu��)����ƌW(xu��)��)2018���1�ڡ��DŮ�e��䛡�“���g”�еĂ��˻�Ȥζ�����Ї������f��“��̓��(g��u)���”�е�֪�R�������R���c�@�N�Ļ��Փ���P(gu��n)�������~��Ʒ�t�o���б�¶��“���g����”�в��ۼ{����һ���棬�@�DZ�������x��“���g”�����ڱε��l(xi��ng)���Ї�����һ�N����
�������ҷ�������ʾ��“�҂������r(n��ng)����Ҫ�Ƴ��ײ��@����Ʒ������ϣ��ͨ�^�����ģ����������l(xi��ng)����˂����fһ�N���ʽ�c������r(n��ng)�壬�I(y��)���r�g���˿��ҕ�����ـ�����錢֮�⣬߀����һ�N��������x�����@��һ�N��ֵ�������ʽ”�����҂�����Ʒ�c�f��һ����L——����10λ�r(n��ng)������LƪС�f�������r(n��ng)���Ո�2012��3��31�ա������r(n��ng)����@�N�B(t��i)����ֵ��ٝ�S�ģ��r(n��ng)��DŮ�l(f��)���I(y��)���l(xi��ng)�������x�Ǵ����������ṩ���ČW(xu��)��Ʒ�����ģ������l(xi��ng)���Ї�һ�N�Ļ�Ҋ�C�����������������������������c�Ļ�����;��Σ�߀�Լ����Գ��F(xi��n)���l(f��)���_(d��)�������l(xi��ng)���ČW(xu��)������J(r��n)֪�ȣ����Ĭ�Ĵ����(sh��)�_���vԒ�ṩ��һ���F(xi��n)���Ęӱ������C;��������һ�����S������̫��(y��u)�㣬�����挍�ɸе��l(xi��ng)���ı����Ƴ���“���g�Ļ�”�����ػ��c���뻯�����l(xi��ng)���Ї��ı����c������Փ���ṩ��һЩ�rֵ���գ��@�nj�֪�R������ʾ��
����Ī���J(r��n)��ͨ�����f��“���ϰ���”ò�Ƶ��{(di��o)���أ�Ҳ�Д����˾Ӹ��R�µĵ����f����ζ������(y��ng)��“���ϰ���”�Ğ�“�����ϰ���”�����ֻ��“����”һ���ϰ���ȥ�ŕ�ƽ�ȵ،���������x�ߣ��ƽ┢�����c�l(xi��ng)�����g��“��ƽ��”�P(gu��n)ϵ���@�N�ᷨ����������Ҫ���x�����ڌ��`����ԓ���ȥ���w�`���@�N“�����ϰ���”����?һ���l(xi��ng)��“�ڵ�”�DŮ�ǘ�ȥ��?�@�ӕ��������ij�Nˇ�g(sh��)�|(zh��)�����½�?�@�N��(d��n)�n���Ǜ]�е����ģ�Ī�����Լ���Ʒ�Ќ�“���g����”�Ŀ�g���Yٝ�cħ�ìF(xi��n)�����x�ַ���ͬ�l(xi��ng)���Į�(d��ng)�½���ˮƽ֮�g���ƺ�Ҳ��һ�β�С�ľ��x��
�������u���Ϸ��������һ�N˼·��“�ӽ�(j��ng)�ijɹ���������һ��֪�R���ӣ�����һ���A�ӌ���һ���A�ӵ��������@�N�����Ą����ܴ�̶���ǡǡԴ�ڶ��ߵIJ��”�Ϸ�������N�������Ļ��о�����1����65퓣�����������ƌW(xu��)Ժ�����磬2000������f���J(r��n)������ز����һζ��ӿ��R�������ڰl(f��)�]���҂��ԣ���(chu��ng)����һ�����ӻ����l(xi��ng)�����磬��α��C�@�N“�”��ҕ�Dz�������߸����ϵľ�Ӣ���x��?�P�߿������r(n��ng)��D١�g(sh��)�υ���R���l(xi��ng)�����¿�������ij�N���գ�����l(xi��ng)���Ї����Ļ����_(d��)��������һ�N��Դ��ڣ������ڱ����Լ��c�l(xi��ng)���IJ�ಢ����Ȼ����(d��o)���l(xi��ng)�����_(d��)��Ť�����ڱΣ�����Ѹ�ġ����l(xi��ng)����ף������ǡǡԴ�ڔ�����֪�R�������R�ď����ڈ��Ō����l(xi��ng)���ľ���֮�����F(xi��n)��������侫տ��
������ˣ��l(xi��ng)�����µ��P(gu��n)�I�����������^�ϱ��ֵ��dž���߀��“���g”�������������ܷ��l(xi��ng)��������|�|���������������P(gu��n)���c��Ҋ����t����ʹ����ĵ���ʾ“���g”����������ģ�M�����L���{(di��o)�е�����ֶ���������ȵؿs���c�l(xi��ng)���Ї��Ŀ��g���x(Ŀǰ�ĉ��ƺ�����һ�N�������ˑB(t��i)һ���ٽ��������g������(d��ng)��“�������_”�Ă���)��Ҳδ��(chu��ng)�������������x���l(xi��ng)���ČW(xu��)��߀������l(xi��ng)�����µ�ģʽ���cͬ�|(zh��)�����@�ڮ�(d��ng)���ĉ������rҊ��
����������P��ϣ���W(xu��)���܉�ʹ��“�l(xi��ng)��”�@�����w�ԡ������Ը�������Ǹ�����̫��֪�R�����Ļ������c���R�ΑB(t��i)���a��“���g”һ�~�����ؽ��l(xi��ng)�傐�����ČW(xu��)ʷ���҂�����(j��ng)���^��Ѹ������ġ��w�����ȸ�����ɫ���l(xi��ng)�������y(t��ng)�������[�����ČW(xu��)���������ܴ����Ї���(j��ng)�IJ��֡��r(n��ng)��DŮ�ĘI(y��)��M��ֻ��һ����(x��)С��֧�������]�Л_���l(xi��ng)���ČW(xu��)��B�ĸ��������s��“�ڵ�”���������f�ķ�ʽ�҂��Q̽�����l(xi��ng)���Ļ�������һ�棬�����ČW(xu��)Փ���е�ijЩδ�M֮̎��һ�������c��ʾ����Ը�W(xu��)���܉��Ƴ�“���g”���R�ΑB(t��i)�ľ����������F(xi��n)�l(xi��ng)�����µĶ��ӻ��c�F(xi��n)�����l(f��)չ��
�������P(gu��n)Փ�ķ��ģ��r(n��ng)���l(xi��ng)���n���YԴ���_�l(f��)������
�����@ƪ�r(n��ng)���о�Փ�İl(f��)�����r(n��ng)���l(xi��ng)���n���YԴ���_�l(f��)�����ã�Փ�Č��l(xi��ng)���n���YԴ�ĸ����M(j��n)���˷�����̽ӑ���l(xi��ng)���n���YԴ�ķ��ᘌ��r(n��ng)���l(xi��ng)���n���YԴ�_�l(f��)�����ó��F(xi��n)�Ć��}�M(j��n)���˷�����̽ӑ����������_�l(f��)�����õČ��ߡ�
�����ڿ�Փ����ԃ
- �r(n��ng)�I(y��)�I(y��)��λ����ؔ��(w��)�����ƶȳ�̽
2025-07-23�g�[����252
- �Ĵ���Ҫ��������Ʒ�N���߲��Ŀ����b�����u�r
2025-07-22�g�[����390
- �F��ʡ�֘I(y��)���B(t��i)�a���C�ƴ��چ��}�����ƽ��h
2025-07-17�g�[����455
- ��(x��)�L���߲�ժܛ�w���ץ���O(sh��)Ӌ�c����(sh��)��(y��u)��
2025-07-17�g�[����273
- ���ڶ��f(xi��)�h�Ĝ���������(li��n)�W(w��ng)ϵ�y(t��ng)�о�
2025-07-17�g�[����381
- �t��Ҏ(gu��)ģ����(y��u)�|(zh��)�S�a(ch��n)���༼�g(sh��)
2025-07-17�g�[����220
- ����ҕ�X�ŷ��Ķ�Ʒ�N����������ϵ�y(t��ng)�о�
2025-07-17�g�[����189
- Ӌ��Cҕ�X���g(sh��)�������C���M(j��n)�����ϵđ�(y��ng)��
2025-07-17�g�[����335
- �\Մ�ǻ۴����л����r(n��ng)ˎ����Ⱦ����
2025-07-17�g�[����350
- ����Ƕ��ʽ��Ӝy�����r(n��ng)�C�_�l(f��)
2025-07-17�g�[����268
���ĺ����ڿ����]
-

-
�y(t��ng)Ӌ�c�Q��
���e���������,CSSCI,AMI�U(ku��)չ
ISSN��1002-6487
���ڣ��M(j��n)��鿴
��ʽ����ԃ�
-

-
�y(t��ng)Ӌ�о�
���e���������,JST,CSSCI,WJCI,AMI��(qu��n)��
ISSN��1002-4565
���ڣ��M(j��n)��鿴
��ʽ����ԃ�
-

-
�Ї��˿ڡ��YԴ�c�h(hu��n)��
���e���������,JST,CSCD,CSSCI,WJCI
ISSN��1002-2104
���ڣ��M(j��n)��鿴
��ʽ����ԃ�
-

-
���W(xu��)
���e���������,CSSCI,AMI����,��ƻ����Y���ڿ�,
ISSN��1000-4238
���ڣ��M(j��n)��鿴
��ʽ����ԃ�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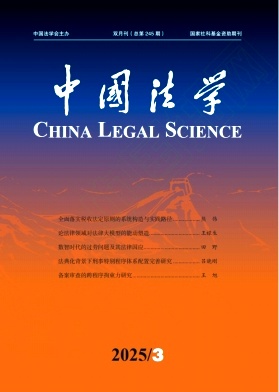
-
�Ї����W(xu��)�s־
���e���������,CSSCI,AMI��(qu��n)��,��ƻ����Y���ڿ�,
ISSN��1003-1707
���ڣ��M(j��n)��鿴
��ʽ����ԃ�
SCI�����ڿ����]
-

-
Scientific Reports
��(sh��)��(j��)�죺SCI
ISSN��2045-2322
���ڣ��M(j��n)��鿴
��ʽ����ԃ�
-

-
ACTA RADIOLOGICA
��(sh��)��(j��)�죺SCI
ISSN��0284-1851
���ڣ��M(j��n)��鿴
��ʽ����ԃ�
-

-
Materials Today Communications
��(sh��)��(j��)�죺SCI
ISSN��2352-4928
���ڣ��M(j��n)��鿴
��ʽ����ԃ�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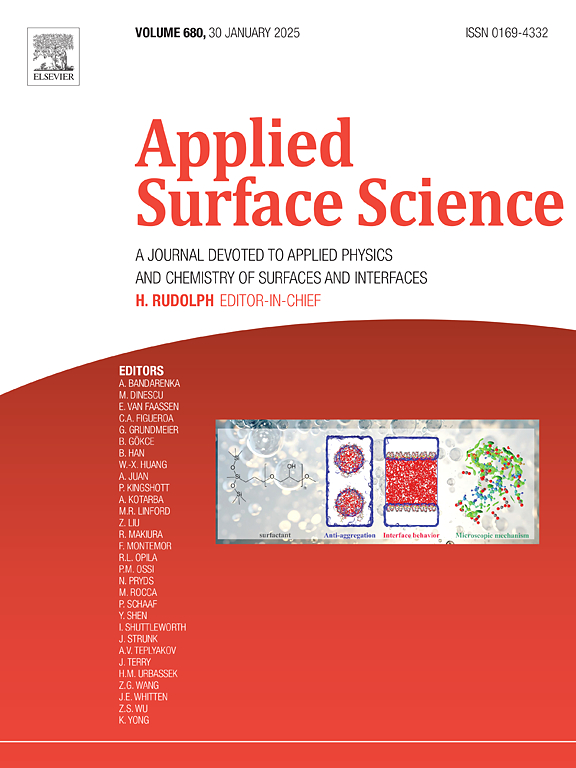
-
APPLIED SURFACE SCIENCE
��(sh��)��(j��)�죺SCI
ISSN��0169-4332
���ڣ��M(j��n)��鿴
��ʽ����ԃ�
-

-
PLANT JOURNAL
��(sh��)��(j��)�죺SCI
ISSN��0960-7412
���ڣ��M(j��n)��鿴
��ʽ����ԃ�
���T�W(xu��)��SCI�ڿ�Ŀ�
���T�����ڿ�Ŀ�
�ڿ��cՓ�Č��}
Փ�ķ����īI(xi��n)�ϼ�
- ��ý�w��Ϣ���g(sh��)�ڻ��W(xu��)�̌W(xu��)��(y��ng)�õ�Փ�ķ���2ƪ
- ���л��W(xu��)���̌W(xu��)��Փ���īI(xi��n)2ƪ
- ���л��W(xu��)�̌W(xu��)Փ��Փ�ķ���3ƪ
- ݔ늾�·����Փ�ķ���2ƪ
- ݔ늾�·�������g(sh��)Փ�ą����īI(xi��n)2ƪ
- �Ļ��z�a(ch��n)�_�l(f��)Փ���īI(xi��n)2ƪ
- �Ļ��z�a(ch��n)���o(h��)���P(gu��n)��Փ���īI(xi��n)5ƪ
- �������n�ý̌W(xu��)Փ�ķ���2ƪ
- ���е����̌W(xu��)3ƪՓ���x�}�����ą���
- �o�C���W(xu��)�̌W(xu��)Փ�ķ���2ƪ
- Ӌ��C���g(sh��)���F(xi��n)�������õ��о�Փ�ķ���2ƪ
- ����ʳƷ���b��Ⱦ��Σ��Փ�ķ���2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