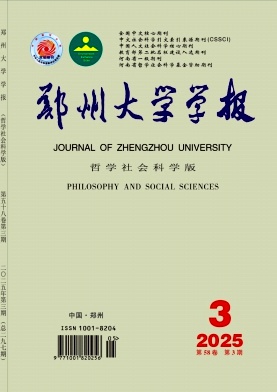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雜志投稿格式參考范文:考古學視野下唐代洛陽里坊市場研究
時間:
有關唐代洛陽城里坊數量自古以來多有爭議,有關此問題的研究目前仍集中在對文獻所載里坊名稱和數量的考辨上,而文獻闕載使隋唐洛陽城里坊建筑及形態問題學界幾無涉及。新中國成立后洛陽地區大量隋唐墓志的發掘出土,使一些不見文獻著錄的里坊名稱不斷出現,卻使里坊問題更加復雜;隋唐洛陽城不間斷的考古勘探及發掘工作,廓清了洛陽城的基本布局,明確了履道坊、寧人坊、政平坊、明教坊、溫柔坊、恭安坊、三市、官營磚瓦窯場的位置及其局部形態,為深化隋唐洛陽城里坊形態研究提供了可能。本文利用考古發現,對唐代洛陽城街道及里坊關系、里坊建筑及布局形態、洛陽三市及商人生活狀態等問題作以研究。不足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一、考古發現的唐代洛陽城街道、里坊
新中國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對隋唐洛陽城即開展有計劃的考古勘探及發掘工作。經過七十年不間斷的考古工作,現已基本明確了隋唐洛陽城的建筑布局,郭城、皇城、宮城位置及里坊區域也已清晰。尤其是上世紀 90 年代以來對寧人坊、履道坊、明教坊、溫柔坊、恭安坊、政平坊、三市的考古勘探發掘等,為了解唐洛陽城里坊建筑、形態及居民生活提供了新資料。
劉慶柱先生說:“(漢唐都城) 城門與道路相連,古代都城之中的道路形成都城的‘骨架’。道路一般是直的。方向為南北向或東西向,因而城內的道路將城內分割成‘棋盤格’ 式布局。不少都城的宮城、官署、里坊、市場等,按其性質分別置于各自‘棋盤格’ 中。” 因此唐洛陽里坊問題的考察,勢必要關照到城門、街道布局及其形態。文獻記載唐代洛陽城洛南里坊區有南北向街道 14 條、東西向街道 8 條,洛北里坊區有南北向街道 7 條、東西向街道 6 條。始于 1961 年的考古勘查確證洛南里坊區南北向街道 12 條、東西向街道 6 條,洛北里坊區南北向街道 4 條、東西向街道 3 條。這些街道不僅構成了唐洛陽城的公共交通網絡,而且也固定了城內里坊、市場的位置和形態。考古發現揭示,洛南里坊區的南北 12 街、東西 6 街構成 55 個坊,洛北里坊區的南北 4 街、東西 3 街構成了 9 個坊。唐代洛陽里坊呈方形、長方形,長寬略有不同,洛南里坊區 55 個坊規格在東西 500 - 580 米、南北 530 - 560 米之間,洛北里坊區探出的 9 坊規格在東西 380 - 500 米、南北 480 - 580 米之間。這與元《河南志》所記每坊東西南北各廣三百步相差較大。其余各坊由于其間街道遭到破壞,有關其形制和范圍大多無法知悉。
里坊內部的道路與郭城內的公共街道相連,共同構成城內縱橫交錯的交通網絡。
通過對定鼎門街、建春門街、長夏門街東第四街、東順城街、履道坊西坊間街道、定鼎門外東西向道路的考古發掘,通過對寧人坊、履道坊、明教坊、南市的鉆探發掘,可知郭城內直通諸城門及坊間的南北向和東西向公共大街布列整齊;里坊內的十字街、曲巷等直接或間接與坊外公共大街相通,共同構成洛陽城內的交通網絡。此外,里坊內部還有沿坊墻夾道、東西向巷曲的存在,它們與十字街一起構成里坊內部的道路系統。上述不同街道寬度不同,既是禮制的反映,也是街道承載不同交通流量的反映。
考古發現揭示唐洛陽城里坊內外各類道路車輛都可通行,里坊十字街及坊外道路上車轍的考古發現即為例證。定鼎門街因中軸線和御街地位不僅為一道三幅形制,而且三幅路面上車轍痕跡 (轍寬在 1.25 - 1.5 米之間) 明顯。建春門街、長夏門街、厚載門街、定鼎門外東西向街道路土上也發現明顯的車轍痕跡,同樣證明這些大街寬闊且都有車輛通行。寧人坊內十字街上也有車轍發現,說明坊內也是允許車輛通行的。
唐洛陽城大小渠溝依附街道縱橫交錯分布。
定鼎門街、永通門街、寧人坊和從政坊間街道、履道坊和集賢坊間道路等兩側都有水渠存在,寧人坊、溫柔坊、恭安坊、履道坊內十字街和其他東西向小路盡管較窄但其側也有小水溝設置。因河水泛濫淤積,溝渠寬度、深度在不同時期都有變化。考慮到洛陽城貨運通行和城市排水的需要,推測郭城內南北向、東西向主干大街及里坊內溝渠建設應有相同的規劃設計。多種街道寬度及排水設施的規劃建設,充分考慮、關照到城市生活及交通的多方需求,體現了唐代城市管理的制度化水平。
考古發現證實唐洛陽城的里坊布局以街道為準繩,道路決定了坊市的規劃布局,二者關系密切。郭城內南北、東西向寬闊筆直的夯土街道縱橫交錯形成棋盤狀格局,這些道路與坊內十字街相連通,不僅構成了規整的里坊區規劃骨架,還構成洛陽城內大街小巷復雜便利的交通網絡。郭城內縱橫道路之間以版筑夯土墻合圍的方形、長方形區域構成布局規整的里坊,從而形成一個個封閉的獨立空間。
二、唐代洛陽里坊建筑、布局形態
唐代洛陽城里坊內部布局及建筑形態文獻記載匱乏。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考古工作者對洛南里坊區的寧人坊、履道坊開展了大規模的考古鉆探和發掘,對明教坊、恭安坊、溫柔坊和南市開展了系統的考古勘探和局部考古發掘,目前正系統開展政平坊全面的考古發掘。考古發現反映盛唐前后洛陽里坊形態變化較大,且因其內部官宅及公共建筑 (官府機構、大型寺廟) 的有無而呈現出多樣化的建設布局形態。
據考古發現,唐洛陽城里坊四周由夯土版筑坊墻合圍,從而形成一個個封閉的獨立空間。坊墻寬度差別不大,墻基及墻體寬度一般在 2 米左右。寧人坊的考古發掘提供了坊墻的基本形態。據 2011 - 2013 年的勘探、發掘結果,寧人坊坊墻下挖基槽,基槽內填五花土,以 0.1 - 0.2 米夯層夯筑而成;四座坊門位于每面坊墻正中,寬 2.25 - 2.8 米的單門道結構坊門聯結坊內外的主要通道,坊門由墩臺和門道組成,墩臺與坊墻分別夯筑;南坊墻、東坊墻均為一次性夯筑而成,西坊墻有過二次夯筑現象,反映出不同時期坊墻修繕的歷史遺跡,可能為文獻記載中坊墻倒塌后修補所致。《全唐文》卷 267 載 (唐中宗時) 右補闕盧俌《對筑墻判》文:“洛陽縣申,界內坊墻因雨頹倒,比令修筑。坊人訴稱:皆合當面自筑。不伏,率坊內眾人共修。” 盧俌判:“坊人以東里北郭,則邑居各異;黔婁猗頓,乃家產不侔。奚事薄言,佇遵恒式;既資眾力,須順人心。垣高不可及肩,板筑何妨當面?” 《全唐文》卷 980 載《對筑墻判》文:“廣術頹墉,見銅駝之咫尺,仲尼數仞,無復及肩。” 這二則唐代判文都反映唐洛陽里坊修葺及 “垣高不可及肩” 的實際情況。當坊墻坍塌時,坊民要求 “當面自筑” 而不是由全體坊民共筑。但政府也有義務修繕倒塌坊墻,如《唐會要》卷八六載:“貞元四年二月敕,京城內莊宅使界諸街坊墻,有破壞,宜令取兩稅錢和雇工匠修筑,不得科斂民戶。” 寧人坊西墻早晚遺跡的發現即說明里坊續修的歷史事實,由此反映出唐代城市管理制度的完備。
坊門為單門道重樓結構。
坊門位于坊墻正中位置,外鄰坊外大街,內連坊內十字街。據《大業雜記》:“(洛水) 大堤南有民坊,坊各周四里,開四門,臨大街。門普為重樓,飾以丹粉。”《資治通鑒》卷 183:“《略記》: 三月辛未,密遣孟讓將二十余人夜入都郭,燒豐都市,比曉而去。癸未,密襲據都倉。乙亥,密部眾入自上春門,于宣仁門東街立柵而住。丙寅,燒上春門及街南北里門樓,火接宣仁門……” 坊門門樓式結構是明確的。史載洛陽里坊門有二、四歧說。韋述《兩京新記》有 “每坊…… 開十字街,四出趨門” 之說,《舊唐書・地理志》載洛陽里坊 “開東西二門”。可能較大的里坊開四門,洛河兩岸的里坊面積較小只開東西二門,與長安城皇城朱雀街兩側的四列三十六坊類似。坊門由坊正負責管理,全體坊民須經坊門出入,以鼓聲為令 “昏而閉,五更而啟”,并與城門的啟閉時間相一致,反映出濃厚的軍事管理性質。
從近年的考古發現看,唐代洛陽里坊及市場內不僅發現了十字街,還有沿坊墻夾道和東西向小街道即巷曲的發現,其寬度應為 3 - 4 米,而且十字街和東西向道路一側還往往有水溝分布。目前在履道坊、寧人坊、明教坊、政平坊、溫柔坊、恭安坊、南市等發現這些巷曲殘寬不一。如履道坊西坊墻北段與白居易宅院院墻之間發現了寬 2.7 米的沿坊墻夾道;十字街南北街與南半部兩條寬 4.2 米的東西向小街垂直相交,交叉路口邊沿處的路土呈圓弧形,路面上有大量碎瓦片和河卵石。這說明履道坊內既開有寬 13.4 米的十字街作為里坊內的主要通道,同時南半部還開有東西向小街道作為十字街的補充。該坊內一縱 (十字街中的南北向街)、三橫 (其一為十字街中的東西向者) 街道分布,輔以沿坊墻夾道,構成了里坊內部的交通網。因白居易宅院位于履道坊的西北隅,可能占有該坊的四分之一地域,因此該坊北半部至今未發現東西向小街道。這些東西向小街道及排水溝也具有規劃坊內居民住宅空間的作用。
坊內這些東西向小街道及沿坊墻夾道應該就是文獻記載中的 “巷”“曲”“靜曲”。
《異聞錄》:“京兆韋道安,大足年中于洛陽早出,至慈惠里西門。由里門循墻 (注:沿坊墻夾道) 而南行百余步,有朱扉西向,扣之,有朱衣官乘道安以大馬,與之聯轡出慈惠西門,由正街西南,自通利街東行,出建春門。” 積善坊中有南曲、李及宅。《唐兩京城坊考》云 “(李) 及云往南曲婦家將息” 即可證明。通利坊中有 “靜曲”。《唐兩京城坊考校補記》:“韋丹、胡盧生至通利坊靜曲幽巷一小門入,數十步復一版門,又十余步乃見大門,有人稱元睿之,流連竟日。” 唐長安城也有相似記載。《太平廣記》卷 484《李娃傳》載:“(長安鄭生) 至安邑 (里) 東門,循理 (應作” 里 “) 垣北轉第七八,有一門獨啟左扉,即娃之第也。” 唐長安勝業坊北街槐樹北門有短曲。“王超過勝業坊北街,有三女子于道側槐樹下蹴鞠,居北坊門短曲。” 這些記載表明唐東、西兩京坊內沿坊墻四周有夾道及小巷道的存在。元代李好文《長安志圖》中唐長安《一坊之制圖》和《皇城南坊之制圖》中,也繪有此類夾道。從沿坊墻夾道和十字街一起出現于圖中看,當時人們是將其與十字街一起視為里坊內部道路的。
上面依據考古發掘及鉆探結果分析歸納了唐代洛陽里坊的建筑及內部規劃布局情況,明晰了圍合的坊墻、單門道重樓坊門、坊內道路系統及溝渠的分布設置。“洛陽第宅,多是武后、中宗時居東都所立。” 隋至初唐時期,由于政治中心在關中,洛陽城中官署及貴族府邸相對較少,因此考古發現的坊內十字街、四出趨門及均衡布局的東西向小街道 (巷、曲) 等規劃齊整,反映的是隋至初唐時期洛陽里坊內部以東西向并列民居建制為主的布局規劃,如寧人坊。武后盛唐時期,隨著洛陽政治地位上升、城市經濟發展及人口日繁,政府機構、官宅府邸增多并與寺觀等公共建筑一起紛紛擴建搶占里坊空間,一些里坊十字街及東西向小街被占壓,侵街現象隨之發生,里坊內部形態也開始多樣化。履道坊因白居易宅第、政平坊因太平公主宅第和國子監等存在就提供了盛唐時期洛陽里坊的另一種形態。
據考古發掘,寧人坊平面呈南北長方形,南北長 527、東西寬 462 米,與上世紀 60 年代考古鉆探所得里坊規模相當,也與《河南志》記載相同。
考古發現坊內街道兩側根據需要設排水溝,在十字街北側距北坊墻 98 米處還發現一條東西向道路及路側水溝,反映出晚唐寧人坊中除一條南北街道外還有兩條東西向街道均衡布局。房屋基址沿道路東西向有序排列,說明當時里坊中居民宅院是依道路為參照物規劃布局的。在寧人坊東南部還發現了夯土臺基、成排分布的磉墩等建筑基址。該建筑基址座北朝南,上距地表深 1.2 - 1.3、東西殘長 5.3、南北殘寬 1.6 米。在建筑基址地面上清理出殘破的佛教造像 6 尊及佛教經幢。據文獻記載,寧人坊中有龍興寺。這個基址和佛教造像是否與唐龍興寺有關,還有待新的考古發現證實。但寧人坊的考古發現提供了唐洛陽城典型的平民里坊規劃建筑特征,此坊與明教坊、溫柔坊、從政坊規劃布局基本相同。
考古發掘及勘探證明,唐代履道坊位于定鼎門街東第八坊,遺址主要有西側的坊間道路、古伊水渠、履道坊坊墻、白居易宅院等遺跡。在履道坊西部發現了西坊墻與白居易宅院西墻間距 2.7 米的夾道,夾道上發現有白灰墻皮、粉紅墻皮、碎瓷片、建筑構件等。白居易宅院位于履道坊西北隅,其宅院形態、院墻以及南園的釀酒遺跡、水溝、池沼等都已明確。據建筑遺跡可復原其宅第為一座北朝南、前后兩進庭院的組合建筑群:前庭院 (南部) 由門房、院落組成;后庭院 (北部) 為組合建筑群,北為上房,中部有廳,上房和中廳之間有東西回廊和東西廂房合圍。前庭院呈長方形,東西殘長 30 米,南北殘寬 16.9 米;后庭院由東西回廊和東西廂房圍合,平面呈 “工” 字形,南部東西長 19.5 米、南北寬 5.3 米,中部東西長 13.2 米、南北寬 10.5 米,北部東西殘長 17.38 米、南北殘寬 1.7 米。南園和西園為白居易宅院園林所在,南園中有面積達 3300 平方米的湖面。其詩文描寫園林中因水、橋、竹林、池館的存在使其宅院 “有林泉之致” 。南園中除有釀酒作坊、池沼外,還應有白氏家族禮佛場所,因為在此區域發現有鐫刻 “唐大和九年”“開國男白居易造此佛頂尊勝大悲” “唐大和九年…… 心陀羅尼” 等銘文的石質殘陀羅尼經幢,此外還有許多與佛教有關的殘存石碑銘文如 “渡群生”“身任真空”“海之因緣” 等字句。另外在遺址西南部宋代文化層之下的一個灶坑中出土刻有 “景祐四年” “在當時白” 的殘碎碑刻 32 塊。石經幢的考古發現證明白居易晚年與佛教關系密切。這些遺物正是白居易宅院在宋代變為大十字寺院的確切證據,同時也證明履道坊西北隅確為白氏宅院所在。另外,通過對考古發掘報告中提供的白居易宅院遺跡到南園淤土范圍的數據計算,可知南北達 160 米。考古發現白居易宅院的地理位置、規模、布局及宅院內的建筑等,與白居易有關詩文可相互印證,因此發掘者推測白居易宅院占據履道坊的整個西北部是符合歷史實際的。
新發現的政平坊位于定鼎門街東第一街,西鄰宜人坊,東接敦行坊,南北接樂和、修行坊。里坊遺址為長方形,南北長 533.6、東西寬 464.6 米,坊內的 “丁” 字形道路將里坊分為獨立的西半坊及東半坊的東南區和東北區三部分。據文獻記載,此坊內有唐代孔廟、國子監、太平公主宅等建筑。從考古發現的建筑基址看,發掘者推斷西半坊為一大型宅院,宅院南半部為園林區、北半部為庭院區。庭院為中軸對稱布局,東西共三路,中軸線上自南向北分布的五座大型夯土臺基對應五進建筑,并有墻 (或廊) 圍合,推測為太平公主的宅院。由于太平公主府邸宏闊,占據西半坊而導致十字街東西街部分被侵占。
三、三市及以職業劃分居住區域的商人形象
史載隋唐洛陽有北市、南市、西市三個集中的市場,但三市存續時間不一。洛陽三市是專門的商貿之區、繁華之地,散布于郭城內西、北、南部里坊區且都與運河漕運系統相通,既便于商品物資運輸,且分散布局也便利城內居民日常生活。1960 - 1965 年考古工作者曾對三市做過勘查,并結合文獻記載確定了三市位置。2004 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隋唐洛陽工作站等曾對南市做過局部考古鉆探。但由于文獻缺載和遺址破壞嚴重,三市內部空間布局及興廢沿革并不明朗。不過《唐兩京城坊考》等文獻關于東、西兩京市場不加區分的一體描述及共時性歷史存在等,反映出唐洛陽、長安市場規劃布局的一致性,考古發現的唐洛陽商人墓志也從另一側面反映了洛陽市場的經營和布局情況。
據文獻記載和考古鉆探,南市位于長夏門街東側,其南與嘉善坊、北與慈惠坊相鄰,遺址在今茹家凹東約 200 米處。隋稱南市為豐都市且占二坊之地。《大業雜記》載:“豐都市,周八里,通門十二,其內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 四壁有四百余店,…… 珍奇山積。” 唐改稱南市,為三市之中規模最大者。十二門之制反映了南市中三縱三橫街道的存在及其將南市劃分為十六個區域、市場內四通八達的歷史事實。唐貞觀九年以后南市踞一坊半地,有邸三百一十二區,資貨一百行,其中有書肆。《太平御覽》和《河南志》對南市也有相似記載。2004 年的考古鉆探在南市南部發現了兩條南北向平行的道路(東西寬 3 - 5 米)、位于西部呈南北向的夯土西坊墻(東西寬 1 - 2 米)等遺跡和鐵渣、銅塊、銅錢等遺物。市場交易、店鋪分布等繁雜情況決定了市場中道路網的復雜,此種街道布局形態與隋唐長安城東、西市的布局基本一致。
北市位于洛北里坊區,遺址位于今洛陽市林校一帶。其地東臨安喜門街,南與景行坊、北與敦厚坊相鄰。北市隋唐時期曾經過由坊改市、再由市改坊的變遷過程,即隋至唐初稱臨德坊,唐顯慶年間改為北市,晚唐時期廢市,其地分為南北二部分,南部改為北市坊、北部稱鄰德坊。北市商業繁榮,出現了不少工商大賈,其中還有許多中亞商人,他們都是經絲綢之路來洛陽經商的,在龍門石窟的造像題記中留下了歷史蹤跡。
西市位于洛南里坊區西南隅,遺址在今洛陽市洛龍區曹屯和董莊之間。西市同樣經歷了由坊為市和由市而坊的變化過程。如西市初稱固本坊,隋稱 “南市”(又曰 “大同”),隋末唐初在此置西市,唐開元十三年罷市。由于西市存在時間較短,故唐洛陽城又有二市之說。其東臨厚載門街,南即郭城南墻,北與廣利坊相鄰,南有通濟渠自西向東貫通,武周大足年間又在其西南開鑿新潭以通諸州租船,以利工商貿易的發展。因渠水泛濫致西市保存很差,加之存續時間短及考古工作不充分,相關資料很少。
由于洛陽城疊壓沿用及后世破壞嚴重,目前洛陽三市內部的空間布局并不明確。但新中國成立后唐長安西市經過系統鉆探和考古發掘,我們可借以豐富唐洛陽的市場情況。長安西市位于郭城內皇城西南,永安渠自南往北流經西市的東部。據考古鉆探,唐長安西市呈長方形,實測南北 1031、東西 927 米,面積 0.96 平方公里。西市的北、東坊墻夯筑而成,寬 4 米。文獻載:“(西市)南北占兩坊之地,東西南北各 600 步,四面各開二門,定四面街各廣百步。” 考古發現唐長安西市內有寬 16 米的南北向和東西向的平行街道各兩條,四街縱橫交叉成井字形,將整個西市劃分成 9 個長方形區域(應與唐洛陽南市相同)。井字形大街上發現有車轍痕跡,路兩側各有寬 30 厘米的明溝用于排水,明溝外側又有 1 米寬的人行道。另外,在市四周圍墻內側也有寬 14 米的順墻街道。市署基址呈長方形,位于市中央部分,東西長 295、南北寬 330 米。參與西市考古發掘與研究的何歲利先生認為,西市各區域內還有巷、曲的規劃布局,巷、曲與井字形主干道共同構成市場內的交通路線。市場內的房屋均沿井字形街道和眾多巷道分布,房屋面闊 4 - 10 米、進深 3 米多,從位置來看應是臨街商鋪。2006、2008、2016 年的發掘證實這些臨街開設的店鋪都是前為售賣經營的店鋪、后為加工制作的作坊,構成了生產制造、售賣流通一條龍的生產經營格局。根據不同建筑基址出土的不同文物,宿白先生認為唐長安西市是同類商鋪集中經營的,其中南大街東端街南為飲食業所在,南大街中部街南為珠寶商的店鋪,北大街中部南側為鐵器、石刻店鋪匯集區,西大街中部可能為兇肆所在。據近年的考古新發現,何歲利先生認為,西市東北十字街周圍及其東道路北側為飲食業所在,南、北大街中段之間區域為骨器店肆,北大街中段道路南側為唐三彩玩具、樂器、骨器店肆,可能還有麩行、食貨行,西大街近西北十字街的路東側為陶器店肆,南大街西端路南側為骨器店肆。骨器、玩具、樂器、陶器店肆也都是臨街開店、店后為作坊。市場內同類商貿集中經營區劃明確,這種經營格局說明唐長安西市不僅是商品交換與貿易的集散地,還是集加工、娛樂(酒肆等)、漕運等于一體的大型商業綜合體。
隋唐東、西兩京市場周圍一些里坊名稱也具有顯著的工商逐利致富含義。如緊鄰洛陽西市的通濟坊、廣利坊,緊鄰北市的豐財坊、殖業坊,緊鄰南市的通利坊等,因此可推測當時居于此坊的居民多以工商為業,反映了唐代等級制度及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的社會現實。近年考古發掘出土的唐代東都洛陽商人墓志也印證了這一推斷,并且為研究東都市場的經營情況提供了珍貴資料。唐代喪葬行用墓志。“墓志之傳世者,莫盛于李唐。雖屠沽走卒,亦有薶銘。” 近年發現的商賈劉善寂墓志、張從古墓志、王進墓志、張詮墓志、李和墓志、司馬元禮墓志等,他們都居住在洛陽南市、北市周圍諸坊中。無獨有偶,據洛陽發現的少數民族墓志,西域胡商等域外民族也多聚居于洛陽南市、北市周圍的里坊中。他們都因善于經商貿易而聞名。延載元年(694 年),武三思率四夷酋長于端門南用銅鐵鑄天樞以鎮四方,這座高 90 尺的標志性建筑就是 “蕃客胡商聚錢百萬億所成”。洛陽商人之眾及商業繁榮由此可見一斑。
商人與市場、工商業聯系緊密,出土墓志反映了唐洛陽商人的經商情況。前述司馬元禮墓志記述了他的經商之道:“總四方會,據一國沖,致天下人,聚域中貨者,曷若旗亭乎!贊賓主禮,取談笑資,成骨肉親,結金蘭分者,曷若玉醴乎!” 其中多處涉及洛陽南市的布局情況:“(司馬元禮)既而乃議卜筑,不避喧湫,得齊人攫金之所,石家販鐵之地,列其廣肆,誓將老焉。” 為了把握商機搶占市場,司馬元禮選擇市場中狹隘喧囂的黃金地段經營私家商鋪經營逐利。旗亭即市樓,是古代觀察、管理集市貿易事務的機構,一般修建于市場中心,因其上立旗而得名。《洛陽伽藍記》云:“陽渠北有建陽里,里有土臺,高三丈,上有二精舍。趙逸云:‘此臺是中朝旗亭也,上有二層樓,懸鼓擊之以罷市。’”
據洛陽唐代商賈墓志銘文,這些商人都居住于市場周圍的里坊中。如王進、司馬元禮居住在東臨南市的福善坊,劉善寂居住在西臨南市的永泰坊,李和居住在西臨南市的臨阛坊,張從古居住在南臨南市的樂城坊;張詮居住在西南臨北市的殖業坊。近市而居便于邸肆經營取利,他們都是略有資本的小商人,既有酒商也有藥商。洛陽北市商人以客商為主體,他們頗具勢力的行會名稱如 “北市彩帛行”“北市絲行”“北市香行” 以及商人姓名等,鐫刻在龍門石窟造像題記中,反映了他們熱衷于開鑿龍門石窟的宗教活動,顯示出鮮明的群體特性。
文獻記載及考古發現揭示,唐洛陽商人相對集中地居住在市場周圍,市場內規劃 “井” 字形街道及巷道以利經貿活動;市場內居中的旗亭不僅是市場的監督管理機構,其內還設置酒肆;按經營種類分區設置的列肆商貿區在市場中各臨大小街道,前為店鋪、后為生產作坊的前店后坊形式構成市場的基本格局,功能區劃明確。
四、余論
考古發現的不完全和文獻的闕載使唐洛陽城坊市形態的探討還需要新資料的補充,本文試就下面兩個問題略述己見以期學界關注。
關于里坊園宅的分配與規劃:隋唐洛陽城的修建是經過事先周密規劃的,里坊及其內部居民園宅布局、大小規定也應是有規可循的。隋代百姓園宅規劃已上升至法律層面。《通典》卷二載:“(隋代規定)其園宅率三口給一畝,奴婢則五口給一畝。” 唐代繼之,“應給園宅地者,良口三口以下給一畝,每三口加一畝,賤口五口給一畝,每五口加一畝,并不入永業口分之限。其京城及州郡縣郭下園宅,不在此例”。唐代京城及州郡縣城居民園宅劃分雖于史無證,但后周大梁城建設為此提供了一定線索。后周世宗因 “大梁城中民侵街衢為舍,通大車者蓋寡” 而整修大梁城時,除 “遷墳墓于標外”,還規定 “其標識內,候宮中擘畫,定街巷、軍營、倉場、諸司公廨院務了,即任百姓營造”。修建計劃中的大梁城 “街道闊五十步者,許兩邊人戶,各于五步內,取得種樹掘井,修蓋涼棚;其三十步以下至二十五步者,各與三步,其次有差” 。這應該是后周針對普通市民宅院范圍的基本規定,而且也是坊市崩潰、開放式街巷出現后的城市新形態。北宋東京開封府延續了周世宗對汴梁城的改建。延至元代,元大都居民的園宅分配也有標準。元大都建成后,曾下詔 “舊城(即金中都)居民之遷京城者,以貲高及居職者為先,仍定制以地八畝為一分;其或地過八畝及力不能作室者,皆不得冒據” 。雖然城市居民住宅建筑樣式是否統一目前難以究明,但后周大梁城、元大都都反映了城市建設、居民生活用地是有預先規劃和分配方案的,這應該與唐代洛陽城里坊區域的考古發現是一脈相承的。
既然里坊內部住宅占地有一定的面積標準規定,那么建設時就需要先明確空間劃分標識。前已述及,城門、街道是城市規劃的骨架,那么坊內十字街和沿坊墻夾道、巷曲等就成為劃分坊內居民園宅的依據而有序而行。傅熹年先生指出,隋大興城營建時,宮室、官署和一些官員的府邸由將作監主持修建,坊內住宅則是劃定地界后由坊民自建。那么當時必定有撥地標準和住宅等第限制,這樣才能統籌公私一體化建設而依序行事。這與后周世宗修大梁城時居民區 “定街巷、軍營、倉場、諸司公廨院務了,即任百姓營造” 是相同的措施。而根據洛陽城的考古發現,可推測唐洛陽城坊內居宅、各類小路也應該是事先規劃、有明確布局規則的。
2. 關于侵街問題:盛唐時期出現的侵街行為在考古發現中已有反映。隋至初唐,洛陽城的里坊應以規整的四面正中開門、坊內開十字街及東西向小街道形制為主,居民宅院依街道整齊布局。自盛唐開始,由于東西兩京城市人口日繁,加之豪門貴族府第擴建、大興兼并,侵街行為日劇,《唐律疏議》中對侵街行為的嚴懲從一個側面證明此問題的嚴重。高宗永徽年間(650 - 655 年)《唐律疏議》中即有 “諸侵巷街、阡陌者,杖七十” 的規定。《唐會要》卷八六也多有記載,如唐代宗大歷二年(767 年)五月詔令 “諸坊市街曲,有侵街打墻、接檐造舍等,先處分一切不許,并令毀拆”。考古發現也證實唐洛陽城里坊中存在大量侵街造舍之事,如寧人坊西坊墻、西坊門、南坊門等處唐代晚期地層下發現有疊壓于這些建筑遺跡之上的道路、卵石區、建筑區、灰坑等,疊壓于坊墻、坊門建筑之上的道路上還有密集的車轍痕跡,這些考古發現為晚唐侵街破壞里坊建筑的生活遺跡。唐長安安定坊的考古發現也提供了相同的證據。從地層堆積看,安定坊內的十字街在唐初或隋代建大興城之初即已形成,唐初仍保存其原來形制;盛唐時期,東西街道的南北兩側 0.6 - 0.7 米處各有一道與街平行的東西向版筑夯土墻基遺跡,這兩道墻將十字街的南北向街道切斷。這是盛唐時期豪門貴族府第擴建侵街的明證。到晚唐之際,貴族大宅擴張更移之勢更甚,在版筑坊墻址之上發現晚唐堆積的地面及水井遺址可為證據。
孫 凱,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202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