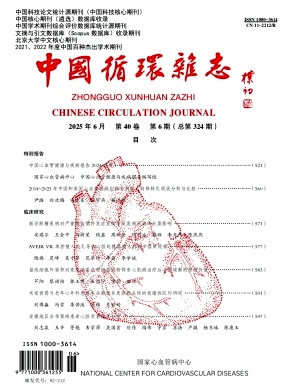中國循環雜志投稿格式參考范文: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相關心肌炎的臨床診治進展
時間:
引言
免疫檢查點抑制劑(ICI)是一種通過抑制免疫檢查點活性恢復并提高 T 淋巴細胞特異性識別及殺死腫瘤細胞能力的單克隆抗體,近十余年來被廣泛用于臨床。根據治療靶點,ICI 分為三大類,即細胞毒性 T 淋巴細胞相關抗原 4(CTLA-4)抑制劑、程序性細胞死亡蛋白 - 1(PD-1)抑制劑及 PD-1 配體(PD-L1)抑制劑。
ICI 可引發嚴重程度不一的免疫相關不良事件(irAE),其中 ICI 相關心肌炎(ICI-M)是一種起病急、癥狀重、進展迅速、發生率低但死亡率高的 irAE,常常首診于急診科,急診醫師需對其進行快速識別與緊急處理。但目前 ICI-M 的相關研究有限,臨床認知相對缺乏。本文對近年來 ICI-M 的流行病學、發病機制、臨床表現、輔助檢查、診斷標準及治療等方面的研究進展進行綜述,以期提高臨床醫師對 ICI-M 的診治能力,從而改善患者預后。
1 ICI-M 的流行病學
一項納入 4751 例 ICI 治療相關心臟毒性患者的 Meta 分析顯示,心臟相關 irAE 發生率為 1.3%,其中心肌炎最常見,占 50.8%。據報道,ICI-M 死亡率為 20%~50%,居所有 irAE 首位。我國研究顯示,ICI-M 發病率約為 1%。
隨著 ICI 適應證的不斷拓展以及臨床醫師對 ICI-M 辨別能力的提升,ICI-M 發病率可能會逐漸升高。
2 ICI-M 的潛在發病機制
2.1 T 細胞介導的免疫反應
有研究顯示,T 細胞介導的免疫反應是 ICI-M 發病的關鍵。生理狀態下,CTLA-4 和 PD-1 介導正常心肌細胞產生免疫耐受而免于被攻擊。研究發現大多數 ICI-M 患者的心肌中有大量 T 淋巴細胞浸潤。CTLA-4 和 PD-1 基因敲除小鼠可發生自身免疫性心肌炎或心肌病,死亡率高。
動物研究表明,心臟 α- 肌球蛋白的自身反應性 T 細胞在 ICI-M 的發病中起關鍵作用,暴發性心肌炎小鼠中 α- 肌球蛋白擴增的 T 細胞抗原受體(TCR)與 ICI-M 患者的心肌細胞、骨骼肌細胞共享 TCR 克隆型,說明 α- 肌球蛋白可能是 ICI-M 患者的一個重要的自身抗原。研究還發現,用抗 CD8 + 耗竭的抗體治療,可提高 Pdcd1⁻/⁻Ctla4⁺/⁻小鼠的存活率;此外,將有 ICI-M 的供體小鼠的免疫細胞過繼轉移至受體小鼠,但不消耗 CD8 + 細胞,可引起致死性心肌炎,說明心肌炎的發生需要 CD8+T 細胞介導。
2.2 共同抗原
心肌細胞和腫瘤細胞有共同的抗原是 ICI-M 的發病機制之一。Johnson 等發現,接受 ICI 治療的患者發生自身免疫性心肌炎后,心肌、骨骼肌、腫瘤細胞表達相同的 T 淋巴細胞,說明 ICI 在激活細胞毒性 T 淋巴細胞攻擊腫瘤細胞的同時,也影響心肌和骨骼肌細胞,導致自身免疫性心肌炎和肌炎。
2.3 心肌損傷
目前認為,潛在心肌損傷亦是 ICI-M 的發病原因之一。腫瘤患者手術或放化療后可能會誘發心肌損傷,受損心肌釋放的自身抗原與反應性 B 細胞產生的自身抗體結合,產生抗體依賴的細胞介導的毒性作用,導致心肌細胞壞死和炎癥反應。受損的心肌組織進一步釋放損傷相關分子模式(DAMP),激活機體自身抗原的免疫應答,DAMP 和其他組織的自身抗原產生交叉反應,進一步加重心肌損傷。
2.4 分子機制
2.4.1 心肌炎癥:有臨床前模型研究發現,接受 PD-1 和 CTLA-4 抑制劑治療的小鼠通過增加核因子 -κB(NF-κB)、NOD 樣受體熱蛋白結構域相關蛋白 3(NLRP3)炎癥體和髓樣分化因子 88(MyD88)的激活,誘導心肌組織促炎表型。CTLA-4 抑制劑也可使促炎因子增加,如干擾素 γ(IFN-γ)、腫瘤壞死因子 α(TNF-α)、白細胞介素(IL)-2、IL-17A 等,進而影響心肌細胞代謝,導致死亡率增加。CTLA-4 抑制劑還可誘導內皮因子激活,增加主動脈內皮中細胞間粘附分子(ICAM)-1 的表達,而 ICAM-1 的減少可改善心臟炎癥反應及心肌收縮功能障礙。動物實驗已證實,PD-1/PD-L1 抑制劑可誘導多種促炎因子(如 TNF-α、IL-1β)的表達,也可通過增加 IFN-γ 的表達和減少磷酸化蛋白激酶 B(Akt)的表達,促進心肌細胞凋亡,誘導心肌炎癥。
2.4.2 心肌纖維化:Quagliariello 等發現,CTLA-4 抑制劑通過調節半乳糖凝集素 - 3、原膠原蛋白 1-α 和基質金屬蛋白酶 9 的表達,導致心肌纖維化。Zhang 等發現,PD-1 表達較低的患者中轉化生長因子 β1(TGF-β1)濃度增加,TGF-β1 在心肌纖維化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PD-1 抑制劑還可促進心肌細胞中促纖維化細胞因子的表達,在心肌纖維化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
2.5 氧化應激
T 細胞的激活可導致活性氧自由基的產生增加,導致氧化應激;Aboelella 等的研究已證實,這與 PD-1/PD-L1 抑制劑誘導的心臟毒性相關。PD-1 抑制劑誘導的氧化應激與 IFN-γ 陽性巨噬細胞的增加相關。而 IFN-γ 可通過抑制磷脂酰肌醇 3 激酶(PI3K)/Akt/ 核因子紅細胞 2 相關因子 2(Nrf2)途徑誘導活性氧產生,導致抗氧化活性降低。
3 ICI-M 的臨床表現
ICI-M 初期臨床表現為心悸、乏力、呼吸急促等,因缺乏特異性常被忽視。隨著疾病進展,患者可出現端坐呼吸、水腫等心力衰竭表現及心包炎、心包積液等一系列臨床綜合征,甚至出現持續性室性心動過速、暴發性心肌炎、心原性休克、猝死等危及生命的情況。ICI-M 發生的中位時間為 ICI 用藥后 27~65 d,約三分之二的患者在接受 1~2 次治療后即出現臨床癥狀。此外,ICI-M 常合并肌炎、重癥肌無力、肝炎、甲狀腺炎等其他 irAE。
4 ICI-M 的輔助檢查
4.1 心肌損傷標志物:研究顯示,46%~94% 的 ICI-M 患者心肌肌鈣蛋白(cTn)T 或 cTnI 水平升高,其中 cTnI 對心肌損傷更為特異,而 cTnT 升高與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發生風險高相關。66%~100% 的 ICI-M 患者 B 型利鈉肽(BNP)或 N 末端 B 型利鈉肽原(NT-proBNP)水平升高。
4.2 心電圖:約 90% 的 ICI-M 患者出現心電圖異常,但缺乏特異性表現,可表現為竇性心動過緩或過速、頻發早搏、室上性心動過速、房室阻滯或室內傳導延遲等;病情嚴重者可表現為完全性房室阻滯、室性心動過速、心室顫動、心臟停搏等;其中相對特異性的表現為房室阻滯,發生率為 39%。
4.3 經胸超聲心動圖(TTE):TTE 檢查提示,約一半的 ICI-M 患者左心室射血分數(LVEF)下降。左心室整體縱向應變(GLS)是診斷 ICI-M 特異性較高的指標之一,無論 LVEF 是否正常,GLS 較低或 GLS 下降幅度較大的患者發生 MACE 的風險更高。一項回顧性研究顯示,ICI-M 患者 GLS 下降與高敏 cTnI 升高相關。2022 年歐洲心臟病學會(ESC)腫瘤心臟病指南建議,所有接受 ICI 治療及基線 cTn 水平升高的患者均應行 TTE 檢查評估 LVEF 和 GLS。
4.4 心臟磁共振成像(CMR):CMR 是診斷 ICI-M 的首選檢查方法,可識別出心肌炎癥、水腫、壞死及纖維化等心肌炎組織病理學改變。ICI-M 的具體 CMR 特征尚未完全明確,2022 年 ESC 腫瘤心臟病指南推薦使用 2018 年改良 Lake Louise 診斷標準協助診斷。有研究發現,ICI-M 患者中 CMR 水腫比(ER)升高的發生率明顯低于其他急性心肌炎患者,而 T2 mapping 陽性率高達 92%,認為 T2 mapping 可能是檢測 ICI-M 的可靠指標。另一項研究則顯示,43% 的 ICI-M 患者 T2 值增高,認為 ICI-M 的病理生理機制可能是持續的心肌炎癥和纖維化,而不是心肌水腫。
Cadour 等的研究顯示,ICI-M 患者釓延遲強化(LGE)發生率更高,LGE 可反映不可逆的心肌壞死和纖維化;ICI-M 的 LGE 以累及室間隔和心肌中層為主,而病毒性心肌炎以累及側壁和心外膜下為主。研究顯示,ICI-M 患者中 LGE 檢出率為 23%~75%,不同研究差異較大可能與患者出現癥狀至 CMR 檢查的間隔時間相關,隨著間隔時間延長,檢出率增高。
近期一項 Meta 分析顯示,發生 MACE 的 ICI-M 患者中 LGE 檢出率高于無 MACE 的患者,前者 T1 值更高,LVEF 更低,T2 值與 MACE 無關,故認為 CMR 的 LGE、T1 值和 LVEF 具有潛在的預后價值。
4.5 心內膜下心肌活檢(EMB):EMB 是確診心肌炎的金標準,特異性較高,心肌炎定性診斷需滿足 Dallas 標準。有研究顯示,ICI-M 急性期心肌組織形態在符合心肌炎的同時,巨噬細胞數量也高于淋巴細胞,這與病毒性心肌炎不同,而與巨細胞性心肌炎相似。ICI-M 與 IFN-γ 誘導的炎癥巨噬細胞擴增相關。高度疑診 ICI-M 或經積極治療效果欠佳時可考慮行 EMB,但因其有創而不推薦作為一線檢查。
5 ICI-M 的診斷標準、嚴重程度分層及恢復評估
ICI-M 的診斷標準尚不統一,通常是排除性診斷。2019 年 Bonaca 等首次提出 ICI-M 的定義,旨在識別臨床試驗中的心肌炎,并將其分為明確的心肌炎、可能性較大的心肌炎、有可能的心肌炎;根據病情嚴重程度,又分為暴發性心肌炎、有臨床意義的非暴發性心肌炎、亞臨床心肌炎。
2022 年初國際腫瘤心臟病學會(IC-OS)提出適用于臨床的 ICI-M 診斷標準,將 cTn 水平升高作為臨床診斷的必要條件,即在除外急性冠狀動脈綜合征和急性感染性心肌炎后,cTn 水平升高加上 1 條主要診斷標準或 2 條次要診斷標準,可診斷 ICI-M;IC-OS 對 ICI-M 嚴重程度的分層在 Bonaca 等的基礎上,增加了激素抵抗型心肌炎。2022 年 ESC 腫瘤心臟病指南與 IC-OS 提出的上述診斷標準一致,但去除了亞臨床心肌炎的診斷標準。然而,對于不符合活檢標準的患者,IC-OS 提出的 ICI-M 診斷標準并未解決其診斷問題。2022 年 Thuny 等修訂了 IC-OS 的診斷標準,并增加病理活檢僅可見炎癥細胞浸潤但無心肌細胞損傷作為次要標準之一。
6 ICI-M 的治療
ICI-M 的治療主要包括停用 ICI、使用糖皮質激素及對癥支持治療。危重癥 ICI-M 患者病情進展快,預后極差,應采取強化免疫抑制治療,若條件允許,應及時給予血漿置換和(或)生命支持等治療。
6.1 一線治療:糖皮質激素是治療 ICI-M 的一線用藥,但目前其起始劑量及應用時機、減量及停藥的最佳方案尚不統一。有研究顯示,以較高的初始劑量(甲潑尼龍或其他等效藥物 500~1000 mg/d)及較早(起病 24 h 內)應用糖皮質激素與良好預后相關。一旦診斷暴發性或非暴發性 ICI-M,均應盡早啟動甲潑尼龍或其他等效藥物(前 3~5 d,500~1000 mg/d,靜脈注射)治療,從而降低 MACE 發生風險。若病情好轉(cTn 在 24~72 h 內較峰值下降 > 50%,左心室功能障礙、房室阻滯及其他心律失常改善),建議改為口服潑尼松龍(起始劑量每天 1 mg/kg,最高 80 mg/d)。逐漸減量停藥的最佳方案尚不明確,但可通過監測臨床癥狀、cTn 及心電圖變化,逐周減少潑尼松龍劑量(常用方案為每周減 10 mg)。當潑尼松龍劑量減少至 20 mg/d 時,需重新評估左心室功能和 cTn 水平;若病情允許,隨后潑尼松龍每周減 5 mg,至 5 mg/d 后,每周減 1 mg。
6.2 二線治療:靜脈應用甲潑尼龍或其他等效藥物聯合其他心臟支持治療 3 d 后,若 cTn 水平較峰值下降≤50% 和(或)房室阻滯、室性心律失常、左心室功能障礙未持續性改善,考慮診斷激素抵抗型 ICI-M,需強化免疫抑制方案或二線免疫抑制治療,包括化學藥物(嗎替麥考酚酯)、靶向藥物(托法替布)、生物制劑(如抗胸腺細胞球蛋白、阿侖單抗、托珠單抗、阿巴西普、丙種球蛋白)及中成藥(西紅花總苷片),以改善患者的臨床癥狀及縮短康復時間。
Salem 等發現,Janus 激酶 2(JAK2)抑制劑魯索利替尼可增強阿巴西普的臨床療效,應用機械通氣、大劑量阿巴西普和魯索利替尼結合循環單核細胞 CD86 受體占有率監測,可將 ICI-M 的死亡率降至 3%。近期研究發現,補體抑制劑依庫珠單抗有望成為肌無力 - 肌炎 - 心肌炎重疊患者的治療策略之一。目前免疫抑制劑治療 ICI-M 的證據相對缺乏,需根據患者的實際臨床情況和用藥經驗制定個體化的治療方案。
在激素抵抗型 ICI-M 患者中,對于強化免疫抑制方案或二線免疫抑制方案療效不佳且病情進展合并血液動力學不穩定、難治性心力衰竭、心原性休克的暴發性心肌炎患者,《中國成人心肌炎臨床診斷與治療指南 2024》推薦立即轉至監護病房,盡早給予機械循環等生命支持治療;若出現低血壓(收縮壓 < 90 mmHg 或較基礎血壓降低 30 mmHg,1 mmHg=0.133 kPa)、心率增快等早期休克表現,推薦應用主動脈內球囊反搏(IABP)治療,若循環仍不能得到充分恢復或出現心臟驟停需心肺復蘇時,建議立即啟用 ECMO 聯合 IABP 治療,并盡早評估心臟移植手術指征;若患者出現呼吸急促 / 窘迫、呼吸頻率快或呼吸抑制時,無論是否合并血氧飽和度降低,建議即刻給予無創機械通氣治療,如臨床癥狀無改善、血氧飽和度持續降低,必要時改為有創機械通氣;合并急性腎功能損傷的患者,推薦采取連續性腎臟替代治療。
綜上所述,一旦確診 ICI-M,應盡早給予大劑量糖皮質激素治療,直至癥狀緩解、cTn 降至正常;如糖皮質激素治療失敗,可強化免疫抑制治療。目前尚無評估發生 irAE 后重啟 ICI 治療的安全性研究。2022 年 ESC 腫瘤心臟病指南建議,當 ICI-M 完全緩解且停用口服激素后,建議通過多學科討論來評估是否重啟 ICI 治療,討論內容包括 ICI-M 的嚴重程度、是否存在替代抗腫瘤方案、ICI 聯合用藥考慮減為單藥治療等。
7 小結與展望
隨著 ICI 的臨床適應證不斷擴大以及聯合用藥的增加,ICI-M 的發病率逐年升高,目前相關研究處于初期階段且高質量研究有限。未來應重視對 ICI-M 發病機制的研究,同時需積極尋找新的免疫檢查點靶點來降低 ICI-M 的發病率,并拓寬 ICI 的免疫新療法。ICI-M 的早期診斷對于盡早開始應用糖皮質激素尤為重要,盡量避免因缺乏或延遲治療而進展為暴發性心肌炎的風險,因此臨床醫師需要提高對 ICI-M 的認識,早期識別 ICI-M 患者。另外,應重視 ICI 治療前、治療期間及治療后的心血管動態監測,加強急診科、腫瘤科、心血管內科及重癥監護病房等多學科癌癥綜合管理。
閆靜靜;劉韶瑜;葛洪霞;馬青變,北京大學第三醫院,202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