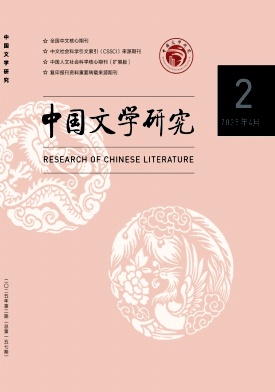中國文學研究雜志投稿格式參考范文:從漢簡看漢代奏議書寫形態(tài)的法定性與視覺修辭
時間:
引言
漢代尊 “禮” 尚 “文”,“禮” 是經(jīng)國家、定社稷、安百姓的重要方式,故 “禮” 實為漢代政治運作的制度根基,其具體方式則是以文書御天下,國制政典主要以 “文” 的形式體現(xiàn)出來。換言之,“文” 是漢代 “禮治” 的核心。各類 “經(jīng)國之文” 中,奏議既是議政制度的產(chǎn)物,也是文書理國最主要的行政方式之一。奏議往往為治國理政的 “當務之急” 而發(fā),追求 “有益于時,能補于世” 的功效。本文擬在前人研究基礎(chǔ)上,以漢簡實物相印證,呈現(xiàn)奏議文本結(jié)撰在語言上的程序化,書寫用簡、字體、布局等均有其 “法定性”,以及傳播效果上的 “視覺修辭” 性,以期拓展和深化學界對這類 “經(jīng)國之文” 的認識。
一、漢代奏議類文章的文體特征
漢代奏議是一個 “文類范疇”,其下又可分為 “章”“表”“奏”“議 (駁議)” 四體,四種文體既有共性,又有個性,具有各自的語言規(guī)范、格式特點及文體功能,且具有法律的規(guī)定性。據(jù)《漢書》載:“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 漢初律法規(guī)定,吏民上書,字體書寫不正,尚要被檢舉,章奏之語言規(guī)范如有差錯,更為法所不容。從具體實踐來說,也體現(xiàn)出其法定性。蔡邕《獨斷》言:凡群臣上書于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議。章者需頭,稱 “稽首”,上書、謝恩、陳事、詣闕通者也。奏者亦需頭,其京師官但言 “稽首”,下言 “稽首以聞”,其中有所請,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臺,公卿校尉送謁者臺也。表者不需頭,上言 “臣某言”,下言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 “某官臣某甲上”。文多用編兩行,文少以五行。詣尚書通者也。公卿校尉諸將不言姓,大夫以下有同姓官別者言姓。章曰報聞,公卿使謁者,將大夫以下至吏民,尚書左丞奏聞報可。表文報已奏如書,凡章表皆啟封,其言密事,得帛囊盛。其有疑事,公卿百官會議,若臺閣有所正處,而獨執(zhí)異議者,曰駁議。駁議曰:某官某甲議以為如是,下言臣愚戇議異。其非駁議,不言議異。其合于上議者,文報曰:某官某甲議可。
這里對章表奏議形式、語言特點法定性的描述,顯然是根據(jù)簡牘書寫的物質(zhì)形態(tài),即在簡牘上由右向左書寫,每行由上而下書寫。“頭”“上”“下”“左”“右” 都是針對奏議等簡冊的物質(zhì)形態(tài)而言。蔡邕是章奏寫作的名家,“任昉《文章緣起》認為上章始于‘后漢孔融《上章謝太中大夫》’。其實蔡邕的《戍邊上章》就是這種‘昭明心曲’之作。這篇文章作于光和元年,蔡邕四十六歲。由于犯顏直諫,被流放朔方,故作此文…… 披肝瀝膽,近于司馬遷的《報任安書》”。《獨斷》在作者寫作實踐的基礎(chǔ)上所總結(jié)的漢代四種奏議文體雖各具特色,但其共同點在于其 “法定性”—— 受文對象皆為皇帝,目的皆為向皇帝進言獻策或陳請議事,行文由專門機構(gòu)負責 (西漢前期為公車司馬,武帝后為尚書門下戶曹),行文過程保密以保護上書人。《后漢書・百官志》:“蘭臺令史,六百石。” 注曰:“掌奏及印工文書。” 又《班彪傳》注引《漢官儀》曰:“蘭臺令史六人,秩百石,掌書劾奏。” 東漢時由蘭臺令史職掌此事。
漢代奏議的撰寫格式和語言也有明確的法定性,以昭示奏議撰作者的不同身份和官職等級的制度劃分。從實際運用來看,章、表、奏、議四種文體也常有文體的交叉。因此劉勰在《文心雕龍・章奏》合而論之:夫設(shè)官分職,高卑聯(lián)事。天子垂珠以聽,諸侯鳴玉以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 降及七國,未變古式,言事于主,皆稱上書。秦初定制,改書曰奏。漢定禮儀,則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議。章以謝恩,奏以按劾,表以陳請,議以執(zhí)異。…… 章表奏議,經(jīng)國之樞機,然闕而不纂者,乃各有故事而在職司也。
據(jù)現(xiàn)有以上四種文體的文本材料可知,漢代禮制規(guī)定,群臣向皇帝上書格式規(guī)定為 “章”“奏”“表”“議” 四種。“謝恩”“按劾”“請陳”“執(zhí)異” 的不同參政方式,既表征了臣與君的關(guān)系狀態(tài),也規(guī)定了章、奏、表、議的文體功能。以此區(qū)別皇帝與臣民的上下尊卑關(guān)系,這不僅展露出漢代官文書制度的結(jié)構(gòu)特征,更體現(xiàn)了禮制精神和 “君君臣臣” 等級觀念。周勛初先生指出:劉勰把 “章”“表” 合在一起,當因二者在 “對揚王庭,昭明心曲” 上有共通之處。“章以造闕,風矩應明;表以致禁,骨采宜耀。循名課實,以文為本者也。” 因為 “章” 更著重于頌圣,所以從文體而言,更為重要。這種區(qū)別,實際上也是很難細化的。因為一般陳情的表文,既對君主有所懇求,必然也要有頌圣的表示,對以前的沐浴皇恩也要再次感謝。
周勛初先生指出了章和表在文體功能和形式方面的重合現(xiàn)象。其實,奏和議也是如此。劉勰雖分四類,但其在實際運用中,界限模糊是事實。西漢的章奏比較典型的如賈誼《治安策》《上疏請封建子弟》、劉歆《上〈山海經(jīng)〉表》、申屠嘉《奏議孝文為太宗廟》、霍去病《請立皇子為諸侯王疏》、嚴青翟《奏請立皇子為諸侯王》、楊敞《奏廢昌邑王》、趙充國《屯田奏》、晁錯《賢良對策》、董仲舒《舉賢良對策》、王嘉《因日食直言奏事》、鮑宣《陳時弊書》等,有的稱 “上疏”,有的稱 “表”,有的稱 “奏”,有的無稱,實際運用中很難截然分開。東漢時代的有陳元《請立左氏博士疏》、蔡邕《戍邊上章》《上始加元服與群臣上壽章》、竇武《上表諫宦官封侯》、桓譚《諫信讖薄賞疏》、蔡茂《上書禁制貴戚》、申屠剛《舉賢良方正對策》《封皇子議》、第五倫《上疏褒稱盛美以勸成風德》等,也是如此。汪桂海先生據(jù)《后漢書》鄭弘上書漢章帝陳謝與蔡邕向漢靈帝自陳欲補撰 “十志” 的例子指出:“章也確實可用于陳事、請示。”“章還可用于舉劾。” 可謂持平之論。
漢代章、表、奏、議的文本,均由 “時間、抬頭、正文、結(jié)尾” 四個部分構(gòu)成,各部分均有固定稱謂和程序化習用語。例如,臣下向皇帝上奏時,稱皇帝為 “陛下”,而自稱為 “糞土臣”“草莽臣”;正文中臣下議事之前首先要表明 “昧死言”,議事完畢必言 “稽首”“頓首”“死罪死罪” 等習用語。這些固定稱謂和習用語的產(chǎn)生,是在漢代官文書制度影響下形成的一套臣下與皇帝溝通時慣用的話語模式,即 “上奏者的官職 + 臣 + 名 + 昧死 / 再拜 (言)+ 皇帝陛下”。這種話語模式系統(tǒng)的運用,不僅維護了皇帝的權(quán)威,也強化了君臣等級觀念。稱謂與用語的固定格式客觀上將奏議形塑為能夠體現(xiàn)皇權(quán)體制等級規(guī)范與禮樂制度的制式化文章。
章、表、奏、議,不僅是君臣之間溝通交流的特定方式,也是皇帝發(fā)現(xiàn)治國之才的重要途徑。許多漢代官員就是通過向皇帝上呈奏議的方式躋身朝堂而步入仕途的。《后漢書・左雄傳》載:“自雄掌納言,多所匡肅,每有章表奏議,臺閣以為故事。” 同書《胡廣傳》:“(胡廣) 遂察孝廉。既到京師,試以章奏,安帝以廣為天下第一。” 在漢代 “對于絕大部分文士而言,只要他們懷有功名追求,仕途熱衷,就必須學習、掌握并熟練運用制式文章這個必要的工具。對于工具的熟練運用,有利于他們功名目標的實現(xiàn)。這是文士走向皇權(quán)體制內(nèi)的必要通道,是打開仕途之門的真正‘敲門磚’”。更重要的是,章表奏議的撰作實踐也體現(xiàn)了漢代文人 “立德、立功、立言” 的士大夫精神,他們將自己的政治抱負與人生理想融入奏議的撰作,字里行間彰顯著立言不朽的崇高人生價值。
二、漢代奏議對特定稱謂的運用
稱謂作為社會關(guān)系最直接的反映,是聯(lián)系個體與社會的重要文化符號。古代人際稱謂不僅包含著約定俗成的角色規(guī)范與潛在的社會語用含義,還展現(xiàn)出社會人際關(guān)系的種種面貌,也折射出特定社會語境中的豐富文化內(nèi)涵和價值取向。早在春秋時代,孔子就提出了 “正名” 的重要觀點。“正名” 的出發(fā)點和落腳點就是通過名分、名稱體現(xiàn)出尊卑等級的不同,彰顯禮制精神。兩漢奏議的行文語言、書寫格式上的稱謂語的運用即是如此。
1.“皇帝陛下” 等專屬稱謂的運用
奏議在起首句或正文當中運用特定稱謂 “(皇帝) 陛下”,用于神圣化臣子與皇帝溝通的話語方式。其絕非簡單的記錄符號,而是皇權(quán)政治的產(chǎn)物,具有鮮明的等級意識和時代烙印。考察傳世文本與出土漢簡實物,可知兩漢時期的奏議在起首語、正文和結(jié)尾處運用 “(皇帝) 陛下” 專門稱謂的具體形態(tài)。
例如,《漢書・南粵傳》載有南粵王趙佗上呈文帝奏疏言: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 起首語即言明 “上奏者身份 + 臣 + 上奏者名” 上書 “皇帝陛下”。又如,西漢申屠嘉《奏議孝文為太宗廟》:丞相臣嘉等奏曰:“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 此例仍由 “丞相 (官職)+ 臣 + 嘉 (上奏者名)+ 奏曰” 四個核心部分組成,奏文首句即稱 “陛下”。
再如霍去病《請立皇子為諸侯王疏》: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 陛下恭讓不恤,群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愿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還有蔡邕《戍邊上章》也很典型性。抬頭、正文均使用 “皇帝陛下” 或 “陛下” 稱謂:朔方髡鉗徒臣邕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邕被受陛下尤異大恩,…… 陛下天地之德,不忍刀鋸截臣首領(lǐng),得就平罪,父子家屬徙充邊方…… 惟陛下留神省察。
以上為史書所錄之奏議實例,經(jīng)過了史家的轉(zhuǎn)寫或改寫,過濾掉了其物化形態(tài)傳達的文化信息。借助出土漢簡實物,可重現(xiàn)和直觀漢代奏議特別稱謂物化形態(tài)的視覺傳達效果。例如敦煌馬圈灣烽燧遺址漢簡上書:皇帝陛下 始建國天鳳三年十二月壬戌上敦德玉門千秋隧 (一八〇);皇帝陛下 始建國天鳳亖年正月甲戌上敦德大煎都候鄣 (一八一);[皇帝陛下臣ム 叫 = 頭 = 十二月王辰敦德玉門行大尉事試守 (一八二)];[皇帝陛下臣ム ⇒ 逆虜恒棱前 (九六九)]。
敦煌馬圈灣烽燧屬漢代敦煌郡玉門都尉所轄玉門候官的駐地,此處出土漢簡時間范圍由西漢宣帝本始三年 (公元前 71 年) 至王莽地皇三年 (公元 22 年) 前后近一百年。其中詔奏文書實物未經(jīng)改易,借此可以還原史書所載奏議的文本形態(tài)、行文格式的原始面貌。簡 180、181 “皇帝陛下” 頂格書寫,字體大于正文,“下” 字的豎筆有意加長加粗,且下空兩格。簡 182、969 與上兩簡相同,但稍有不同的是 “皇” 字后空一格,以此凸顯皇帝獨尊的地位及不可僭越的政治屬性。“臣” 字后的 “厶” 是留空符號,可根據(jù)需要填寫上書者的名字,表明這是按固定格式預備的公文模板,這樣可以提高工作效率。與史書所載奏議文本雖大體相同,但形式的法定性更顯直觀。1981 年面世的《王杖詔書令冊》中節(jié)錄有平民給漢成帝的上章,其文本亦以 “皇帝陛下” 稱謂起首:皇帝陛下:臣廣知陛下神零,覆蓋萬民,哀憐老小,受王杖、承詔。臣廣未 (弟十三);皇帝陛下 (弟十八)。
比較漢簡實物和傳世章表奏議文本可知,“(皇帝) 陛下” 為奏議起首語,有時也運用于正文和結(jié)尾部分,屬于臣子對皇帝的專有稱謂。在正文中,依據(jù)奏議作者的陳述需要,有時省去 “皇帝” 二字而直接用 “陛下”。在撰作中,皇帝稱謂或皇帝批答語常抬頭書寫,其書寫另行且位置高出其他文字,從閱讀時的直觀感受來看,顯然是借視覺上的書寫位置,標志著皇帝擁有至高無上權(quán)利。
“皇帝” 稱號自秦始皇始。《史記・秦始皇本紀》載秦王嬴政統(tǒng)一六國后感嘆:“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后世,其議帝號!” 于是丞相王綰、御史大夫馮劫、廷尉李斯等共同上書曰:“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nèi)為郡縣,法令由一統(tǒng),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制’, 令為‘詔’, 天子自稱曰‘朕’。” 王曰:“去‘泰’, 著‘皇’, 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 制曰:“可。”“皇帝” 的稱謂源于對三皇、五帝的尊稱,亦是對君王功業(yè)盛德的稱美。“陛下” 原指站在臺階下的侍者,依禮當臣子向天子進言時,不能直呼天子,須先呼階下侍者轉(zhuǎn)而告之,以示對皇帝的尊敬。應劭《風俗通》對于 “陛下” 有精要闡釋:“陛者,升堂之陛。王者必有執(zhí)兵陳于階陛之側(cè)。群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以達尊之意也。若今稱殿下、閣下、侍者、執(zhí)事,皆此類也。” 由此可知,“陛下” 的核心含義在于 “因卑以達尊”, 是禮儀的空間關(guān)系符號化抽象化的結(jié)果。
章表奏議稱 “皇帝陛下”, 尤顯尊榮頌美之意。“皇者,大也,言其煌煌盛美。帝者,德象天地,言其能行天道,舉措審諦,父天母地,為天下主。” 自西漢至東漢,奏議文本中的稱謂多因時代而變化,但 “(皇帝) 陛下” 這種專門稱謂從未發(fā)生改變,它意味著擁有 “至尊” 地位的 “皇帝陛下” 是群臣 “不敢指斥” 的專用語,“它的本質(zhì)含義就是通過專有語辭的設(shè)置,使得‘最貴’的皇帝與任何臣民之間,形成一條不能逾越的精神文化塹壕”。自命為天帝之子的皇帝奉天之命來統(tǒng)治萬民,在 “君權(quán)神授” 觀念背景下,皇帝的思想、行動乃至話語無一不是神明至圣的。臣下不僅在面奏皇帝時態(tài)度要謙恭敬畏,而且于奏議之文中,也要使用 “皇帝陛下” 等特定稱謂。作為古代皇權(quán)的崇高象征與書寫標志,在漢簡文書中不僅需要 “抬頭” 或 “提行” 書寫,還須使用有別于其他文字的獨特書體 —— 漢代通行的標準隸書。
2.“(某某) 臣” 固定稱謂的運用
奏議中既然有對皇帝的專屬稱謂,自然也有上奏者用以自稱的固定稱謂。上奏者通常以 “臣”“糞土臣”“愚臣”“草莽臣”“草茅臣” 自稱,以示謙卑。“臣” 的稱謂在殷商卜辭和周金文中即已有之,指奴隸。甲骨文、金文 “臣” 字像豎目形狀 “”“”, 許慎《說文解字》解釋為 “事君者,象屈服之形”。在商代,那些供服御、為宰治的小臣、王臣雖然所任職位不同、官階地位不同,但對于商王而言,他們是奴仆,故稱之為 “臣”。西周時期 “臣” 的內(nèi)涵發(fā)生了較大變化。除繼續(xù)用作對奴隸的稱謂之外,“臣” 還用于統(tǒng)治集團內(nèi)部等級之間隸屬者的稱謂,“公臣”“家臣” 就是此時期出現(xiàn)的兩種極具特色的政治性人際稱謂。戰(zhàn)國時期,士人自稱臣,以示謙卑恭敬之意,對象不限于君王。秦漢是中國君主專制制度創(chuàng)立和發(fā)展的重要時期,這些制度強化了皇帝與群臣的等級,皇帝是所有官吏的唯一君主,各級官吏應當對皇帝惟命是從,在至尊的皇帝面前都應俯首稱臣。如此,通過固定稱謂就明確地界定了帝王與臣民之間的身份及地位之差別。奏議中還用 “糞土”“草莽” 等自我貶低的詞語與 “臣” 配合使用。例如許慎之子許沖給漢安帝的上書,起首曰:召陵萬歲里公乘草莽臣沖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
自稱 “草莽臣”, 較單稱 “臣” 更顯謙卑。又如,西漢文帝時期,晁錯《舉賢良對策》中的起首語:臣錯草茅臣,亡識知,昧死上愚對,曰:……。昧死上狂惑草茅之愚,臣言唯陛下財擇。晁錯自稱 “草茅臣”“亡識知”“狂惑草茅之愚”, 尤顯謙卑。臣民上書皇帝時自稱 “草莽臣” 亦有其歷史淵源。《孟子・萬章下》載 “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 即謂無官職者為草莽臣。清人胡匡衷《儀禮釋官・士相見禮》亦曰:“在野,則曰‘草茅之臣’。”“草茅”“草莽” 音近義同。“草茅” 在漢代平民奏章中也有所見,《漢書・梅福傳》梅福歸壽春家居時上奏,云 “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涂野草,尸井卒伍,故數(shù)上書求見,輒報罷”, 即自稱為 “草茅臣”。
還有以 “糞土” 自稱者,東漢蔡邕入獄前的上書,起首便云:議郎糞土臣邕頓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論語・公冶長》:“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杇也。” 程樹德引舊注:“糞土朽木,諸家以為質(zhì)不美之譬。” 使用 “糞土臣” 自稱,顯示其儒者氣象。《漢書・東方朔傳》載,武帝擴建上林苑,占去農(nóng)田,東方朔上書諫阻,奏文末曰: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愿,愿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
于 “糞土” 之外,又加 “愚” 字。傳世文獻中 “草莽臣”“糞土臣” 的稱謂在出土漢簡中亦得印證,表明史書所錄奏議文本大體不違原貌。
如居延漢簡所見 “上書” 簡:肩水候官令史觻得敬老里公乘糞土臣熹昧死再拜上言變事書 562・17+387・12。再如肩水金關(guān)漢簡所見 “上書” 簡:糞土臣德昧死再拜上言變事書,印曰臣德,其丁丑合蒲藍□□EPT52:46A;杜衍習陽里公乘草莽臣鎮(zhèn)昧死再拜上書 EPT52:318A。再如敦煌馬圈灣漢簡所見 “上書” 簡:使西域大使五威左率都尉糞土臣厶稽首再拜上書 (一一七)。
以上所舉均為臣子 “上書” 或 “上變事書” 之標題簡,或曰首簡,只單簡單行書寫 “上書” 或上 “變事書” 的主體。其中居延漢簡 EPT52:46A 言 “印曰臣德”, 知是 “上書” 或 “變事書” 簡冊之封檢。“上書” 或上 “變事書” 均以隸書書寫,以示重視。唯馬圈灣漢簡一例為略帶草書筆意之隸書。以上所引簡牘實例簡上端皆留有空白。
“草莽臣”“草茅臣”“糞土臣” 等稱謂都是上奏或上書者表示禮敬的謙辭,在漢代逐漸成為臣民向皇帝上書時的習慣用語。《禮記・曲禮上》云:“凡為長者糞之禮,必加帚于箕上。” 糞之本意為掃除。“糞土” 意為從事灑掃等事務的仆役;以 “糞土臣” 自比,反映出漢代皇權(quán)體制下君尊臣卑等級思想的逐步強化及在官方文書中的顯現(xiàn)。
三、漢代章表奏議的程序化語言
語言學上所謂程序化語言,是指由整體習得并儲存于記憶中的多種類型詞串。作為語法、語義和語境的結(jié)合體,程序化語言有著穩(wěn)定的搭配意義和特定的語用環(huán)境,并且在使用時可直接從記憶中提取,無需進行語法生成和分析。這種情況在章表奏議中也比較常見,其程序化語言的運用整體上比較穩(wěn)定,但也有個別例外,并非一成不變。
1、臣屬奏請中的程序化語言
蔡邕《獨斷》載:“漢承秦法,群臣上書皆言昧死言。王莽盜位,慕古法,去昧死曰稽首。光武因而不改。朝臣曰稽首頓首,非朝臣曰稽首再拜。公卿侍中尚書衣帛而朝曰朝臣,諸營校尉將大夫以下亦為朝臣。” 通過傳世文獻與出土材料互為印證,可知《獨斷》對于奏議所用程序化語言因王莽改制這一重大歷史事件而發(fā)生變化的論述恰切精當。對比以下兩個奏議文本,即可見其端倪。
嚴青翟《奏請立皇子為諸侯王疏》: 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 昧死上言: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議:古者裂地立國,并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臣旦、臣胥為諸侯王。從行文格式上看,該篇 “奏” 文起首即曰 “臣昧死言”, 由于文中就具體事項有所請示,故末尾再言 “臣昧死請”。
東漢建光元年,許慎遣其子許沖將《說文解字》獻于漢安帝,并上其奏曰:召陵萬歲里公乘草莽臣沖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伏見陛下神明盛德,承遵圣業(yè),上考度于天,下流化于民,…… 作《說文解字》。…… 臣沖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稽首再拜,以聞皇帝陛下。建光元年九月己卯朔二十日戊戌上。奏文抬頭由 “昧死” 變?yōu)?“稽首再拜”, 正文結(jié)尾再次強調(diào) “稽首再拜”, 并連用 “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諸詞,表現(xiàn)上奏者之恭謹敬慎與合乎古禮。程序化習語及其變化不僅使奏議文書肅穆典雅,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禮的地位的升降。
《周禮・大祝》鄭玄注曰:“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 賈公彥疏云:“二種拜,俱頭至地,但稽首至地多時,頓首至地則舉,故以叩地言之,謂若以首叩物然。” 又云:“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 頓首,即引頭至地,只作短暫接觸。行稽首禮時須引頭至地進行跪拜,停留時間要比頓首長。是以稽首、頓首有別,而稽首之禮尤重,乃敬之至也。自西漢末王莽改制,臣下上奏皇帝,除言 “稽首” 之外,亦可言 “頓首”, 或連用 “頓首頓首”, 以此表示對皇帝的尊崇。“昧死” 作為章奏起首語的專用詞匯一直使用到西漢末期,王莽新政之后便為 “稽首”“頓首” 所替代,少見于章奏文書。
結(jié)合出土漢簡奏議實物,更能夠真切感受到漢代官文書制度下奏議文本中臣子自稱程序化語言書寫的物質(zhì)形態(tài)與視覺效果。肩水金關(guān)遺址出土的《永始三年詔書簡冊》較為完整地使用了此類固定用語,茲引述如下:丞相方進、御史臣光昧死言;明詔哀閔元 = 臣方進、御史臣光,往秋郡被霜,冬無大雪,不利宿麥,恐民(73EJF1:1);調(diào)有余給不足不 (補) 民所疾苦也,可以便安百姓者,問計長吏。守丞條封;臣光奉職無狀,頓 = 首 = 死 = 罪 =, 臣方進臣光前對問,上計,弘農(nóng)大守丞(73EJF1:2);令堪對曰:富民多畜田出貸□(73EJF1:3);郡國九谷最少可豫稍為調(diào)給立輔預言民所疾苦可以便宜;弘農(nóng)大守丞立山陽行大守事、湖陵□□上谷行大守事 (73EJF1:4);來去城郭、流亡、離本逐末,浮食者浸□……(73EJF1:5);與縣官業(yè)稅以成家致富開并兼之路,陽朔年間 (73EJF1:6)。
《永始三年詔書策》由 16 支簡組成,以上所引 8 簡前 7 簡是奏書,均低兩格書寫。內(nèi)容是永始三年丞相翟方進與御史孔光向漢成帝劉驁奏書陳請施行 “除貸錢它物律” 和 “還息與貸者它不可許” 的律令,用以解決嚴重自然災害造成的社會危機與民生疾苦等問題。這份奏議經(jīng)過皇帝 “制可” 之后,成為詔書下發(fā)至全國執(zhí)行。73EJF1:8 “制可” 后 8 簡是下達詔書的具體要求,均頂格書寫,尤其是 “制可” 一簡不僅另簡頂格書寫,且 “可” 字豎筆出以夸張寫法,不僅有醒目的視覺效果,也宣示了皇帝的權(quán)威。章奏起首用 “職位 + 臣 + 昧死言” 的固定搭配,每奏一事后用 “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作結(jié),文書結(jié)尾以 “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作結(jié)。
再如,敦煌馬圈灣所出漢簡中:以稱職叩頭死罪死罪 (二六);西域都護領(lǐng)居盧訾倉守司馬鴻叩頭死罪死罪 (九五);臣稽首再拜謹□□前奉書臣厶稽首再拜 (一一〇);使西域大使五威左率都尉糞土臣厶稽首再拜上書 (一一七);當先到臣請欽到知審以狀聞臣稽首再拜(一三二)。以上出土的漢簡奏議文書屬王莽時代,故其臣子上奏稱 “叩頭”“稽首”, 格式變化與蔡邕《獨斷》所載相符。叩頭,原本為下級或晚輩見長上的最高禮節(jié),死罪謂觸犯了大罪。26 簡文所示 “叩頭死罪死罪” 以十分工整的隸書書寫,疏朗整飭的書風實際上是奏議書寫者書寫心理的外在顯現(xiàn)。另外,從行文看,95、110、117、132 簡應是戍邊官吏上呈皇帝的章奏文書,邊塞官吏不在朝官之列,故言 “稽首再拜”。
2. 皇帝批答奏議的固定用語
在 “文書行政” 背景下,漢代奏議上呈與詔令下達不僅從行文格式與撰作措辭等方面不斷完善規(guī)范要求,且在撰作、收發(fā)、辦理、保管等各個環(huán)節(jié)都有嚴格的制度流程。奏議作為臣屬進呈君主的上行文書,以陳政事于王庭為主要目的。為增加言政的效論,且使陳事達情語義明確,就需要在修辭上特別使用說服技巧。很多情況下,皇帝制詔就是要進行重大決策。決策往往需要獲取可信的第一手資料作為依據(jù),大臣的奏議就是獲得可靠信息的主渠道之一。奏議一般由執(zhí)掌呈奏與制詔職能的機樞部門上報皇帝,由皇帝酌定是否需要交御前會議、宰輔會議或百官會議等決策系統(tǒng)進行討論,若皇帝同意,即可擬詔實行。《獨斷》:“群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下有司曰制,天子答之曰可,若下某官云云” 及 “群臣有所奏請,無尚書令奏、制之字,則答曰已奏如書,本官下所當至。” 作為上行文的奏議,待皇帝允準之后,在制詔下發(fā)前批答 “可”“下某官” 或 “已奏如書” 等。
例如,元朔五年六月,武帝下詔要求 “導民以禮,風之以樂”“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朝”“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崇鄉(xiāng)黨之化,以厲賢才”。公孫弘據(jù)此事上奏《請為博士置弟子員疏》, 闡述勸學興禮對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作用,并奏請武帝為五經(jīng)博士設(shè)立弟子員,還為在職官員擬定了以儒家經(jīng)學與禮義為標準的升遷辦法和授官條件。這些提議均得到武帝首肯,在其奏議后批答 “制曰:可”。再如,《史記・三王世家》大司馬霍去病上奏請立諸皇子,武帝批示 “制曰:下御史”。即將此奏議轉(zhuǎn)為詔書交由御史大夫處理。《三王世家》又載:“太仆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與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立皇子閎為齊王,旦為燕王,胥為廣陵王。’”《漢書・楚元王劉交》載:“會薨,大鴻臚奏德訟子罪,失大臣體,不宜賜謚置嗣。制曰:‘賜謚繆侯,為置嗣。’” 皇帝批 “制曰可”,“可” 字表示準允,有時是對該奏議的具體處理意見。這種在原奏議上做批示和轉(zhuǎn)辦意見的方式,可以節(jié)省書寫材料,同時也高效便捷,所以一直為后世各代所沿用。
出土文獻中皇帝批答 “制曰” 的實物能夠更為直觀地體現(xiàn)奏議與詔令之間文體轉(zhuǎn)換的視覺效果。如《元康五年詔書冊》所見:御史大夫吉昧死言丞相相上大常昌書言大史丞定言元康五年五月二日壬子日夏至宜寢兵大官抒井更水火進鳴雞謁以聞布當用者・臣謹案比原宗御者水衡抒大官御井中二 = 千 = 石 = 令官各抒別火 (10.27);官先夏至一日以除隧取火授中二 = 千 = 石 = 官在長安云陽者其民皆受以日至易故火庚戌寢兵不聽事盡 [甲窩五日臣諾布臣昧死以聞 (5.10)];[制日可 (332.26)];元康五年二月癸丑朔癸亥御史大夫吉下丞相承書從事下當 [用者如語書 (10.33)];[二月丁卯示相相下車騎將 = 平 = 中二 = 千 = 郡大守諸侯相承書從事下當用者如詔書 少史慶令史宜王始長];三月丙午張掖長史延行大守事肩水倉長湯兼行丞事下屬國農(nóng)部都尉小府縣官承書從事 [下當用者如設(shè)書 / 守屬宗助、府依定 (10.32)];閏月丁巳張掖肩水城尉誼以近次兼行都尉事下候城尉承書從事下 [用者如語書 / 守卒支義義 (10.29)];閏月庚申肩水士吏橫以私印行候事下尉候長承書從事下當用者如詔書 / 令史得 (10.31)。
《元康五年詔書冊》由 8 支簡組成,出土時已散亂失序,大庭脩等學者對其進行復原,使之完整可讀。冊書內(nèi)容涉及西漢宣帝元康五年 (公元前 61 年) 二月,大史丞定針對夏至禮儀的 “更火”“寢兵” 等提出具體意見,其奏文經(jīng)由太常蘇昌上報丞相,再由丞相轉(zhuǎn)御史大夫丙吉,丙吉審定后呈報皇帝。皇帝批示 “制曰可” 后,成為詔書,于是又通令全國在夏至日舉行更火、火供及疏浚水井的活動。詔令從漢廷中樞經(jīng)張掖郡太守處下達給肩水都尉、候官及其下屬的部和燧等邊塞基層組織。候官、候、部或燧大致相當于內(nèi)地的縣、鄉(xiāng)、亭或里。漢代依月令行事,邊塞地區(qū)也不例外。通過觀察此詔書冊圖版,我們可以看到其中 “制曰可” 有明顯的法定特別性形式特征。首先是提行書寫;其次是該簡書寫位置高于奏請部分的簡文一至兩字;再其次是 “制曰可” 字體明顯大于其他部分,“可” 字的最后一筆呈現(xiàn)出遒勁有力且別具一格的書寫形態(tài),使其成為在文書程序上彰顯皇帝詔令權(quán)威的重要象征。
武威漢墓出土《王杖詔書令冊》也比較典型:長安敬上里公乘臣廣,昧死上書 (弟十二);皇帝陛下:臣廣知陛下神零,覆蓋萬民,哀憐老小,受王杖、承詔。臣廣未 (弟十三);常有罪耐司寇以上。廣對鄉(xiāng)吏趣未辨,廣對質(zhì),衣僵吏前。鄉(xiāng)吏 (弟十四);(第十五簡缺);下,不敬重父母所致也,郡國易然。臣廣愿歸王杖,沒入為官奴。(弟十六);臣廣昧死再拜以聞 (弟十七);皇帝陛下。(弟十八);制曰:問何鄉(xiāng)吏,論棄市,毋須時;廣受王杖如故。(弟十九);元延三年正月壬申下 (弟廿)。
《王杖詔書令冊》完整記錄了漢朝對待老人的優(yōu)惠待遇和措施,真實反映出當時的尊老養(yǎng)老制度。該簡冊原簡共 27 簡,除第 15 簡缺失外,其余 26 簡保存完整。簡冊中第 12 簡至 18 簡為名叫 “廣” 的公乘 (爵名) 向皇帝進行自訴的上奏文,第 19 簡為皇帝的 “批答語”, 第 20 簡則是皇帝的下詔。此簡冊也完整地保存和呈現(xiàn)了漢代奏議與詔書間的轉(zhuǎn)換過程。簡冊中的 “皇帝陛下” 與 “制曰” 皆為頂格書寫,高于其余文字一格或兩格,對深入認識漢簡文書的行文格式方面具有重要價值。
在其他西北漢簡中,可見 “制曰可” 另行頂格書寫、“制” 后空兩格的形式,較其他書寫方式更具積極的視覺修辭效果。例如《居延新簡集釋》EPT59:536: 長秩官吏員丞相請許臣收罷官印上御史見罔自 臣昧死以聞;制 曰可。此簡右側(cè)一行 “相” 字后、“見” 字后各有空白,當是兩道編繩處,表明此簡為一冊書之組成部分,且為編連成策后書寫。“制曰可” 為標準的漢隸,“制” 字下空兩格,“曰可” 與右面一行齊平位置。右行所書為奏議,具體的處理意見可能在 “制曰可” 后的其他簡上書寫。《懸泉漢簡 (壹)》I 90DXT0116②:4: 制曰下丞相御史・臣宣臣駿前奏林隆使案驗逐捕商等首匿者……;捕斬渠率一人為尤異奏可林隆發(fā)起商等從跡過樂成侯去疾臧匿在四月甲辰赦令前臣宣;臣駿。此簡出自王駿幕府檔案,“制曰可” 視覺修辭方式與上一簡大體相同,所不同者,標明處理方式為 “下丞相御史”, 由其落實 “臣宣臣駿” 奏議所言逐捕逃犯及首匿等事宜。由簡牘實物有所書文字推斷,此簡為單簡,可能是制書的抄錄本。
皇帝批示 “制曰” 之例還見于東漢《乙瑛碑》。碑文云:司徒臣雄、司空臣戒稽首言:魯前相瑛書言詔書崇圣道勉 “六藝”。孔子作《春秋》, 制《孝經(jīng)》。刪述 “五經(jīng)”, 演《易系辭》。經(jīng)緯天地,幽贊神明。故特立廟,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即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lǐng),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廟。春秋饗禮,財出王家錢。給大酒直,須報。謹問大常祠曹掾馮牟史郭玄,辭對。故事辟雍禮未行,祠先圣師,侍祠者孔子子孫、大宰、大祝令各一人。皆備爵大常丞監(jiān)祠,河南尹給牛羊豕雞□□各一,大司農(nóng)給米祠。臣愚以為,如瑛言孔子大圣,則象乾坤,為漢制作。先世所尊,祠用眾牲。長吏備爵,今欲加寵子孫,敬恭明祀,傳于罔極。可許。臣請魯相為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掌領(lǐng)禮器,出王家錢給大酒直,他如故事。臣雄、臣戒愚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聞。制曰可。元嘉三年三月廿七日壬寅,奏雒陽宮。《乙瑛碑》即《漢魯相乙瑛奏置孔廟百石卒史碑》, 東漢桓帝元嘉三年置立。碑文敘述身為魯相的乙瑛因孔廟禮器無人掌管,奏請在孔廟設(shè)守廟百石卒史,以執(zhí)掌祭祀之事。因推選的卒史為孔氏后人孔龢,俸祿百石,故《乙瑛碑》也稱《百石卒史碑》或《孔龢碑》。碑文照錄司徒吳雄、司空趙戒和魯相乙瑛,共同奏請選任孔龢為百石卒史的奏文,及皇帝批答 “制曰可” 的簡冊而成。由右錄碑文拓本可見,“制曰可” 高出一格且獨占一行。從 “司徒臣雄、司空臣戒稽首言” 至 “臣雄、臣戒愚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聞” 為奏請。在書寫形式和內(nèi)容上,碑文保留了制詔奏議的書式,但因碑的形制而更具積極的視覺修辭效果。
四、結(jié)語
綜上所述,關(guān)于漢代奏議書寫形態(tài)及其文化內(nèi)涵,我們似可達成如下共識:
第一,奏議或皇帝批示后成為詔令的奏議是一個由文字和轉(zhuǎn)化為圖像或符號化的 “書寫” 組成的 “復合文本”。有學者指出:“漢字不僅有形、聲兩個編碼,同時可傳達兩個信息量,更重要的是漢字不像一切拼音文字那樣在構(gòu)型上是一維的線性形式,漢字是方塊字,有左右或左中右、上下或上中下結(jié)構(gòu),是二維性的平面結(jié)構(gòu),這種‘面’結(jié)構(gòu)本身有表意性,是一種情境性的象思維。所以,漢字從根本上孕育、孳乳了中國傳統(tǒng)哲學思想中的情境本體和情境反思的思維方式,漢字與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情境本體和情境反思的思維方式有內(nèi)通性。” 簡冊中的 “皇帝陛下” 與 “制曰” 等,皆需以隸書提行頂格書寫,以體現(xiàn)皇權(quán)等級觀念。由奏議的上行屬性轉(zhuǎn)變?yōu)樵t書下行屬性的程序化過程更是對漢代禮制的物化彰顯。“制曰” 等,是對皇權(quán)的文書修辭層面的具體展現(xiàn)。
第二,漢代章表奏議的書寫具有嚴格的 “法定性”。奏議書寫的視覺呈現(xiàn)形式,以及其中 “糞土臣”“草莽臣” 等特定稱謂的使用,“昧死言”“昧死請”“昧死再拜” 等禮敬語的運用,都是皇權(quán)對政治角色的制度化與符號化的規(guī)定性。程序化語言在奏議文中的使用與認同也能夠呈現(xiàn)出在 “禮治” 秩序下君臣關(guān)系的政治定位。
第三,漢代奏議簡冊在重視文字信息傳達的同時,還自覺運用 “視覺修辭” 策略。奏議簡牘中皇帝批復 “制曰可” 中的 “可” 字,呈現(xiàn)獨特的書寫筆法,最后一筆 (豎畫) 夸張肆意、筆畫向下,行筆過程中順勢左向掠出,加粗加重,厚實遒勁。“皇帝陛下” 的 “下” 字,“昧死再拜以聞” 的 “聞” 字等,也已經(jīng)完全藝術(shù)化、抽象化、符號化。這種書寫現(xiàn)象,最初或許是書寫者的夸張?zhí)幚恚髞碇饾u成為有意識標志固定用語的方式和手法。從視覺修辭層面來講,其迥然不同的書寫形態(tài)明顯具有積極修辭的價值。此種意識和策略不斷強化,最終符號化、抽象化為官文書制度背景下的典型形態(tài)和固定運筆方式,以此彰顯皇帝的權(quán)威。
第四,漢代奏議的文本形態(tài)、書寫方式與大一統(tǒng)政治相契合,與禮制及其實踐相表里。特定稱謂和程序化的句式與用語,在被頻繁使用過程中形成奏議的法定性,賦予其特殊的政治權(quán)威。奏議是 “經(jīng)國之樞機”, 關(guān)乎大漢王朝的治國理政,“其主要目的在于通過‘文’的方式彌補君主專制政體的不足,因而具有強烈的‘尚文’傾向與人文色彩”,體現(xiàn)出漢代 “禮法相須” 的政治思想。
韓高年;王敬博,西北師范大學文學院,202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