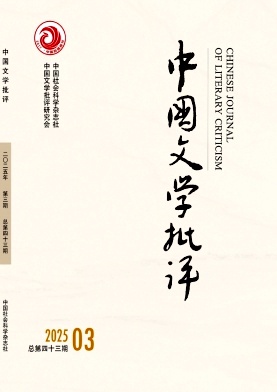中國文學批評雜志投稿格式參考范文:中國當代文學主流傳統中的陜西經驗
時間:
無論從何種意義上說,陜西都是中國文化地理版圖上較為獨特的地方。就中國當代文學而言,陜西不僅是始發地,而且也是較具代表性的實踐區域。因此,本文所要討論的陜西經驗,絕非一個地方性話題,而是一個從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和當代文學主流傳統中生長出來的文學藝術現象。陜西的作家不僅為中國
當代文藝貢獻了一大批精品力作,其文學實踐所生成的陜西經驗,還對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有著廣泛而深遠的啟示意義和借鑒價值。
一、中國當代文學主流傳統的生成與陜西實踐
中國當代文學經歷了 80 多年的發展,形成了多種不同層面、不同形態的傳統和經驗。但中國當代文學的主流傳統是從陜西開始并延續下來的。20 世紀三四十年代在陜西延安展開的文藝實踐,以及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對中國當代文學主流傳統的形成和發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1949 年 7 月第一次全國文代會將《講話》精神確立為新中國文藝的指導方針,此后中國文學藝術各領域基本沿此發展,盡管歷經多種思潮沖擊,當代文藝主流傳統依然貫穿始終,進入新時代后進一步彰顯和發展。
在中國當代文學主流傳統的實踐中,陜西作家是備受矚目的一支勁旅。其歷史淵源是延安文藝傳統在陜西當代文學中的延續,新中國成立后一批延安時期的作家、藝術家和文藝機構留在陜西,成為這一傳統的火種。以柳青、杜鵬程、王汶石等為代表的第一代文學陜軍,將延安文藝的種子播入三秦大地,成為中國當代文學踐行延安文藝精神的典范和陜西經驗的開創者、奠基者,他們的作品是中國當代文學主流傳統延續和發展的標志性作品,也是陜西經驗生成的奠基之作,影響了后來陜西多種藝術門類的發展。
以路遙、陳忠實、賈平凹等為代表的第二代文學陜軍,起步于 20 世紀七八十年代,他們的文學實踐伴隨著改革開放展開,雖所處語境與第一代不同,但文學觀念和創作道路沿第一代路線前行,是其在新語境中的延伸與發展,他們的作品如《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秦腔》等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當代文學的代表作,也體現了陜西經驗。
以楊爭光、紅柯、陳彥等為代表的第三代文學陜軍,起步于 20 世紀九十年代,引入更多時代因素,觀念和方法變化較大,但陜西經驗的核心因素在其作品中延續,他們為文學陜軍注入新的體驗和敘事方式,豐富和擴展了陜西經驗的內涵。
由 20 世紀 70—90 年代出生的作家組成的第四代、第五代文學陜軍,在爭議和選擇中成長,雖遭遇多種沖擊,但因背后有強大的陜西經驗形塑,形成獨特現象,終將賡續和豐富陜西經驗的內涵。經過幾代作家接力,文學陜軍的實踐形成了陜西經驗,成為中國當代文學主流傳統的重要標識。
二、陜西經驗:內涵與啟示
緣起于延安時期,經過幾代文學陜軍前赴后繼的實踐而形成的陜西經驗,之所以能夠成為中國當代主流文學傳統的重要標識,是因為陜西經驗集中體現了延安文藝以來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文藝思想和文藝路線,并對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產生廣泛的啟示意義。概括來看,文學上的陜西經驗有以下幾方面內容。
始終堅持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自《講話》以來,文藝與人民的關系、文藝與現實生活的關系就成為中國文藝發展、文藝主體改造與建構的核心問題。經由幾代黨的領導人的不斷強調和深入論述,幾代作家藝術家的自覺實踐,文藝為人民大眾的方向、文藝反映現實生活,并由此形成的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以下簡稱 “深扎”)的實踐,已成為中國當代文學的主流方向和重要傳統。盡管這一傳統在各地的作家中都在延續,特別是在延安時期和 20 世紀五六十年代相當普遍,如趙樹理長期住在山西老家、李季舉家遷到玉門油田等。但在陜西,“深扎” 現象更為集中典型。柳青 “深扎” 長安縣皇甫村 14 年寫出《創業史》、杜鵬程深入西北野戰軍戰地采訪寫出《保衛延安》、陳忠實在白鹿原老家西蔣村居住幾十年寫出《白鹿原》。路遙、賈平凹本身自幼有著艱辛的鄉村生活體驗,即使在進城成為專業作家后,依然每年堅持行走在家鄉的山山水水、家家戶戶間,才有了《平凡的世界》《秦腔》等這樣一批典型的 “深扎” 事例。并且,陜西已經將 “深扎” 制度化、習慣化、長期化。絕大多數陜西作家都有到區縣、企業掛職體驗生活的經歷。高建群在西安高新區、葉廣芩在周至縣、紅柯在寶雞金臺區、馮積岐在鳳翔縣、方英文在漢陰縣、冷夢在米脂縣、朱鴻在長安區等。有的作家甚至多次深入基層體驗生活。作家藝術家在 “深扎” 中拉近了與老百姓的關系,親身感知了民生疾苦、具體了解了老百姓的生活細節,學習到了大量地方性知識、行業性知識,獲得了在書齋里想象不到的生活體驗。這就是陜西作家能夠佳作迭出的真正原因,也是最重要的陜西經驗。
始終堅持走現實主義道路:現實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唯物論的反映論在文藝思想中的直接表現,是整個中國當代文學的主流傳統。作家能否堅持現實主義精神,直面現實,尊重生活真實,揭示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創造出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被確立為評價當代文學的重要準則。走現實主義道路,是幾代文學陜軍的基本共識。從《創業史》《保衛延安》到《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秦腔》,再到《裝臺》《主角》,當代文學各個階段最主要的現實主義代表作品,集中出自陜西。這足見走現實主義道路是陜西當代文學的基本經驗,也足可證明陜西是中國當代現實主義文學的代表區域。盡管隨著時代和社會生活的發展,現實主義從精神到方法都在不斷深化、不斷豐富、不斷拓展,但其反映真實生活、揭示社會歷史發展的本質規律、創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等基本原則卻一以貫之。
柳青在《創業史》中面對的是中國農民到底該集體創業,還是個人創業的矛盾;路遙在《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中反映的是中國農民該留守土地,還是走向城市、走向外面的世界的矛盾。所不同的是,柳青的結論是確定的、肯定性的,而路遙的結論是反思性的。而在楊爭光的《從兩個蛋開始》中,中國農民又一次回到集體創業與個人創業的艱難抉擇之中,但與柳青不同的是,楊爭光的結論是批判性的。盡管作家們因面對的時代和社會生活不同而做出了各自不同的判斷,采用了不同的寫法,但他們直面現實、力求揭示社會生活本質的現實主義原則卻是一致的。
同時,隨著作家們的文化視野、個人經驗和文學體驗的流變,現實主義在不同代際的陜西作家筆下,融入了不同的元素和寫法。陳忠實的現實主義融入了一部分魔幻色彩;楊爭光的現實主義融入了較多的荒誕色彩;賈平凹、紅柯的現實主義融入了更多的浪漫氣質;陳彥的現實主義則更多地將現實生活戲劇化、喜劇化;而陜西的 “90 后” 作家范墩子的《抒情時代》則又將鄉村社會現實的書寫延伸到了超現實主義的寫法。陜西經驗在告訴人們,現實主義不是一種固定的寫作模式,而是一種直面現實的文學精神。作家對現實所做出的不同感知和體驗,以及所采用的不同寫法,正是對現實主義的豐富和發展。只有在這個意義上,現實主義的道路才越走越寬廣。
現實主義文學的一個成功標志,就是塑造出特定時代、特定區域的典型形象。在陜西作家越走越寬廣的現實主義道路上,走出了中國當代文學人物畫廊中的一大批典型形象。梁生寶、梁三老漢、高家林、孫少安、孫少平、朱先生、白嘉軒、鹿子霖、田小娥、莊之蝶、引生、劉高興、刁順子、憶秦娥等都已成為深入人心的典型形象,其中有的形象已成為一個時代的文化符號。同時,陜西文學的現實主義道路,也在不斷地被延伸到戲劇、電影、電視等領域。從 20 世紀 80 年代開始,陜西的現實主義文學作品陸續被搬上舞臺和銀幕,《人生》被改編為電影;《平凡的世界》兩次被改編為電視劇,近年又被改編為話劇;《白鹿原》被改編為秦腔現代戲、舞劇和話劇,以及電影和電視劇。
《雞窩洼的人家》被改編為電影《野山》;悲劇色彩濃重的《高興》被改編為同名喜劇電影;《裝臺》被改編為電視劇;《主角》被改編為話劇、電視劇;近年來,陜西的現實主義代表作家柳青、路遙也被搬上舞臺和銀幕,先后出現了話劇《柳青》、電影《柳青》、話劇《路遙》等。這些改編作品是現實主義文學的擴展版,將文學中的一批典型形象擴展到了舞臺和熒屏,并通過電視、網絡、智能手機等大眾傳播媒介送入更廣大人民群眾的視野。幾代陜西作家藝術家連續不斷地推出反映不同時代現實生活的力作,塑造出不同時代、不同特質的典型形象,共同延續并拓展了現實主義的文學道路,使現實主義成為陜西經驗的重要組成部分,也使三秦大地成為中國當代現實主義文學的肥沃土壤。
始終保持與傳統文化的血脈聯系:眾所周知,陜西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發源地和集散地。因此,陜西作家與傳統文化的血脈聯系是天然的,且在其具體實踐中得到了充分證實。與傳統文化的血脈聯系,首先表現為陜西作家充分延續了中國傳統文人的精神稟賦。這種稟賦是中國傳統文人數千年來在綿延不斷的 “文”“道” 關系中形成的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歷史使命感和鐵肩擔道義的精神。唐代詩人白居易的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宋代關學大儒張載的 “橫渠四句”——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 便是這種精神稟賦的準確表述。
在陜西的當代文學中,無論是第一代文學陜軍的代表柳青的《創業史》,第二代文學陜軍的代表路遙的《平凡的世界》、陳忠實的《白鹿原》、賈平凹的《秦腔》,還是第三代文學陜軍的代表楊爭光的《從兩個蛋開始》、紅柯的《西去的騎手》、陳彥的《主角》,都立足于書寫社會歷史的史詩式巨變,都是對鄉土中國及其人的生命和命運的深重關切、對 “時” 與 “事” 的謳歌和書寫,都是道義擔當、文脈延續、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的真實寫照。在作家們的寫作中,直接書寫、延續和轉化中國傳統文化,是陜西作家的突出優勢和特色,也是陜西經驗的重要組成部分。陳忠實的《白鹿原》盡管可以從不同角度去闡釋,但歸根到底是一部文化小說。其所講述的是以關學為代表的儒家文化和以白鹿原為代表的農耕文明,在現代文明、社會變革的沖擊下,如何一步步走向式微的歷史過程。該作講出了作家在這一過程中的復雜而矛盾的心理,其中有贊賞、有反思、有惋惜、有批判、有期待,是站在現代文明的視角下,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一次重新審視。
截至《白鹿原》出版的 1993 年,如此集中而深入地反思中國傳統文化的大部頭長篇小說還比較少見。賈平凹的寫作始終是在傳統文化的氛圍中進行的。他對佛、禪、道,以及金石、書法和文人畫的濃厚興趣人盡皆知。他生長于陜南商洛,其性格中本身延續著復雜的文化基因,融合了楚文化的靈性和秦文化的堅韌。賈平凹與傳統文化的血脈聯系,最重要的表現在于他對中國敘事傳統的自覺沿用。無論是從漢字、漢語到漢詩的 “立象盡意” 的象征傳統,佛道哲學中的靜觀美學與空間敘事,還是志怪、筆記、史志,以及古代的白話世情小說、文人小說等,中國傳統敘事中的種種傳統,都能在賈平凹的小說和散文中找到嘗試的痕跡。在當代作家中,始終自覺延續中國敘事傳統者,非賈平凹莫屬。陳彥自幼進入戲劇院團,從演員到編劇再到團長、院長,一直到中國劇協領導,其對傳統戲曲的熟悉程度可想而知。
其代表劇作 “西京三部曲” 是戲曲現代戲創作的標志性作品。盡管進入小說寫作較晚,但其小說 “戲曲三部曲”——《裝臺》《主角》《喜劇》,不僅以密集的行業性知識書寫了當下社會中梨園行里的人生百態,而且將戲曲這一最精粹、最典型的中國傳統文化延伸到了當代小說的視閾之中,綻放出獨異的光彩,且以《主角》獲得茅盾文學獎。浸潤在傳統文化中的作家,在陜西非獨上述幾位,還有眾多作家以不同的文體、不同的風格和敘事方式呈現著其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種種血脈聯系。與此同時,陜西的畫家、音樂家、導演大都有著深厚的傳統文化情懷。例如,長安畫派明確以 “一手伸向傳統,一手伸向生活” 為藝術宗旨,并以此將傳統國畫現代化;趙季平等在陜西工作的作曲家的音樂作品幾乎都與傳統戲曲音樂、民歌有著直接的淵源關系。之所以如此集中地出現了這么多關注并書寫中國傳統文化的作家、藝術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在陜西,在中國傳統文化遺存最集中的地方。因此,他們與傳統文化的血脈聯系必然會成為陜西經驗的重要組成部分。
始終堅持書寫鄉土中國現代化之路:陜西是中國農耕文明的起始地。史料和傳說中記載的神農氏炎帝、“治五氣,藝五種” 的黃帝,以及作為炎黃后人和周部落祖先、“教民稼穡” 的農神后稷等農耕文明的始祖,都是在陜西的土地上開始耕種的。即使在當今中國,國家級農業高新技術產業示范區之一,以及被譽為 “中國農業奧林匹克盛會”、定期舉辦的 “中國農業高新科技成果博覽會” 都落地陜西楊凌。按照費孝通的說法,“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而陜西應該是鄉土中國的腹地。因此,幾代文學陜軍大多以鄉村敘事為主。有人甚至由此認為文學陜軍是一支農民大軍,缺乏現代性。但筆者認為,在當今中國文壇,文學陜軍真正集中書寫了中國式現代化進程,尤其表現在鄉村敘事方面。
從魯迅、沈從文到新中國成立后的文學陜軍,構成了現代鄉土敘事的一條主線。僅就文學陜軍而言,如果將其書寫的中國鄉村社會現代化的進程,按照時間順序連接在一起,便可清晰地呈現出一條鄉土中國現代化的道路。陳忠實的《白鹿原》從廢除帝制后中國鄉村社會的變革寫起,一直寫到新中國成立;柳青的《創業史》從新中國農村變革寫起,書寫了鄉土中國走上集體化道路的歷史過程;賈平凹的《古爐》和路遙的《在困難的日子里》書寫了 20 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鄉村社會的真實境況。
路遙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書寫了改革開放初期鄉村青年在城鄉交叉地帶的奮斗史;賈平凹的《秦腔》《高興》等書寫了改革開放進入深水區之后,鄉村社會的深刻變化和農民與城市的關系;而楊爭光的《從兩個蛋開始》則從新中國成立一直寫到改革開放之后中國鄉村社會的一系列變化。作家們書寫的這條道路盡管彎彎曲曲,但卻真實地呈現了中國鄉村社會一步步從傳統的農耕文明走向現代文明的完整歷史。這正是一條鄉土中國的現代化之路,其中揭示的中國人的心理和精神歷程蘊含著中國文學特有的現代性。因此可以說,真正完整書寫了鄉土中國現代化、接續了中國文學現代性的,恰恰是被視為 “鄉土作家” 的文學陜軍。
三、陜西經驗生成的歷史文化淵源
陜西經驗生成的最直接原因,當然是前述的延安文藝和《講話》精神,而文學陜軍整體上所接續的精神稟賦和傳統文脈則更加深遠。中國文學史上的幾大重要文學傳統,幾乎都淤積在陜西的厚土之中,像巖礦一樣一層一層深埋在地下,卻滋養著土地上的生靈。
首先,無論是從史料還是從傳說中都可獲知,我們今天書寫文學作品,從古沿用至今的文字 —— 漢字,其誕生與陜西頗有淵源。在史料和傳說中,最早造字的倉頡,是黃帝的左史官,出生于陜西白水史官村。“倉頡造字” 盡管是傳說,卻也是史料中記載的關于漢字誕生的歷史依據,也是漢字發展的第一塊里程碑。而漢字發展的第二塊里程碑也立在陜西,那就是秦始皇統一六國文字,即所謂 “書同文”,完成了文字國家化、規范化的過程。
用漢字表達思想、抒發感情、書寫文學作品則是從西周開始的。公元前 1046 年,西周王朝建都鎬京(今西安市內),周公旦在這里制禮、作樂、修史,便有了后來被孔子編輯成書的《詩經》《尚書》《周禮》《樂經》《易經》中的絕大部分內容。其中,設 “大司樂”,立民間采詩制度,使《詩經》成為中國文學的第一大文脈,并由此開啟了中華文脈。
以《楚辭》為代表的另一條文脈緣起于長江流域,但以楚人為首的多支秦末農民起義大軍,先后涌入關中,占領咸陽,最終由劉邦建立了漢王朝,定都長安(今西安)。楚人入主關中,自然將緣起于長江流域的楚歌楚舞引入長安,一時長安城里、漢帝宮中楚歌楚舞彌漫,這一情景被刻在漢畫像石中至今可見。更有甚者,當地文人紛紛仿作《楚辭》,實則是將產生于長江流域的《楚辭》與產生于黃河流域的《詩經》相融合,最終形成了一種新的文體 —— 漢賦。劉熙載在《藝概》中說 “長卿《大人賦》出于《遠游》,《長門賦》出于《山鬼》;王仲宣《登樓賦》出于《哀郢》;曹子建《洛神賦》出于《湘君》《湘夫人》,而屈子深遠矣”。事實上,漢賦受《楚辭》影響,從宋人朱熹到近人郭沫若、陸侃如也有論述。由此可見,即使形成于長江流域的《楚辭》傳統也匯入了關中長安,并促成了漢賦的誕生。
漢朝延續并擴大了周朝的民間采詩制度和秦朝的樂府,又加設了 “太樂府”,大量從民間采集歌謠,并與文人詩歌融合,形成了樂府詩歌傳統。這一傳統賴以生成的 “采詩制度”,盡管是當時的統治者為了觀察民情所設,但在客觀上為文人創作開辟了源頭活水。這種文人創作汲取民間文藝的傳統,直到延安時期才成為一種自覺的文藝思想,成為文人創作追求民族化、大眾化的一條坦途。由此可以發現,文人創作與民間文藝相互融合之路的幾個標志性的里程碑,都樹立在陜西這塊古老的土地上。
漢朝為中國文學特別是中國文學的敘事傳統,開辟的又一條重要文脈,便是以司馬遷的《史記》為代表的史傳傳統。被魯迅譽為 “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的《史記》,盡管是一部 “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的史書,卻對文學敘事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以至讓后世的小說、戲劇、影視的敘事藝術較難超越。而司馬遷則是生長于陜西韓城,其任職、撰述《史記》均在長安。
及至唐朝,中國的幾大文脈均臻于成熟,且又隨著絲綢之路上的交流,吸納了外來的佛教和西域文化的諸多元素,以及音樂、舞蹈、繪畫、書法等其他藝術門類的養分,最終融合為一座人類歷史上空前的文學高峰 —— 唐詩。僅據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完成編校的《全唐詩》收錄,就有詩歌 48900 余首,詩人 2200 余位,共計 900 余卷,僅目錄就有 12 卷。這些詩人當然出自各地,但大多云集長安,使長安成為人類詩歌文明的重鎮。
唐以后的陜西盡管隨著政治中心的東移不再孕育新的文脈,但以宋代的張載、藍田四呂,明代的馮從吾,清代的李二曲,以及近代的劉古愚、牛兆濂等為代表的關學,不僅發展了儒家學說,還開啟并推動了宋明理學的發展。他們提出并踐行了 “橫渠四句” 所倡導的中國文人的責任擔當和精神稟賦,制訂了以《呂氏鄉約》為代表的鄉村自治方略,為中國鄉村社會的治理與發展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方案,對陜西乃至中國社會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這種影響一直延伸到了近現代。
近代的于右任、張季鸞、吳宓、李儀祉等重要歷史人物,都同出于關學大儒劉古愚門下。關學對當代的文學陜軍的影響既是深層次的,也是直接的。陜西作家對鄉村社會的關注和書寫、對社會責任和歷史使命的擔當,以及陜西經驗中的 “深扎” 傳統、現實主義精神、與傳統文化的血脈聯系,都與關學有著深層次的、潛在的聯系。陳忠實的《白鹿原》是受到 “藍田四呂” 的《呂氏鄉約》的直接啟示,才萌發了寫作動機的。《白鹿原》中的朱先生更是以關學大儒牛兆濂為原型的。
這些一層又一層的文學、文化傳統,淤積在陜西的沃土之中,形成了揮之不去的文學氣場,直接或間接地形塑著當代陜西的作家、藝術家,成為陜西經驗形成的重要的歷史文化淵源。
李 震,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202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