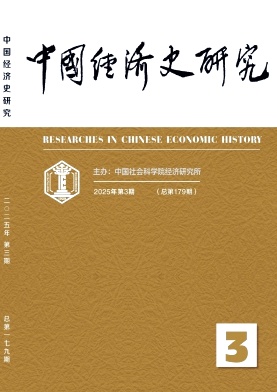中國經濟史研究雜志投稿格式參考范文:元代紙幣的編號及作用——以“料”為核心
時間:
中國古代,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金屬貨幣逐漸無法滿足市場交易和國家財政需求,從宋金時期開始,官方發行紙幣,與金屬貨幣并行。紙幣進入流通領域,發揮了巨大作用,但也在金朝末年造成了嚴重的惡性通貨膨脹。到元代,官方決定全面使用紙幣,故而吸取前代的經驗教訓,設計了全新的、更為完善的貨幣制度,紙幣從分界、定額、限地域,發展到不分界長期流通、不限定額發行、不限地域全國使用,紙幣的發行、流通和回收制度得到逐漸完善。
關于元代鈔法的運行機制,已有不少學術成果,但對于元代紙幣制度的整體設計還沒有完全明了,其中的編號制度仍是目前的研究空白。編號與紙幣的發行、回收體系息息相關,對于紙幣編號的討論或可以推進我們對元代紙幣制度的認識深度。
元代紙幣的編號又稱 “料號”,其中最關鍵的是 “料” 這一概念。元代鈔法中有 “料鈔”“料號”“料例”“配料” 等多個與 “料” 相關的專門名詞,雖然關于鈔法的研究論著經常提及這些詞或引用包含這些專名的史料,但很少對其進行解釋和研究,與之相關的制度亦未有過深入討論。截止目前,學界僅有陳高華、張帆、劉曉《〈元典章・戶部・鈔法〉校釋》對這些概念做過注釋,然而限于體例,未能專門討論與這一系列概念相關的制度設計和運行機制。本文擬探討元代鈔法中與料相關的一系列概念和元代紙幣編號的制度及其運行機制。
一、料鈔和料號
之前學界提及 “料鈔” 和 “料號” 兩個概念的成果較多,這組概念也比較好理解。料鈔即新鈔,元代史料中經常記錄用昏鈔兌換料鈔的相關規定,根據上下文很容易明白,即指用已經破舊的紙幣兌換新印紙幣。但新鈔為什么被稱為 “料鈔”,《〈元典章・戶部・鈔法〉校釋》“料鈔” 條指出:“‘料’是宋元時期用于成批、成組物品計量的量詞,一料意謂一批。” 蓋因新印紙幣成批印制和運輸到兌換紙幣的機構 —— 行用庫,故而稱之為 “料鈔”。料號是字料和字號的合稱。《〈元典章・戶部・鈔法〉校釋》“字號” 條校注詳細說明:“元鈔承襲金制,在鈔紙中部兩側分別印有‘字料’和‘字號’。‘料’是大的成批印造單位,‘號’是紙鈔的具體編號,皆用《千字文》字序排列,將每張紙鈔定位為某字料某字號。”《南臺備要》“建言燒鈔” 至正十一年(1351)六月十七日條:“照得元配料內俱有合用印帖,一切于上開寫,…… 玄字幾號至元貫佰壹料壹仟張。” 據此每料應為 1000 張。
據《金史・食貨志》載,交鈔之制,外為闌,作花紋,其上衡書貫例,左曰 “某字料”,右曰 “某字號”,料號外篆書曰 “偽造交鈔者斬,告捕者賞錢三百貫” 可知金代紙幣已有料號。但目前未發現金交鈔實物,僅有鈔版,無法確知金代料號是否亦用《千字文》中的文字表示,亦難以推斷金代料號的編制原則。
元代長期行用的中統鈔和至元鈔,形制與金代交鈔比較接近。李逸友《元代紙幣啟蒙篇(一)》一文中描述了現存出土中統鈔、至元鈔上的字料和字號,在《中國古鈔圖輯》中也可見到相關圖片。紙幣上半部分中間為貫佰,即面額,左側為字料,右側為字號,均用《千字文》中的文字編號。
《元典章・戶部・鈔法》“添工墨鈔” 條顯示,世祖統治前期,料號均由漢族士人手工填寫,后來則逐漸改變。根據出土的元代紙鈔實物來看,世祖時期發行的中統元寶交鈔,字料為字戳加印,字號為手寫;至元通行寶鈔和至正年間發行的中統元寶交鈔,字料和字號均為字戳加印。這樣既減少工作量,降低工作門檻,也可以減少舞弊行為。
填寫或加蓋料號的工作,很可能在倒換昏鈔時由庫子當場完成。黑城遺址出土了一部分未加蓋字料、字號的紙幣,大概是行用庫尚未進行兌換的料鈔。
學者大都把料號看作元代紙幣的編號,但這個編號與今天我們所熟知的人民幣編號有所不同。每張人民幣都有字母和數字組成的獨一無二的十位編號。由于絕大部分編號由前兩位的兩個字母和后八位的八個數字組成理論上共有 26×26×10⁸種排列組合足夠給每張人民幣提供一個編號,但元代紙幣的編號只有字料和字號兩個漢字,這兩個漢字均來自《千字文》。字料和字號均使用《千字文》中的單字,相互搭配的情況下,最多有 100 萬組不同編號。
元代長期行用的紙幣有中統鈔和至元鈔兩種。中統元年(1260)開始發行中統鈔,早期發行量較小,中統年間最高年發行量為 8 萬錠,至元十二年之前,最高發行量不過 40 萬錠。至元十三年南宋地區納入元朝統治,紙幣發行量劇增,至元二十三年高達 218 萬余錠。至元二十四年鈔法改革,發行價值為中統鈔 5 倍的至元鈔,停止發行中統鈔。至元鈔年發行量從 20 萬左右到 200 余萬錠不等,年平均發行量大約是 100 萬錠。至大四年(1311)后,中統鈔再次開始發行,作為小額輔幣與至元鈔同時使用,大多數年份發行 10 萬錠。
中統鈔面值有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一貫、二貫共 10 等,一套不同面額的中統鈔面值共 4210 文。至元鈔有二貫、一貫、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五十文、三十文、二十文、十文、五文共 11 等面額,一套不同面額的至元鈔面值共 4215 文。1 錠為 50 貫,1 貫為 1000 文。假定一年所發行紙幣的每種面額的張數相同(實際上通常要求多發小額零鈔,四六配搭,總張數更多),那么 100 萬錠中統鈔約為 1 億 1876 萬余張,100 萬錠至元鈔約為 1 億 3048 萬余張。即使只發行 50 萬錠中統鈔,也需印制 5938 萬余張紙幣,使用由《千字文》單字組成的 100 萬組編號,絕不可能做到每張紙幣互不重復。一年印制 100 萬錠中統鈔的情況下,每組編號最少需 118 張紙幣共用,若為至元鈔則每年發行的新鈔最少需 130 余張共享同一編號。
實際上,100 萬組編號最多只能讓 100 萬張紙幣獲得每張獨一無二的編號,假定這 100 萬張紙幣都是中統鈔,且每一種面額的數量相同,市場上流通的紙幣總額大約是 8000 余錠。如果都是至元鈔,則市場流通貨幣總額只能是 7000 余錠。中統鈔發行量最小的年份是至元六年,共發行 22896 錠;發行至元鈔最少的年份是至元三十一年,共發行 193706 錠。而且元代紙幣不分界,不限制流通地域,任何一年發行的紙幣都可以在全國范圍內長期流通。也就是說,用兩個來自《千字文》的漢字表示字料和字號,這種方式組成的貨幣編號,即使在元代發行量最少的時候,也不夠確保每張紙幣獲得一個獨一無二的編號,因此一定會有大量紙幣編號重復。隨著紙幣不斷發行,每個編號可能會有成千上萬張紙幣共享。那么,元代怎么給紙幣分配編號呢?由字料和字號兩個漢字組成的料號,在元代鈔法體系中究竟起什么作用?
實際上,現在國內出土的元代紙幣實物非常豐富,除了西藏、甘肅、寧夏、湖南等地傳世和出土的少量紙幣之外,在內蒙古自治區阿拉善盟額濟納旗黑城遺址先后出土紙幣 500 余張,青海格爾木農場出土紙幣 400 余張。在這些成批出土的紙幣中,應有很高概率包含同批印制相同面額的紙幣,但考古報告中很少提及出土紙幣的字料和字號。如能根據實物來查看元代紙幣的料號編排方法,將會很容易地解決這個問題。可是目前為止我們無法得知成批出土的元代紙幣每張的料號,因此暫時只能根據史料進行推測。為了探究元鈔料號的編制方法和功能,需要從料例和配料入手。
二、料例與配料
之前關于元代鈔法的論著中較少提到料例和配料,但《〈元典章・戶部・鈔法〉校釋》中對這兩個專名做了解釋:“‘料例’一詞在《元典章》中多見,當系指一組(一‘料’)紙鈔的面額情況,或指對大量紙鈔根據不同面額進行分類、配組(稱為‘配料’)的狀況。” 這條校注已經指出,料例與紙幣的面額相關,但沒有說明所謂 “一組紙鈔的面額” 具體是什么情況。實際上,元代史料中經常直接用料或料例來表示紙幣的面額。如《南村輟耕錄》記載至元通行寶鈔的 11 等面額,題目為 “至元鈔料”,“至元印造通行寶鈔,分一十一料:貳貫、壹貫、伍伯文、叁伯文、貳伯文、壹伯文、伍拾文、叁拾文、貳拾文、壹拾文、伍文。” 又如《元典章》“禁治茶帖酒牌” 條,監察御史請求多發行 11 等面額之內的 6 種較小面額零鈔,解決民間小額貨幣不足的問題。中書省則要求各地鈔庫如遇到缺少零鈔的情況,應 “開坐各各料例”,也就是寫明缺少的各種紙幣面額,提前派官前往大都領取。
由于料即指面額,文書中也可以看到將大額紙幣稱為 “上料大鈔”,將小額紙幣稱為 “下料零鈔” 的情況。由此可知,雖然在料鈔和料號中,料指代數量或編號,并引申具有新鈔的含義。但在料例中,“料” 指代面額。在 “配料” 一詞中,“料” 既與編號相關,也與面額相關,這是因為元代紙幣料號中的字料這一編號與面額掛鉤,是相互吻合的。
從出土實物來看,同一面額的紙幣不一定使用同一個漢字作為字料,《中國古鈔圖輯》收入的多種紙幣可看出相同面額紙幣之間用作字料的漢字有所區別。字料與面額的匹配關系應是多對一的,甚至有可能隨著年份和批次不同而改變。
關于 “配料”,《〈元典章・戶部・鈔法〉校釋》中已提出 “或指對大量紙鈔根據不同面額進行分類、配組”。但究竟如何分類、配組,以及這樣做的意義,還有繼續討論的必要。要理解配料的方式和作用,最重要的史料是《南臺備要》“建言燒鈔” 條。
這是一件元朝后期的文書。當時偽鈔泛濫,而且經常有人偽造昏鈔,但并不使用,而是與行用庫官員勾結,用偽鈔換取新鈔。偽造的昏鈔按照規定統一被燒掉后,犯罪證據就被順利銷毀,不會留下蛛絲馬跡,因此官府在昏鈔倒換和燒鈔環節設置了很多防范和檢查手段。根據這件文書,行用庫庫子收到昏鈔之后,需要先 “配料鈔錠”,然后在 “元配料內” 附上 “合用印帖”。文書中提到的印帖包括如下內容:(1)“行用庫子王諒配料鈔錠”;(2)“玄字幾號至元貫佰一料一千張”;(3)“盛寧縣雜物行人某 (筆者注:此處有簽名)”;(4)“配料官三原縣主簿不嚴達實,庫子王諒,貼庫門諒 (筆者注:此處有三人簽名)”;(5)“年月日”。
上引印帖中的 “玄字幾號至元貫佰一料一千張” 這一信息至關重要,由此可知,一批紙幣配料完成之后,應為字料、面額相同的 1000 張,這證明了元代紙幣的字料與面額掛鉤,相同面額的紙幣字料編號相同,否則印帖無法以此種形式書寫。正由于這一制度設計,“料” 在元代的紙幣體系中既表示編號,又表示面額。而從印帖的這種形式來看,配料時很可能還需要把字料和字號都相同或者相同字料幾種字號的紙幣放在一起,湊成 1000 張。由于元代料號數量不多,如果字料與面額掛鉤的話,每種面額的紙幣字號將大量重復。此外,如前所述,元代紙幣制度運行一段時間后,字料和字號全都改為用加蓋印戳的方式填寫,則可能字號與地區有一定關系。如果每個地區的行用庫都準備全套 1000 多個漢字的印戳,似乎數量過大,也沒有必要;每個地區僅分配少量漢字印戳用來加蓋料號,則可能更為合理。在同一地區料號數量有限的情況下,把相同料號,或字料相同、幾種字號的紙幣配成 1000 張,做到這一點難度并沒有那么大。
寫好印帖之后,還要設置一個勘合簿,由庫使掌管,勘合簿上需要再次登記料號、配料官、庫子、貼庫、行人等信息,要與印帖完全符合。一旦在燒鈔之前檢查昏鈔時,發現其中混入偽造的昏鈔,就要對照配料內的印帖、庫使手中保管的勘合簿,查明偽鈔在哪個環節混入,落實責任人,由其賠償。上引 “建言燒鈔” 文書內提到,這些昏鈔并沒有經過具有專業技能的行人查驗真偽,只是由庫官、庫子和配料官密封標記之后,才讓 “行人辯驗”,雖然印帖與勘合簿信息相符,但燒鈔時查出的偽鈔,“并不是元檢之數”,而且不像那些符合規定的堪燒昏鈔背面 “有行人小印記事”,由此可知是庫官、庫子和配料官相互串通,把偽鈔混入昏鈔之中,并瞞過了查驗的行人。因此要求倒換昏鈔配料之后,需要 “檢閘上料行人” 負責檢查大額紙幣,因很少有人偽造小額零鈔,故而專業行人只需要檢查上料大鈔,并標記封存,防止行用庫之內的官員串通作弊。
配料勘合這一流程,在元曲《上高監司》中被描述為 “逐戶兒編褙成料例來,各分旬將勘合書”。編褙成料例,即配料鈔錠,書寫勘合,即開寫印帖和勘合簿。《上高監司》中把 “配料” 寫作 “編褙成料例”,由此亦可知配料時主要以料例 (即面額) 為標準。想象一下,元代倒換昏鈔的行用庫大概類似于今天的銀行柜臺,收到不同面額的昏鈔,蓋上退印之后放入不同的盒子。一種面額紙幣積累至 1000 張時,將其配成一料,登記料號,開寫印帖,密封待燒。
從史料來看,配料很可能是至元二十四年鈔法改革之后出現的新要求。《元典章・戶部・鈔法》“常川開平準庫條” 記錄了至元二十年倒換昏鈔的流程,至元二十年,行用庫收入的昏鈔并不進行配料,只是到了起解日,把昏鈔送往統一地點燒毀的時候,才由 “提點官封記樁入包子”,然后把鈔包的編號和個數、提點官的職位姓名和押解庫官的姓名申報給戶部即可。天歷二年 (1329) 之前,每年發行的鈔數都有明確記載,但至元二十五年時,桑哥批評 “中統鈔行垂三十年,省官皆不知其數”。所謂 “不知其數”,指的應是不知道市場上流通的中統鈔數,大概在至元二十四年鈔法改革之前,行用庫并不對回收的昏鈔進行配料和登記,無法統計回收了多少昏鈔,因此對市場上仍在流通的紙幣數量難以估計。
元貞二年 (1296) 的 “起解昏鈔違限罪名” 條初次提到 “配成料例” 的規定,這件文書中使用 “照得” 一詞,可知提及的是之前已有的規定。由此來看,配料制度是至元后期建立起來的,可能為至元二十四年鈔法改革的內容之一。通過配料,可以很方便地統計所回收昏鈔的數額,因此能夠解決 “中統鈔行垂三十年,省官皆不知其數” 的問題。元代的料號這一形式雖然繼承自金代,但金代紙幣料號的功能應是用于分界,元代紙幣不分界,早期料號只有標志面額、兌換時對應新舊紙幣等作用。但在至元二十四年鈔法改革設計出配料制度后,料號就可以用來統計紙幣數量。
除統計數量外,料號還有關防作用。元代制作偽鈔的方法之一是挑改紙幣面額,將小額紙幣偽造成大額,再倒換同面額的新鈔。紙幣的面額與字料掛鉤,挑改者若要做到天衣無縫,在改面額的同時,還需要改字料。如果偽造者不知道面額與字料有關,或不知道哪些字料對應哪些面額,偽造時就很容易出現漏洞。因此《通制條格》“倒換昏鈔” 條提出辨驗偽鈔的程序。
由于挑改鈔額者勢必將數額改大,因此料例相同的情況下,面額較大者即為偽鈔。根據前引《南臺備要》“建言燒鈔” 條可知,在燒毀昏鈔的過程中,料號和配料制度也起到了重要的關防作用。在燒鈔時,燒鈔官查出有偽鈔 “并不是元檢之數”,正是因為有了嚴格的配料制度,才很容易地發現混入正規昏鈔的 “不堪短少” 紙幣。
三、結論
元代鈔法系統中出現了料鈔、字料、料號、料例、上料、下料、配料等多個與 “料” 相關的專名,理解這些名詞的含義,有助于我們了解元代鈔法的運行機制。“料” 的含義很豐富,本意是估量、度量,在宋元時期用于成批、成組物品計量的量詞,在這個意義上,料鈔指的是成批印制的新鈔,料號即指一批紙幣的編號,這種編號由字料和字號兩個來自《千字文》的漢字組成。料例指紙幣的面額,這是因為紙幣在印制分組的時候,同一料紙幣的面額相同,類似于今天銀行會把相同面額的一批紙幣打包成一捆。因此,在元代鈔法中,料與編號、面額兩個含義相關,而元代紙幣的料號和面額也相符合。根據史料來看,元代一料紙幣為 1000 張,這 1000 張紙幣的字料相同。配料就是指在回收昏鈔時,把字料相同的紙幣配成一料,密封后統一燒毀。配料的情況需要在印帖和勘合簿上進行登記,既方便統計回收昏鈔的總額,也有防偽作用。元代的配料制度并不是從一開始就有,而是逐漸發展起來的,體現出制度在運行中的不斷完善。
李鳴飛,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202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