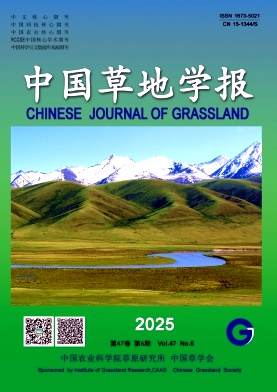中國草地學報雜志投稿格式參考范文:祁連山國家公園不同類型草地植被及土壤特征研究
時間:
引言
祁連山橫跨甘肅和青海兩省,位于青藏高原、黃土高原、內蒙古高原的交匯地帶。1988 年,國家批準設立了甘肅祁連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2017 年,祁連山國家公園體制試點工作全面啟動;2020 年,我國成立第一批國家公園,祁連山國家公園位列其中。祁連山國家公園總面積 50237 km²,其中甘肅片區占 68.5%,青海片區占 31.5%。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祁連山國家公園在畜牧業生產、區域生態平衡維護、生物多樣性保護、水源涵養、碳循環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祁連山國家公園內高山、溝谷和山間盆地交錯,復雜的地形孕育了溫性草原、高寒濕地、高寒荒漠、高寒草甸、溫性荒漠草原等不同的草地類型,這些草地在維持當地畜牧業生產及經濟發展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人類活動的增加,祁連山國家公園內草地面臨著生物多樣性降低、生產和生態功能退化、鼠害泛濫等諸多問題,威脅國家生態安全屏障的建設和保護,嚴重影響當地居民的生產和生活。對不同草地類型植被、土壤之間相互關系的研究可為解決草地退化問題提供基礎數據及參考。
土壤是草地生態系統的重要組分,不僅是植物獲取必需養分和水分的基本來源,同時也是各種動物和微生物的棲息地以及各種營養物質循環、能量流動的場所。現有研究資料表明,草地植被與土壤理化性質間存在一定的相互關系,植被的變化會引起土壤理化性質的改變,而土壤的變化又反過來影響地上植被。同時,微生物直接或間接參與土壤理化過程,并對氮、磷、鉀等營養物質的循環具有重要作用。近年來,對祁連山國家公園內草地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某種特定草地類型的植被及其與土壤特性之間的關系等方面,而對公園內不同草地類型植被差異及其與土壤特性和微生物之間的關系關注較少。青海省門源縣地處青藏高原腹地祁連山南麓,是祁連山國家公園重要的組成部分,擁有天然草地面積 45.77 萬 hm²,占全縣土地面積的 66% 左右,其中可利用天然草地面積 38.88 萬 hm²,約占草地總面積的 85%。但是,公園內不同草地類型植被、土壤特性和微生物的基礎數據尚不清楚。為此,本試驗對門源縣 4 種典型草地類型的植被、土壤特性及微生物進行調查分析,為不同草地類型的合理利用和生態保護提供科學建議,同時也為祁連山國家公園的生態治理提供基礎數據。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
研究區位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門源回族自治縣(門源縣)(100°55'28″~102°41'26″E、37°03'11″~37°59'28″N),屬于祁連山國家公園青海片區,地處青藏高原東北部,屬高原大陸性氣候,海拔 2388~5254 m。日照時間長、輻射強、晝夜溫差大,年均溫在 4℃以下,年均降水量 400 mm 左右。草地類型主要有高寒荒漠、高寒草甸、高寒濕地、溫性草原、山地草甸、低地草甸等。植被以毛茛(Ranunculus japonicus)、委陵菜(Potentilla chinensis)、嵩草(Kobresia myosuroides)、披堿草(Elymus dahuricus)等為主。
1.2 植物調查與土樣采集
2022 年 7 月,在門源縣選擇了討拉溝和硫磺溝這兩處具有代表性的地區,對高寒荒漠、高寒草甸、高寒濕地和溫性草原 4 種典型草地進行植被和土壤調查。在調查地區中,選擇各草地類型的代表性樣地,并在每種草地類型內設置 3 個相互間隔至少 10 m 的大樣方(10 m×10 m)作為重復。在每個大樣方內設置 3 個小樣方(1 m×1 m),利用針刺法測定植被的總蓋度,并測定樣方內植物的種類、覆蓋度和高度,取 3 個樣方的平均值作為一個重復;地上生物量通過在每個樣方內齊地面刈割 1 m×1 m 的地上植被稱鮮重獲取。同時,在每個樣地的小樣方周圍隨機取 5 鉆深度 0~20 cm 的土樣,并使用內徑 5 cm、容積 100 cm³ 的環刀采集土壤樣品 3 份,將大樣方內的 15 鉆土樣混合后作為一個重復。將混合的土壤樣品取 3 份分裝至 1.5 mL 的凍存管中,并立即轉移到低溫儲存箱中保存,隨后用干冰包裹送往上海派森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進行微生物分析。其余土樣帶回實驗室,經風干過篩后用于土壤理化性質的測定。
1.3 測定指標與方法
1.3.1 植物多樣性
(1)Nᵢ(第 i 個物種重要值)=(相對蓋度 + 相對多度 + 相對頻度)/3。
(2)物種 α 多樣性計算方式為以下 3 種:
Simpson 多樣性指數(D):D=1−∑(i=1 到 s) Nᵢ²;
Shannon−Wiener 多樣性指數(H):H=−∑(i=1 到 s) Nᵢln (Nᵢ);
Pielou 均勻度指數(P):P=H/lnS。其中,S 為樣方內物種數。
1.3.2 土壤理化性質
用濕篩法測定土壤團聚體;用環刀法測定土壤容重;用烘干法測定土壤含水量;用酸度計法測定 pH;用 K₂Cr₂O₇氧化−外加熱法測定土壤有機質;用半微量凱氏法測定全氮;用堿解氮擴散法測定速效氮;用 HClO₄−H₂SO₄消煮后,分光光度法測定全磷;用鉬銻抗比色法測定速效磷;用 NaOH 熔融−火焰光度法測定全鉀;用火焰光度法測定速效鉀。土壤孔隙度 =(1−土壤容重 / 土壤密度)×100%(土壤密度采用密度值 2.65 g/cm³)。
1.3.3 土壤微生物
土壤微生物中細菌使用引物 338 F(ACTCCTACGGGAGGCAGCA)和 806R(GGACTACHVGGGTWTCTAAT)擴增細菌 16S rRNA 的 V3−V4 區域;真菌使用引物 ITS5(GGAAGTAAAAGTCGTAACAAGG)和 ITS2(GCTGCGTTCTTCATCGATGC)擴增真菌 ITS 的 V1 區域。使用 Divisive Amplicon Denoising Algorithm 2(DADA2)進行序列分析,以過濾和去除數據中的疑問序列。DADA2 精確地推斷序列,從而產生擴增子序列變體(ASV)。DADA2 不再以相似性聚類,僅執行 100% 相似性的去重復或聚類。
1.4 數據處理
利用 SPSS 26.0 軟件對數據進行 Pearson 相關性和單因素方差分析,用 Excel 2016 和 Origin 2023 軟件作圖。
2 結果與分析
2.1 不同草地類型的植被特點
高寒荒漠以景天科(Crassulaceae)、莎草科(Cyperaceae)植物為主,優勢種有青海景天(Sedum tsinghaicum)、矮嵩草(Kobresia humilis)等。高寒草甸、高寒濕地主要以莎草科、禾本科(Gramineae)植物為主,優勢種主要有高山嵩草(Kobresia pygmaea)、苔草(Carex spp.)、垂穗披堿草(Elymus nutans)、珠芽蓼(Polygonum viviparum)、毛茛等。溫性草原莎草科植物減少,而以禾本科植物為主,優勢種有草地早熟禾(Poa pratensis)、針茅(Stipa capillata)等。
高寒荒漠草地植被蓋度和地上生物量最低,顯著低于高寒草甸(P<0.05)。高寒草甸植被蓋度最高,達 98.83%,顯著高于高寒荒漠、高寒濕地、溫性草原(P<0.05)。高寒草甸地上生物量最高,達 348.67 g/m²,顯著高于其余 3 種草地類型(P<0.05)。高寒草甸植物群落的 Shannon−Wiener 多樣性指數最高,為 2.53,顯著高于高寒荒漠和溫性草原(P<0.05),但與高寒濕地沒有顯著差異。高寒濕地的 Simpson 多樣性指數顯著高于高寒荒漠和溫性草原。4 種不同草地類型植物群落的 Pielou 均勻度指數沒有顯著差異。
2.2 不同草地類型的土壤物理性質
4 種不同草地類型中,高寒荒漠的土壤以 <0.25 mm 和> 2 mm 粒級的團聚體占比最高,為 62.27%。高寒濕地和高寒草甸的土壤均以 > 2 mm 粒級的團聚體為主,分別為 83.60% 和 68.88%。而溫性草原的土壤則以 < 0.25 mm 粒級團聚體為主。其中 > 2 mm 和 0.5~0.25 mm 粒級團聚體含量在 4 種草地類型間均有顯著差異(P<0.05)。2~1 mm 粒級團聚體含量在高寒濕地與高寒荒漠、高寒草甸間有顯著差異(P<0.05)。1~0.5 mm 粒級團聚體含量在高寒荒漠和溫性草原與高寒草甸和高寒濕地間有顯著差異(P<0.05)。<0.25 mm 粒級團聚體含量在溫性草原與高寒濕地和高寒草甸間有顯著差異(P<0.05)。
高寒濕地土壤孔隙度最高,為 74.35%,與高寒草甸沒有顯著差異,但顯著高于高寒荒漠和溫性草原(P<0.05)。高寒荒漠的土壤容重最高,為 1.27 g/cm³,高寒濕地的土壤容重最低,為 0.68 g/cm³。不同草地類型土壤含水量差異顯著(P<0.05),呈高寒濕地> 高寒草甸 > 溫性草原 > 高寒荒漠。
2.3 不同草地類型的土壤化學性質
高寒草甸的土壤速效氮和土壤全氮含量最高,分別為 30.49 mg/kg 和 7.54 g/kg,高寒荒漠的土壤速效氮和土壤全氮含量最低,分別為 14.48 mg/kg 和 2.01 g/kg,高寒草甸的土壤速效氮、全氮含量與高寒荒漠和溫性草原的土壤速效氮、全氮含量有顯著差異(P<0.05)。高寒草甸的土壤速效磷和全磷含量最高,分別為 4.67 mg/kg 和 0.99 g/kg,高寒荒漠的土壤速效磷含量最低,為 2.29 mg/kg,溫性草原的土壤全磷含量最低,為 0.48 g/kg。高寒草甸的土壤速效鉀含量最高,為 259.42 mg/kg,高寒荒漠的土壤速效鉀含量最低,為 120.42 mg/kg。高寒荒漠的土壤全鉀含量最高,達 21.14 g/kg,高寒草甸的土壤全鉀含量最低,為 17.11 g/kg,且高寒荒漠與高寒草甸的土壤全鉀含量具有顯著差異(P<0.05)。高寒草甸的土壤有機質含量最高,為 150.73 g/kg,而高寒荒漠的土壤有機質含量最低,為 39.81 g/kg。溫性草原的土壤 pH 值最高,為 7.80,高寒濕地的土壤 pH 值最低,為 6.46。
2.4 不同草地類型土壤細菌群落特征
高寒荒漠、高寒草甸和溫性草原土壤細菌的 2 個指數之間均沒有顯著差異。高寒濕地土壤細菌的 Shannon−Wiener 多樣性指數和 Pielou 均勻度指數最低,顯著低于高寒荒漠、高寒草甸和溫性草原(P<0.05)。
高寒荒漠、高寒草甸、溫性草原土壤的細菌群落中,放線菌門(Actinobacteria)、變形菌門(Proteobacteria)、酸桿菌門(Acidobacteria)、綠彎菌門(Chloroflexi)相對豐度較高,其他 6 個門的相對豐度較低。而高寒濕地土壤的細菌群落中,除上述 4 個門外,擬桿菌門(Bacteroidetes)的相對豐度也較高,其余 5 個門的相對豐度較低。
不同草地類型土壤細菌群落 PCoA 分析表明,在 PCo1 軸上,高寒濕地和溫性草原兩組的樣本點投影距離較近,而高寒荒漠組的樣本點在 PCo1 軸上的投影距離這兩組較遠,即在 PCo1 維度上,溫性草原與高寒濕地的細菌群落組成結構相似,而在這一維度,高寒荒漠的細菌群落組成結構與這兩種草地類型間差異較大,此外,高寒草甸和高寒荒漠的細菌群落組成結構在同草地類型的不同樣地間表現出差異,而高寒草甸下這種差異更大(解釋度為 23.1%)。在 PCo2 軸上,高寒荒漠、高寒濕地、溫性草原 3 組的樣本點間投影距離較遠,而高寒草甸組的樣本點在 PCo2 軸上的投影仍舊在不同樣地間表現出差異,在 PCo2 維度上,在同草地類型的不同樣地間細菌群落組成結構較為接近(解釋度為 19.9%)。置換多因素方差分析(Permutational MANOVA, Adonis)表明不同草地類型對土壤細菌群落影響顯著(P=0.001)。
對土壤細菌群落作層次聚類分析可知,高寒荒漠和高寒草甸間細菌群落組成相對接近,且與溫性草原下的細菌群落組成差異較大,而與高寒濕地下的細菌群落組成差異最大。
2.5 不同草地類型土壤真菌群落特征
4 種草地類型土壤真菌的 Shannon−Wiener 多樣性指數范圍區間為 4.72~6.43,Pielou 均勻度指數范圍區間為 0.53~0.72,但各樣地間均沒有顯著差異。
在高寒荒漠、高寒草甸、高寒濕地、溫性草原 4 種草地類型的土壤真菌群落中,羅茲菌門(Rozellomycota)、毛霉菌門(Mucoromycota)、壺菌門(Chytridiomycota)和球囊菌門(Glomeromycota)的相對豐度較低,而子囊菌門(Ascomycota)、擔子菌門(Basidiomycota)和被孢霉門(Mortierellomycota)的相對豐度較高。
在 PCo1 軸上,溫性草原和高寒濕地的樣本點投影距離較近,而高寒荒漠的樣本點在 PCo1 軸上的投影距離這兩組較遠,即在 PCo1 維度上,溫性草原與高寒濕地草地的真菌群落組成結構相似,而在這一維度,高寒荒漠的真菌群落組成結構與這兩種草地類型的真菌群落組成結構差異較大,此外,高寒草甸的真菌群落組成結構在同草地類型的不同樣地間表現出較大差異(解釋度為 13.4%)。在 PCo2 軸上,溫性草原、高寒草甸和高寒荒漠的樣本點間投影距離較近,而高寒濕地的樣本點在 PCo2 軸上的投影離這 3 組較遠,即在在 PCo2 維度上,溫性草原、高寒草甸與高寒荒漠間真菌群落組成結構較為接近,而高寒濕地的真菌群落組成結構與之差異較大,在 PCo2 維度上其真菌群落組成結構更接近高寒草甸(解釋度為 9.1%)。置換多因素方差分析表明不同草地類型對土壤真菌群落影響顯著(P=0.001)。
對土壤真菌群落作層次聚類分析可知,溫性草原和高寒濕地的土壤真菌群落組成較為近似,而高寒草甸下來自不同樣地的兩組樣本間土壤真菌群落組成差異較大。
2.6 植被特征與土壤理化性質及土壤微生物多樣性的相關性
植被總蓋度與土壤全鉀、土壤容重呈極顯著負相關(P<0.01),與土壤全磷、土壤速效鉀呈顯著正相關(P<0.05),與土壤全氮、土壤速效氮、土壤有機質、土壤孔隙度和土壤含水量呈極顯著正相關(P<0.01)。植被地上生物量與速效氮、速效鉀和總蓋度呈極顯著正相關(P<0.01),與全鉀呈極顯著負相關(P<0.01)。細菌 Shannon−Wiener 多樣性指數與土壤的容重、含水量、孔隙度具有極顯著關系(P<0.01)。真菌 Shannon−Wiener 多樣性指數與土壤速效鉀具有顯著關系(P<0.05)。
3 討論
3.1 不同草地類型植被特征
土壤質量既影響植物生長發育,又影響草地生產力。本研究中祁連山不同草地類型植物群落的結構和組成各不相同,其植被蓋度、物種數量、地上生物量等植被特征均有差異。地上生物量反映了植被的生長狀況,是草地生產力的直觀體現。本試驗中地上生物量與蓋度極顯著正相關(P<0.01),其中高寒濕地的植被蓋度高于溫性草原,但地上生物量卻顯著低于溫性草原(P<0.05),與這兩種草地類型的優勢種的高度有關。高寒濕地優勢種主要為珠芽蓼、矮嵩草等低矮植被,平均株高低于溫性草原的草地早熟禾與針茅,導致高寒濕地雖蓋度較高但地上生物量較低。與溫性草原相比,高寒草甸植被長勢較好,土壤營養成分含量更高,物種更豐富,且在長期的演替過程中形成了抗干擾能力較強的穩定群落,地上生物量與植被蓋度高于其他草地類型,優勢種也從禾本科的針茅、早熟禾以及由于草地退化入侵的狼毒等毒雜草轉變為莎草科的矮嵩草、蓼科的珠芽蓼等。植被蓋度隨物種豐富度的提高而增加,植被蓋度、物種豐富度和地上生物量的差異導致凋落物的種類和數量不同,進而使土壤的營養成分產生差異,使高寒草甸土壤有機質、土壤全氮含量等也隨之升高。
3.2 不同草地類型土壤理化特性
土壤理化特性與氣候條件、植被類型、海拔高度等因素息息相關。土壤含水量會對土壤 pH 產生影響,張苗苗等研究表明,不同草地類型土壤 pH 差異較小,溫性類草地土壤 pH 值通常高于高寒類草地土壤。在本研究中,高寒草原和高寒荒漠具有更高的土壤 pH,其原因可能與土壤含水量相關。高寒荒漠降水少,土壤含水量低,氣候干旱以及大土壤蒸發量使土壤深處的鹽離子隨水分蒸發到土壤上層,加之降水量少導致的土壤中氫離子來源少,造成土壤 pH 偏高。土壤團聚體是由顆粒、粘土礦物、有機質等通過各種力和物質粘結在一起形成的結構性單元,土壤團聚體的形成與生態環境、植被覆蓋等因素密切相關。本研究中高寒荒漠土壤 > 2 mm 粒級的大團聚體占比最高,達到 38.42%,比 < 0.25 mm 粒級的微團聚體占比高,與前人研究結果并不一致,這可能與土質有關,高寒荒漠裸地面積大,水蝕、風蝕作用強,加之凍融加劇和草食動物踐踏導致土壤微團聚體破碎形成游離態粉粒、黏粒,而游離態粉粒、黏粒的增加使大團聚體隨之增加。
土壤作為生物與環境聯系的基質,含有大量植物生長所需的營養物質,對植物的生長發育至關重要,可直接影響草地群落的組成。本研究中土壤全磷含量均偏低,可能是由于高寒地區土壤全磷主要來源于礦物的風化作用,這直接導致了生態系統所具有的磷從一開始就是固定的,并且即使是非常微小的損失也難以得到補充。同時,磷酸鹽在堿性土壤中可溶性低,較難淋溶,這也解釋了為何土壤 pH 較低的高寒草甸、高寒濕地的土壤全磷含量顯著高于土壤 pH 較高的高寒荒漠與溫性草原。土壤氮含量的多少直接影響植物生長發育、土壤微生物的數量和分布以及土壤中酶活性。本研究中土壤全氮含量范圍為 2.01~7.54 g/kg,高于全國平均水平。這可能與樣地環境有關,Dinakaran 等認為高海拔地區土壤全氮含量較高與土壤溫度低時有機質分解速度緩慢有關,門源縣年平均氣溫在 4℃以下,土壤溫度低,有機質分解速度緩慢,這與本研究結果相同。高寒荒漠的土壤全氮含量較低可能與水分有關,水分作為對植物生長發育具有關鍵作用的限制因子,通過對植物產生影響進而干預地上氮源對土壤的輸入。已有研究表明,禁牧可以有效提高草地的土壤養分含量,是草地生產力維持和健康發展的有效措施,因此,管理部門今后可以通過一些政策引導牧民進行圍欄封育,以利于祁連山國家公園內草地的可持續利用及退化草地的恢復。
3.3 不同草地類型土壤微生物群落特征
與王占青等對高寒草地土壤微生物群落的研究結果相近,本研究的 4 種草地類型中,群落相對豐度較高的細菌門類主要為放線菌門、變形菌門、酸桿菌門、綠彎菌門和擬桿菌門。高寒濕地中放線菌門的豐度相對較低,這可能與放線菌細胞壁成分有關,放線菌作為革蘭氏陽性菌,細胞壁主要由肽聚糖、磷酸鹽等組成,細胞壁強度高,更適應干旱環境。酸桿菌門在土壤含水量更低的高寒荒漠中相對豐度最高,且與高寒草甸沒有顯著差異,這與張平究等研究結果并不一致,他們發現酸桿菌更適宜生存在土壤水分較多的環境中,這可能與酸桿菌自身的耐旱性以及營養需求有關,Ward 等研究發現酸桿菌大量新型高分子排泄蛋白和纖維合成基因的存在使其具有一定的耐旱性,同時,酸桿菌作為寡營養型細菌也可以解釋為何其在土壤有機質含量更低的高寒荒漠中相對豐度更高。
本研究的 4 種草地類型中,群落相對豐度較高的真菌門類為子囊菌門、擔子菌門和被孢霉門。子囊菌門和擔子菌門均在降解木質素、纖維素等物質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在本研究中,擔子菌門多存在于溫性草原、高寒草甸等土質較好、地上生物量更高的區域,與 Sergio 等研究結果類似,他們發現擔子菌在地上生物量更高,即可供其降解的木質素、纖維素含量更豐富的地區更容易形成優勢群體。而子囊菌門由于其更強的抗逆性在高寒荒漠等嚴重退化草地占據優勢。
本研究中,土壤微生物群落特征與土壤理化性質具有顯著相關性,說明微生物對其生存的微環境變化是敏感的,不同草地類型的土壤 pH、含水量、養分含量等均不同,進而使微生物群落產生差異。高寒荒漠土壤孔隙度高,含水量低,透氣性好,因此如被孢霉門類好氧微生物豐度較高。高寒濕地土壤含水量高達 92.05%,凋落物和有機質分解緩慢,雖然能使土壤有機質含量保持在較高水平,但透氣性較差,土壤氧氣含量低,導致好氧微生物豐度減少,群落結構脆弱,進一步解釋了為何高寒濕地土壤微生物群落結構與其他 3 種草地類型相比更簡單。說明不同的微生物對環境的適應性存在差異,如放線菌更適宜在干旱環境生存,子囊菌門抗逆性更強,對環境的適應性更廣。
4 結論
不同草地類型的植被特征不同,高寒草甸植被蓋度、地上生物量均最高,高寒草甸、高寒濕地以莎草科和禾本科植物為主,高寒荒漠以景天科植物為主。高寒草甸、高寒濕地土壤有機質、土壤全氮含量等較高,不同草地類型土壤物理性質差異顯著。植被蓋度與土壤速效氮、土壤全氮、土壤全鉀和土壤容重呈顯著相關關系,其中與土壤容重、土壤全鉀含量呈極顯著負相關,與土壤速效氮和全氮呈極顯著正相關。在土壤含水量較高的高寒濕地中放線菌門相對豐度較低,而在土壤含水量較低,土壤透氣性好的高寒荒漠中酸桿菌門、被孢霉門等好氧微生物相對豐度較高。在植被豐富、地上生物量高的高寒草甸和溫性草原中擔子菌門豐度較高。
張陽燦;楊文權;魏興勇;屈世清;蔣文昊;李 霄;李希來;寇建村,西北農林科技大學草業與草原學院;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青海大學農牧學院,202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