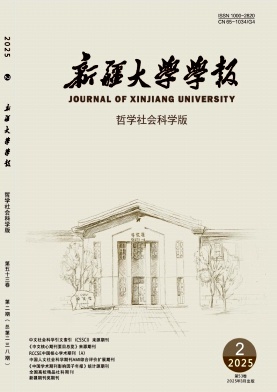新疆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版雜志投稿格式參考范文:診斷與異議:文學在福柯哲學中的批判作用
時間:
文學之所以在福柯哲學中占據特殊的位置,一是文學具有一種對知識型 (episteme) 加以診斷的能力,二是文學能夠對理性話語秩序提出異議。這兩個方面共同形成了一種關于現代性的批判態度,即診斷我們如何所是、所為、所思的規則,以及提出在當下如何不依照這些規則去是、去為、去思的異議。在福柯的作品中,這種批判作用通過許多文學家或文學人物得以體現,而堂吉訶德、薩德、波德萊爾在其中起到了典范作用。三者作為各自時代的另類角色展示了一種對于主流統治的積極反抗,福柯通過對自我的另類身份或實踐的肯定,表達了一種獨特的批判觀念,即批判是我們不被如此這般統治和自愿反抗的藝術。福柯的這種批判與當下的自我密切相關,并指向一種對主流秩序的反抗,但是,其反抗不是基于主體化的普遍理性,也不旨在形成某種總體化策略,而是基于一種個人化的生存美學,旨在提示人們以一種審美的方式來創造自我及自我的生活。
一、作為診斷的文學
文學在福柯的知識考古學中承擔了重要的診斷角色,即診斷詞與物的關系以及話語規則的轉變,從而揭示人在歷史上和當下如何是其所是。福柯指出,至少自尼采以來 “哲學的任務是診斷,而不再是試圖說出一個對所有人和所有時代都有價值的真理。我試圖診斷,對現在做出診斷:說出我們今天是什么、我們今天所說的意味著什么”。因此,以人文科學知識為對象的知識考古學并不是探索如何用話語表達出事物的真正內涵或普遍邏輯,而是通過追溯事物在話語層面的歷史存在方式來理解當下。同樣,文學作品在《詞與物》中的作用也不在于揭示知識的不變本質,而是作為一個界線診斷不同時期知識型的轉變,這些不同的知識型塑造了人在歷史上的不同主體形式。
福柯之所以視《堂吉訶德》為 “西方第一部現代文學作品”,就在于它作為一個邊界文本展示了從文藝復興時期到古典時代的知識型轉變,并標識和診斷了相似性原則與表象原則之間的邊界和斷裂。在福柯的分析中,“堂吉訶德的冒險形成了邊界:它們標志著相似性和符號之間舊的相互作用的結束,并包含了新關系的開始”。堂吉訶德之所以被同時代的人視為瘋癲的人,不是因為他的語言不能解釋世界,而是因為詞與物的組合方式在古典時代發生了變化。堂吉訶德的騎士理想是文藝復興時期知識型的話語產物,即以感性的相似性為原則來解釋世界和呈現自己。
堂吉訶德顯然是一個熱情擁抱世界的人,但他忠實于騎士小說中對世界的解釋,小說成為他的生活范本,他忠實于小說并努力保持它的真實性,他的世界也以書中所描述的方式得以展現。堂吉訶德努力使自己成為書中的一個角色,并通過為自己所遭遇的對象和環境提供相似性關聯來填寫現實世界的細節,從而精確地復制書中那些精心設計的神奇世界。堂吉訶德的整個旅程都在尋找書與世界之間的相似之處,所以,羊群、侍女和客棧成了軍隊、淑女和城堡,理發師的銅盆和驢鞍成為騎士高貴的頭盔和馬鞍,鄰村的女子成為臆想中的貴婦,一座座的谷倉風車成為成群的巨人。雖然堂吉訶德那些站不住腳的聯想被人們所嘲笑,但他正是通過相似性規則將現實世界構造成為了一個完整的騎士故事。
因此,堂吉訶德不是一個不正常的人,他只是以過去的方式去理解一個已經被古典時代話語規則所解釋的世界,但新的話語規則不再像文藝復興時期那樣注重相似性,而是以表象和推理為原則。世界并非不能通過相似性來描述,當世界以書的形式出現,那么書就是世界,但是古典時代習慣于通過一些被認為清晰的人工符號來形成對象的區分或分類,從而形成關于事物的表象秩序,而不是以模糊的、感性的相似性來呈現它。文藝復興時期的話語規則在古典時代已經瓦解,“寫作不再是世界的散文;相似性與符號已經解除了它們以前的聯盟;相似性已經變得具有欺騙性,接近于幻想或瘋狂”,改變的不是世界,而是認識和解釋世界的方式,而堂吉訶德的方式與古典時代格格不入。
對福柯來說,詞不是對物的秩序的反映,相反,物的秩序由話語的規則所安排。話語為某個特定對象可以說什么、做什么、甚至想什么設置限制,“我們將把話語稱為一組陳述,只要它們屬于同一話語形式…… 它由數量有限的陳述構成,我們能夠為這些陳述確定一組存在條件。從這個意義上說,話語不是一種理想的、永恒的形式,它也擁有一段歷史”。話語不是在虛空中或抽象中形成,相反,它們是 “系統地形成它們所談論的對象的實踐”,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結合點上,關于事物的某些陳述被認為是正確的,其他的則不是,而知識就是按照特定話語規則所表達出來的陳述。也就是說,所有的話語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或更新,相應的,知識或真理也是如此,關于事物的知識都是由歷史上局部的和特定的話語規則所構建,而不是取決于穩定不變的某種事物秩序。同時,在福柯看來,人并不直接面對和認識現實的事物,相反只是通過話語和話語規則來間接地接觸和整理事物,事物通過話語才變得對人有意義,人們將事物構成為話語的對象,并在意義系統中根據話語規則來設置事物的秩序,而除了人們通過語言描述給事物所賦予的秩序之外,事物并沒有本身內在的秩序。
同樣,對福柯來說,人也不具有不變的本質,而是特定話語規則的歷史產物,當下的我們也同樣如此。堂吉訶德被視為同時代的另類,但他只是以另一種不同于理性主體的方式理解世界,正如他的經歷所展示,知識型并不只有一種,相應的,人也不只有理性主體這樣一副唯一的現代面孔。就如堂吉訶德在古典時代的遭遇一樣,“人” 之死的原因在于知識型的轉變,大寫的人作為理性話語的產物,同樣會如沙灘上隨時被沖散的沙畫一樣消失。
福柯對文學的偏愛與其對瘋癲的討論相似,都旨在通過非理性的話語形式形成一種對理性主體的診斷與顛覆。福柯希望通過文學獲得一種類似瘋癲之于理性的外部思維,從而可以與傳統的主體哲學決裂,即擺脫主體本身去探索一種可以在歷史框架內解釋主體構成的分析,“這是一種歷史形式,它可以解釋知識、話語、對象領域等的構成,而不必提及一個在事件領域中先驗的或在整個歷史過程中以其空洞的同一性運行的主體”。對于福柯來說,一方面,文學作品中的瘋癲描述使傳統哲學中那些不可見的東西變得可見,或者說不可能的東西變得可能。福柯通過堂吉訶德展示理性主體之外的可能性,因為,“瘋子傳達的是無法傳達的東西;他們擾亂了世界的邊界和最穩固的分界線”,“瘋癲揭示了看不見的東西…… 瘋癲的作用不僅在于像耍把戲一樣揭示事物的真相,而且還在于表達文學、戲劇、小說的真相”,瘋癲可以顯示理性主體之外的不可見之物,就好比堂吉訶德使得表象規則之外的、被社會排斥的、與現實相分離的其他可能話語形式變得可見。
另一方面,福柯認為文學與瘋癲具有神秘趨同的、鄰近的語言體驗。“它們都在 (理性) 語言之外,都是那些奇怪的、邊緣的、略帶越界的體驗,在它們自己的空間里,觸發著它們的代碼、它們的密碼、它們自己的語言體系。” 文學語言打破了諸如意義和作者等傳統主體哲學觀念,“文學作品有能力將一種陌生和外來的元素引入特定文化在特定時間的經歷中,使得文字和事物之間看似穩固的聯系走向崩潰”。因此,文學和瘋癲一樣可以讓人們獲得一些通往異質真理的途徑,并對理性秩序形成一種類似的顛覆作用。無論是瘋癲還是文學對理性主體和話語規則所產生的診斷和顛覆,都是通過在詞與物之間引入異質元素而產生,正如在《詞與物》開頭所謂《中國百科全書》的動物分類所表明,一種非西方的話語模式為西方文化所帶來的不僅是新奇和怪誕,它本身也是對西方主體哲學和理性話語秩序的顛覆。
二、作為異議的文學
文學對福柯哲學的第二個思想作用是提出異議,如果說診斷意味著分析我們如何是其所是的規則,那么,異議則意味著我們如何超越這些規則。異議問題在福柯關于巴塔耶和布朗肖等人的文學評論中得到了集中的體現,文學被認為能夠通過提出異議來逾越特定的話語規則,從而創造通向外部的可能性空間,薩德則被福柯視為是這些作家的先驅。福柯認為現代思想具有一種普遍的主體秩序理想:“人的他者必須成為與他自己相同的人”,而薩德提供了對這種現代話語模式的挑戰,其作品提供了一種 “在西方文化中持續不斷的模糊低語 (murmur)”,薩德在這種低語中暴露欲望,并體現了無序的欲望與細致有序的話語表象之間的不穩定平衡,他所喚起的語言的力量不是一種對表象真理的追尋,而是以一種赤裸的放蕩經驗對 “我思” 主體的自明性提出異議并構成沖擊。
與《堂吉訶德》相似,福柯認為薩德的作品也位于一個新舊知識型的交界。“朱斯蒂娜 (Justine) 和《朱麗葉》(Juliette) 在現代文化的門檻上,就像堂吉訶德在文藝復興和古典主義之間所占據的位置一樣。”《堂吉訶德》開啟了古典時代,而《朱麗葉》則結束了這個時代,前者表現了基于相似性的話語規則如何在古典時代淪為荒謬和瘋癲,后者則表現了欲望如何沖擊理性表象的極限,“它不再是表象對相似性的諷刺勝利;而是欲望對表象界限的晦澀而反復的暴力沖擊”。詞與物之間的關系并不是固定不變,兩者可以從話語的相似性規則轉變為表象規則,非理性語言也可以對表象規則形成沖擊。
與《堂吉訶德》不同的是,薩德作品的重要性不只是標識和診斷不同知識型的變化或話語的轉換,而是能夠超越主流知識和話語的秩序,薩德作品中的人物總是試圖對禁忌加以侵犯,從而體現出一種發出異議的能力。薩德與古典時代的差異不是他找到了一種不同的語言或話語規則,他的寫作事實上并沒有違背理性話語的規則。如福柯所言:“在薩德的書中,把哲學話語和感官描述裹在一起的做法,無疑是復雜的建筑原理的產物”,但是,薩德提出了理性話語的另一種選擇,他利用理性話語描述欲望與暴力,并將人們拋入一個無規則的空白地帶。“在放蕩思想的建構和表達中,薩德同樣訴諸一種純粹理性的話語,換言之,他試圖在理性的秩序 (ordre) 中再現非理性的混亂 (désordre)。因此,薩德的作品一方面體現為一座宏偉而嚴謹的理論大廈,處處反射著古典的幾何精神,另一方面則在建筑的深處容納一切難以想象的瘋狂事物,把內部的空間變成謀殺、欺詐、奸淫、虐待和偷盜的無法無天的國度。”
因此,薩德的作品并不是一種理性的他者話語,但作品中那些 “不正常” 的人物傳達了一種異議。這種異議是一種顛覆,但不是話語模式的顛覆,而是從理性邏輯的內部展示人如何獲得非理性的其它可能性。薩德的文學并不以思想的面貌出現,而是體現了作為否定力量的欲望,放蕩者通過欲望廢除了理性邏輯和思想的規則,但并沒有展示出欲望的真理,而是一種否定的證明,“放蕩者的存在本身就證實了上帝的不存在”。放蕩者 “講” 出其欲望的過程,就是一個 “不正常的人” 表達異議的過程。福柯在《越界序言》中將薩德對性的描述與越界 (transgression,亦作僭越) 聯系在一起,“從薩德到弗洛伊德的現代性論的特征并不在于它們找到了語言來描述性的邏輯或本質,而是通過將性‘變性’(denatrued) 和借助語言暴力,將性拋到了一個空白的地帶,在這個空白地帶,性所獲得的任何貧乏的形式都是通過建立它的限制來賦予的”。對福柯來說,薩德是一個越界的典范,性在現代的興起是神圣的東西失去其積極特征和豐富意義的結果,薩德對神圣的褻瀆只是重申了這種失去,他關于性的話語將人們帶到了上帝缺席的夜晚,“人們的所有行為都以瀆神的方式來應對、識別和驅散這種缺席,并在其中耗盡自己,再將其恢復到已經被僭越的空洞純潔”。性作為一種不受任何限制的運動,與西方關于上帝的神圣話語共同形成了越界這樣一種有關侵犯與界線的獨特經驗,“上帝之死并沒有為我們恢復一個受到限制的、實證主義的世界,而是恢復了一個由經驗而揭示出其各種限制的世界,這個世界被那僭越它的過分行為既制造又拆解”。
因此,對福柯和薩德來說,性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為性代表著一種原始對文明的沖擊,而是性可以創造人與人關系的不同可能性。福柯認為:“我們生活在一個關系的世界里,而制度則相當貧乏,因為管理一個關系豐富的世界會非常復雜,社會和構成社會的制度為此限制了關系的可能性,因此,我們不得不與關系結構的貧困化作斗爭…… 孤獨的生活往往是我們社會中可能的關系缺乏的結果,在這個社會中,制度使所有可以與他人建立的關系都不充分,甚至是必然稀少的。”
過度的、反常的性行為作為挑戰規范秩序的典范,不是通過政治與司法來建立某種新的關系,而是通過個體化的新的自我實踐方式來創造自己,從而能夠以提出異議的方式來打破人與自我以及人與人之間的貧困關系。
福柯和薩德都通過性異常者的越界行為展示異議,薩德通過放蕩者的形象,而福柯則是將同性戀作為例子。對于放蕩者,薩德的作品顯示了一些 “變態” 的描述,這些描述可能會被解讀為令人厭惡的或是色情的,但從福柯的分析角度來說,這些作品中的人物以放蕩的方式對十八世紀的生活方式提出了批評。“薩德的越界行為并不是為了展示一種更好的規范,而為了對人們已經接受的規范制造不安”,這樣,薩德的作品不僅可以解讀為尋求變態的刺激,也可以解讀為它們在重新想象人與人的關系或生活方式的更多可能性。
對于同性戀來說,也是同樣如此。福柯在《友誼作為一種生活方式》中認為,人們總是傾向于將其與 “我是誰” 和 “自我欲望的秘密是什么” 這樣的問題聯系起來,但是,真正的問題應該是 “我們可以通過同性戀建立、發明、繁衍和調節什么樣的關系”,因此,“問題不在于發現自己的性真相,而在于從現在起利用自己的性取向來達成多重關系”。也就是說,在福柯看來,與其試著把同性戀的身份固定到已有的社會關系類型之中,不如試著讓其逃離到這些關系類型之外,這雖然看起來充滿了危險,但其中蘊含著創造新的關系和豐富自身生活方式的可能性,而且這種做法不僅僅是為了捍衛某一類人 (如性異常者),而是針對所有現代人,因為正常人也并不比另類的人具有更豐富的關系和可能性選擇。
總的來說,薩德的作品被福柯視為一種越界的文學并擁有提出異議的能力。福柯所說的文學不是主體對世界忠實反映的產物,而是自我反映、分解和重組世界的工具,是一種試圖擺脫既有話語模式 (如主體) 的束縛或統治的話語形式。但是,福柯并不旨在形成一種文學對哲學、非理性話語對理性話語的替代。越界作為一種逾越是與界線打交道的行為,“越界與界線之間的對抗游戲由一種簡單的頑固性來調節的,越界行為不斷重復地越過界線,而界線在極短的時間內閉合,因此它又一次回到了不可逾越的地平線上”。越界不是為了達到外部而消滅界線,相反它需要不斷地確認和碰觸界線,越界不是對某種外部本質的確認,而是一種對界線之外的可能性的不斷探索,它不是絕對的外部,只有在相對于界線的內部時,它本身才能以異議的方式得以呈現。
發出異議的人并不能完全處于界線之外,異議雖然可能逾越了界線,但只有當人們努力達到這些界線時異議才可能出現,一個發出異議的人必須處身于界線之上,并超越外部與內部這樣非此即彼的選擇。福柯認為話語具有一些限制原則,而話語就是一系列限制性或封閉性操作的結果,而文學能夠為異議提供場所,因為,“文學就是一種越界的語言”,它既碰觸這些話語限制,也在這些限制之外發揮作用,這使得人們有可能看到某些一直隱藏在理性外部的元素,能夠說出不想被看到或被聽到的東西。這也使得文學處于危險的地位,它相對于已有的話語規則來說是否定性的,但是,這種否定性不是一種消極的力量,相反,它是一種能夠揭示自我存在的積極力量,這與福柯在晚期所表達的直言 (parrhesia) 是一致的。同樣,被福柯視為越界的薩德作品并沒有提供一種更優的明確秩序,而是在于讓文學語言不再以受表象所支配的形式出現,從而想象出一些不符合性主體的規范的東西,對人們習以為常的主體理想提出質疑。事實上,無論是薩德筆下的放蕩者還是福柯所關注的同性戀,所展示的欲望都是一種違背主流話語秩序的力量,而這種力量為自我存在的新形式提供了可能性。
三、作為批判的文學
文學在福柯哲學中的診斷與異議作用,共同體現為一種關于現代性的批判態度,這在福柯借助波德萊爾所作出的啟蒙闡釋中得到了典型體現。
在《什么是啟蒙》中,福柯將波德萊爾作為解釋康德同名文章的一個有效資源,并對現代性進行了批判闡釋。福柯認為反思啟蒙的價值在于理解當下的現代性,因為被康德所稱為啟蒙的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決定著我們今天是什么、思考什么和做什么”。福柯一定程度上贊同康德的啟蒙描述,即如果我們要達到一個更自主 (autonomy) 的狀態,我們就必須進行持續批判。對康德來說,只有通過合法地使用理性,個人的自主才能得到保證,啟蒙就是一個將我們從人類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狀態中釋放出來的過程。康德在其 1784 年的文章《什么是啟蒙》的開篇明確表示:“啟蒙就是人從他咎由自取的受監護狀態走出。受監護狀態就是沒有他人的指導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理智的狀態。如果這種受監護狀態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缺乏無須他人指導而使用自己的理智的決心和勇氣,則它就是咎由自取的。
因此,Sapere aude [要敢于認識]!要有勇氣使用你自己的理智!這就是啟蒙的格言。” 福柯同樣認為自主對個人的批判性能力至關重要,但是,他反對以統一的理性主體為基礎對其加以演繹,理性主體只不過是人在歷史中的一種特定形式,因此,批判不應該在尋找具有普遍價值的形式結構中進行,而是應該置身于對事件的歷史調查,這些事件引導我們構成自己,并認識到我們自己是我們所做、所思和所言的主體。這種指向自我調查的批判,并不是把自我視為一種先驗的主體,而是視為一個歷史的、實踐的對象。
因此,福柯認為我們應該將現代性更多地視為一種態度,而不是一段特定的歷史時期。如其所說,“這種態度與一個人的當下方式有關,如一些人所作的自愿選擇,如思考和感受的方式,或行動和行為的方式,這些方式既是這種態度的屬性,也呈現為它的任務,有點像希臘人所說的精神氣質 (ethos)”。對福柯來說,批判沒有純粹先驗的或非歷史的價值,因為它總是處于歷史的語境中,“將我們與啟蒙聯結起來的脈絡并不在于信守教條,而在于不斷重新激活一種態度,這種態度是某種哲學的精神氣質,我們可以將其描述為對我們所處歷史時代的永久批判”。
正是在這個時候,福柯將波德萊爾帶入到關于現代性的批判討論之中。福柯將波德萊爾所說的浪蕩作風 (dandysme,亦作紈绔主義) 視為一種自我創造的現代性,既是一種自我與當下的關系,也是一種必須與自己建立的關系模式。在《現代生活的畫家》中,出于對自身藝術評論的反思以及追求新穎的審美目的,波德萊爾將美與現代性的特征相關聯。一方面,他反對傳統的審美觀念,即美是絕對的和永恒的,而是認為美具有雙重的構成維度,它既有永恒的元素,也有短暫的、相對的歷史性元素,這種短暫和相對的元素被識別為當下的時尚、習俗以及一些稍縱即逝的東西。另一方面,波德萊爾認為現代性就是當下短暫的偶然性,“現代性就是過渡、短暫、偶然…… 這種過渡的、短暫的、其變化如此頻繁的成分,你們沒有權利蔑視和忽略。如果取消它,你們勢必要跌進一種抽象的、不可確定的美的虛無之中,這種美就像原罪之前的惟一的女人的那種美”。美的短暫性與現代性形成了一種對應,藝術就是對當下的短暫性的審美表達,一個現代的藝術家的角色就是為現在的短暫性賦予美的形式,從 “時尚” 中汲取歷史上可能包含的詩意,從短暫中提取永恒。在這種觀點下的美總是另類的,同時,“學科化的美學無法欣賞新奇的美,甚至無法欣賞另一種文化中日常的美”,因此,波德萊爾的審美并不指向一種被學科的概念體系所定義的美,他所強調的不是普遍性而是差異,而與其相關聯的則是一種充滿了異議和風險的現代主義態度。
對波德萊爾來說,文學和藝術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現在,并使現在的生活變得有意義,而浪蕩子是一個試圖在現在的短暫性中找到詩意的現代人。波德萊爾式的浪蕩子不是一個完美的存在,也不具有任何確定的內涵,“他拒絕給定的身份,以便代表自己說出或創造一種身份,通過這種方式,一個人以不可還原到給定類別的方式構成自己的身份”。浪蕩子不是一個將愛情或金錢作為最終目標的游手好閑之人,而首先是一個富于異議并喜愛個人創新的現代人,同時,浪蕩子是一個意識到自己和自己處境的歷史局限性的人,但他試圖超越這些局限性。一個作為現代人的真正的浪蕩子不遵循任何既定的規范或界線,而是以審美的方式創造自我,他雖然致力于無用的激情和極端的休閑,但其目的并不盲目,而是為了讓單一的生活變得充滿個性。浪蕩子并沒有廢除現實,而是在當下使自己英雄化,以創造性的自由來對抗現實,“浪蕩作風是英雄主義在頹廢之中的最后一次閃光…… 浪蕩作風是一輪落日,有如沉落的星辰,壯麗輝煌,沒有熱力,充滿了憂郁”。因此,浪蕩子的形象事實上是一種對主流文化所合理化的生活方式的異議與反抗。
福柯并沒有參與波德萊爾關于美的本質的思考,但同樣將現代性與審美相關聯,將現代性解釋為一種態度或藝術化的自我風格。一方面,對福柯來說,波德萊爾式的浪蕩作風代表了自我與某種傳統的決裂態度,是一種自我在當下轉瞬即逝的瞬間新奇感。“這種深思熟慮的、艱難的態度在于重新把握某種永恒的東西,它既不在現在之外,也不在現在之后,而在現在之中。” 同時,這種態度并不在于對某一發現的惰性接受,而是在于對一個不一樣的自我的發明。波德萊爾的浪蕩作風被福柯視為一種事關自我的現代藝術,成為現代人并不是接受自己處于過去的時刻,而是將自我視為當下復雜而艱難的闡述對象,并以審美眼光發現自我的新奇之處。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對福柯來說,波德萊爾式的現代性代表了一種積極的哲學態度,即一種塑造自我的自由實踐:“通過我們自身的歷史本體論,對我們之所說、所思、所做進行批判。” 可以說,波德萊爾式的浪蕩子同樣是一個越界的例子,“浪蕩子把自己的身體、行為、感情、激情甚至自己的存在都變成一件藝術品。對于波德萊爾來說,現代人不是去發現自己、發現自己的秘密以及真理的人;他是一個試圖發明自我的人。這種現代性并不在人自身的存在中解放人,它迫使一個人面對生產他自己的任務”。
浪蕩子以富有想象力和異于尋常的方式行動,這些行動不是出于某種現實的功利目的,而是用來打破社會對個人的限制。福柯認為波德萊爾式的現代性是一種實踐,在這種實踐中,“當下的崇高價值與一種不顧一切的渴望是分不開的,那就是去想象它,去想象它不像它本來的樣子并去改造它,不是通過摧毀它,而是通過在它本來的樣子中把握它…… 對現實的極端關注面臨著一種自由實踐,這種自由實踐既尊重又違背現實”。浪蕩子恰恰體現了這種現代性的態度,他把握并改變現在,而不是逃避這個任務,他既沒有躲在自己所喜歡的過去的時尚之中,也沒有飛向一個脫離現在的未來。正是這種對當下的關注并著眼于改變當下的觀念,讓福柯看到了現代性與啟蒙的聯系,也就是說,一種可以被描述為對我們的歷史時代進行永久批判的哲學精神。因此,現代性態度處于力量游戲中,它既試圖保持對其現實的忠誠和關注,又試圖顛覆和侵犯現實,這不僅是對當下的創造,也是對主體本身的創造,既是一種確認現實的診斷,也是一種改變現實的異議,“它不再從我們所是的形式中推斷出我們不可能做或不可能認識什么,而是從使我們成為我們現在之所是的那種偶然性中,得出我們不再依照我們所是、所做、所思的去是、去做、去思的可能性”。
總之,與波德萊爾一樣,福柯試圖形成一種對現代性的批判解釋,強調現代性是創造自我,而不是在自我深處去發現關于自我的普遍理性結構。首先,福柯與波德萊爾都懷疑啟蒙運動的成功,正如《什么是啟蒙》的最后所說:“我不知道我們是否會到達成熟的成年期。” 對福柯來說,自由不是一種固定的存在狀態,只是一種我們超越強加給我們的限制以及創造自我的可能性。事實上,無論是康德,還是波德萊爾與福柯,現代性都代表了一種個人對自身歷史處境所作出的批判性回應,康德強調理性的普遍有效并對此充滿樂觀,而波德萊爾與福柯則沒有像他那樣表現出對人類通過理性擺脫不成熟的積極信念。因此,波德萊爾與福柯專注于尋找轉瞬即逝的現代性體驗,他們筆下的現代人試圖不斷從強加于自己存在的限制中尋找出路,波德萊爾把目光投向巴黎的流浪漢、乞丐和妓女,而福柯則聚焦于瘋子、罪犯與同性戀。
其次,福柯與波德萊爾都認為現代社會中的個人是一個不確定的主體,因此反對理性邏輯對現代個體的支配,并強調自我風格化的重要性,試圖將個人的生活變成一個審美性的越界場所,也就是寄希望于通過個體的審美化來反抗對個體本質的邏輯化。個體的自我審美雖然旨在創造一種更富于可能性的生活,但這并不是一個與他人無關的、孤立而封閉的自我項目,個體的審美不可避免地面對著各種外部規則和力量,這意味著需要與他人不斷對話。因此,福柯所說的 “作為藝術作品的自我” 需要探索和改造的不僅僅是自我,但是,這種自我審美的首要目標依然是自我與自我的關系,即福柯所謂的倫理。關于自我,福柯持有構建主義的立場:“自我應該被看作是我們歷史上發展起來的技術的相關物。于是,問題就不在于拯救自我,不在于‘解放’自我,而在于考慮如何才能設想我們和自己關系的新類型、新種類。” 同時,如其所言,“批判是不被統治到如此程度的藝術”。所以,肯定自我的另類身份或實踐 (如放蕩者、浪蕩子或同性戀) 所產生的批判性價值,正是在于它們代表了一種對于統治的積極反抗。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自我的審美實踐作為一種反抗與權力關系密不可分。福柯晚期的生存美學將自我與藝術品相關聯,事實上也是試圖通過審美來積極地反抗權力關系,從而創造自我的更多可能性。因此這種美學不是一種主體化和學科化的知識 (connaissance),而是一種風格化的批判策略,它不基于自我的某種固定的本質身份,而基于應對不斷變化的權力關系,個人無法脫離權力關系,但可以在其中通過不斷的審美實踐構成風格化的自我。
四、結語
在福柯的作品中,文學所表達的診斷、異議和批判大多基于歷史考察,但是其真正目的仍聚焦于當下的自我,并蘊含著反抗這一政治指向。福柯通過《堂吉訶德》形成了對話語規則的診斷,通過薩德的作品提起了一種對具有中心地位的話語模式的異議,而這種診斷和異議通過波德萊爾體現為一種關于當下自我的激進批判,即反思我們在當下如何所是、所為、所思的規則,以及如何不依照這些規則去是、去為、去思。因此,福柯的批判與反抗某種話語模式的統治密切相連,如其所說:“批判將是自愿反抗的藝術,是充滿倔強的反思藝術。批判本質上將確保在我們稱之為‘真理的政治學’的語境中解除主體的屈從狀態。”
福柯并沒有提出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反抗策略,而是從個體意義上提出了一種生存美學層面的反抗藝術。福柯式批判并不基于普遍的共同理性,其生存美學也不是某種學科意義上的美學理論,而是一種事關自我的 “精神氣質”,即一個人把自己的生活視為一件藝術品,以一種審美的而不是規范化的方式來創造和定義自身生活的努力。
這種努力由于與外在規范格格不入而導致自身顯得另類。在福柯的作品中,無論是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還是薩德作品中的放蕩者,或是波德萊爾筆下的浪蕩子,并不簡單地代表或肯定某種話語類型或話語規則,他們的共同之處主要在于他們是各自時代的另類典范。這種另類不是一種膚淺的標新立異,而是可以納入到一個福柯所說的 “我們自身的歷史本體論” 的批判性項目之中,這不是一種理論或者學說,而是一種態度或哲學生活,是一項對強加于我們的限制的歷史分析和超越它們的可能性的實驗。這種實驗性質的自我美學意味著危險和艱難。之所以危險,是因為當一個人不斷沖擊自我的界線并對已有的規范加以質疑時,他自然而然地處于否定性的反抗位置,而這對于任何一方都是一種危險的沖擊;之所以是艱難的,是因為一個人并不知道自己當下反抗的行動標準,也不知道如何確定自己的所思和所為是自主的,因為他無法控制或消除施加于己身的外在支配,甚至無法意識到自己并沒有處于自主狀態。
在反抗如何實現的這一政治維度上,福柯個體化的策略顯然會招致許多質疑。政治意義的反抗可以從個體出發但不會滿足于個體層面,對此,福柯關于反抗的觀點顯得有些無力,這與他反對一切總體化的方案有關,也與他對自身的角色定位密不可分,如其在一次訪談中表明:“我的角色是向人們展示,他們比自己感覺的要自由得多,人們接受在歷史的某個時刻建立起來的一些主題作為真理和證據,而這些所謂的證據是可以被批評和摧毀的。改變人們思想中的某些東西,這就是知識分子的角色。” 在福柯看來,我們不可能通過把握整個歷史來形成一個普遍的標準,我們只能為我們的時代以及我們自己建立一個有效的視角,以此批判和超越歷史強加給我們的限制。不過,對于如何超越這些限制,福柯拒絕給出一個明確的答案,他既沒有主張任何事情都會發生,也沒有主張某事應該或不應該發生。因此,他并不是一個現實反抗活動的指南者,而只是一個發出思想提示的人,其目標不在于提出一種旨在形成某種現實變革的整體方案,而是提示人們具有自我創造的更多可能性。
夏天成,安徽大學哲學學院,202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