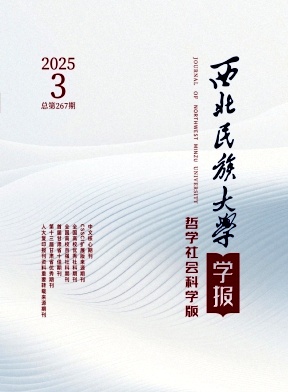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雜志投稿格式參考范文:文學交融視域下的明清河湟詩文創作述論
時間:
河湟,河是指黃河,湟是指湟水,后來泛指黃河、湟水、大通河流經的 “三河間” 地區。今天來看,河湟地區主要包括青海省東北部農業區和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中華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一個歷史過程,也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一個重要維度。” 河湟地區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環境,逐漸成為農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交匯區、多民族聚居區,多民族文化在這里交往交流交融。明清時期,隨著中華各民族文化交融的不斷深入,河湟地區詩文創作愈發興盛。
一、明清河湟詩文創作興起的文化背景
(一)儒家文化的傳播
“文教政策作為清廷實現民族政治一體化,達到‘華夷一家’和大一統目的的方式之一”,為儒家文化在河湟地區的傳播創造了有利條件。明清時期,中央政府在河湟地區修建學校,培養人才,大力發展儒學教育。儒學、書院、社學、義學、私塾五位一體,共同構成了河湟地區的文教體系,也是河湟地區儒學教育的主要陣地。儒學,即地方官學,明清兩代河湟地區共建立了 7 所儒學,即河州儒學、西寧府儒學、碾伯縣儒學、貴德廳儒學、西寧縣儒學、大通縣儒學和循化廳儒學,奠定了河湟地區儒學教育發展的基礎,推動了河湟地區儒家文化的發展。同時,建立了大量的社學、義學和私塾。社學、義學、私塾是中國古代的啟蒙教育,不列入官學之內。明清時期,河湟地區共建立了社學 28 所、義學 93 所,以及大量的私塾。此外,河湟地區建立了 14 所書院,即河州大書院、小書院、鳳林書院、龍泉書院、愛蓮書院、西寧府五峰書院、西寧縣湟中書院、大通縣三川書院、大雅書院、泰興書院、碾伯縣鳳山書院、貴德縣河陰書院、循化廳龍支書院和丹噶爾廳海峰書院。書院多由著名學者主持,學術氛圍比社學、義學等教育機構更濃。儒學、書院、社學、義學、私塾的大量建立,標志著河湟地區的文教體系已趨于完備。
“文學發展與儒學傳播具有一定的同步性。可以說,受過儒學熏陶的作家,在創作上往往都將儒學作為文學創作的基礎和底蘊,從儒學中獲取文學創作所需的道德修養、創作靈感、詩歌題材及詩學話語。” 河湟地區文教事業的發展,廣泛、系統地傳播和普及了儒學文化,科舉考試等制度也大大激發了人們學習儒學文化的積極性,作為科舉考試內容之一的詩文,自然也成為讀書人的必修課。由此,河湟地區產生了一大批文人儒士,使河湟地區的詩文創作得到了空前的發展。
(二)外來文人的影響
明清兩代,大量文人隨著駐軍、移民、屯田、經商以及官員蒞任等途徑進入河湟地區,為河湟地區帶來了良好的文化氛圍,推動了河湟地區詩文創作的發展。
文學名家引領河湟文學風尚。《河州志》載:“解縉,字縉紳,江西吉水人。洪武間進士,入中書知制誥堂翰林內外志。三十一年,謫河州衛禮房吏,詩文草書,遺留甚多。” 解縉謫居河州期間留有大量詩篇,影響深遠;同時,解縉在河州期間常與當地文人酬唱贈答,影響了一大批文人,其《鎮邊樓》一詩,引來明清兩代數以百計的文人唱和,堪稱文壇佳話。一些名家雖然沒有在河湟地區長期生活的經歷,但途經河湟地區時留下了諸多詩歌名篇。楊一清在陜西為官時,創作了《積石峽》《過河州》等詩歌。吳鎮,清代臨洮著名詩人,其《陳子昂談河州牡丹之勝悵然有作》《積石歌》等詩歌均是對河湟地區的吟詠。在這些文學名家的影響下,河湟地區文學氛圍愈發濃郁,詩文創作蓬勃發展,積石峽、鎮邊樓等已經成為河湟地區的標志性景觀。
文人儒士啟迪后進,培養人才。文學巨匠對河湟地區詩文創作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一些文人儒士來河湟地區教書育人,培養文學人才,推動河湟地區詩文創作的發展。如《西寧府新志》載:“梁景岱,陜西三原縣人。康熙二十二年,任西寧衛儒學教授,率諸生修葺西寧、碾伯澤宮,振興學校。甘澹泊,立崖岸,其為人礌礌如也。存心既正,而文藝亦優。察諸生有可教者,必殫盡心力;敢后者,則痛撻之。其施教侃侃如也。” 梁景岱擔任西寧衛儒學教授期間,以身作則,盡心盡力,帶領學生修葺學校,對可教之才殫盡心力,改變了當時重武輕文的風尚。再如《河州志》載:“李景,字士林,號松月,河州衛籍,淮安人。性度從容,善吟詠,恬退不樂仕進,鄉曲子弟多賴啟迪。進士朱紳、舉人吳禎輩,皆陶成于門下。” 李景不追求仕途的進步,對當地學子多有啟迪,河州進士朱紳、舉人吳禎都是他的弟子。這些外來文人對振興河湟地區的文學風氣起了重要作用。
外來文人對河湟詩文創作的貢獻實際上體現了中原文人對于河湟地區的關注,促進了河湟地區與中原內陸之間的文學文化交往,而明清河湟詩文創作的發展也體現了河湟地區文人對于儒家文化的認同和對詩文創作的向往,是中華各民族文化交融一體的重要體現。
二、明清時期河湟詩文創作概貌
明代以前,河湟地區的詩文作品多出于外來文人之手。及至明清,隨著河湟地區儒學文化氛圍日趨濃厚,加之外來文人的大量涌入,河湟本土文學才逐漸嶄露頭角。明清時期是河湟地區詩文創作的黃金時期,從作家身份來看,既有本地文人,也有外來文人;既有漢族文人,又有少數民族文人。從作品內容來看,河湟地區獨特的自然風光、人文歷史、風土人情成為文人創作的不竭源泉。
(一)作家作品概況
根據《河州志・文籍志》(嘉靖)、《河州志・藝文志》(康熙)、《西寧志・藝文考》《西寧府新志・藝文志》《西寧府續志・藝文志》《貴德縣志・藝文志》《大通縣志・藝文志》《丹噶爾廳志・藝文》等著述的記載,《中國古籍總目》《清人別集叢刊》《叢書集成初編》《西寧府續志・志余》《甘肅新通志・藝文志・著書目錄》《中國西北文獻叢書・西北文學文獻》等著作的收錄以及相關圖書館的館藏檢索統計,明清兩代,河湟地區有詩文作品傳世的本地文人共計 52 人。其中 15 人有詩文別集存世,共計 30 部,散存詩文作品共計詩 315 首,文 55 篇。由明至清,河湟地區本地文人的詩文創作整體上呈現作品數量不斷增多,藝術水平不斷提高的特點。明代,河湟地區有詩文作品傳世的本地文人有 12 位,其現存詩文作品主要散存于地方文獻之中,以王竑、朱家仕二人存詩最多。清代,河湟地區有詩文作品傳世的本地文人有 40 人,有 15 人 30 部別集存世,并且出現了如吳栻、張思憲、來維禮等享有詩文盛名的文人。河湟本地文人詩文創作的蓬勃涌現,是河湟文化取得重大進步的標志,其詩文作品是中華民族文化寶庫的重要組成部分。
據河湟地區相關地方志記載,明清時期在河湟地區留有作品的外來文人就有 65 人。其中現存與河湟地區有關的詩文別集主要有 4 部:賈勛《望云草堂詩集・宦游草》一卷,共收錄詩歌 168 首,多為其在大通為官時所創作的作品;闊普通武《湟中行記》兩卷、《青海奉使集》兩卷,均為其往返青海途中所見所聞所感;斌良《抱沖齋詩集・青海紀行集》三卷,共收錄詩歌 262 首,是其奉命來青海致祭途中所作。其他與河湟地區有關的詩文作品散存于卷帙浩繁的文獻資料之中。
(二)題材內容類析
縱觀明清河湟詩文創作,題材廣泛,內容豐富,寫景紀游、即事感懷、詠史懷古、酬唱贈答等應有盡有,并且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和地域特色。從詩歌內容來看,河湟地區詩歌作品主要包括三大主題:吟詠河湟美景、反映現實生活、抒發報國豪情。
吟詠河湟美景
河湟地區獨特的自然風光與人文景觀,是文人創作的源泉。明清時期,河湟地區本地文人創作出大量吟詠河湟美景的詩歌,充滿著對家鄉的贊美之情。清代詩人吳栻懷著對家鄉的熱愛,寫下大量詩篇,其中以《碾伯八景》最為著名。《南山積雪》詩云:“皎潔凌空似玉山,深秋常見羽人還。高低望處峰千疊,遠近看來月一彎。影射長天迷素鶴,光浮淺水失群鷴。堪將此地千峰雪,置向巴陵伯仲間。” 此詩由近及遠、由此及彼,全方位展示了南山積雪的美麗景象,雄奇奔放,令人向往。末尾兩句將南山積雪的美景與洞庭之秀色相提并論,直接反映出詩人對家鄉美景的熱愛。《三川杏雨》詩云:“曾將爛熳照三川,活色生香誰于憐。柳外青簾堪問酒,水旁紅雨自成泉。千家門巷皆鋪錦,十里園林盡罩煙。豈是中州文杏好,移來還待探懷賢。” 詩人用夸張的手法,將杏花爭艷的美麗景象表現得淋漓盡致。諸如此類的詩歌還有張和《河州八景》,張思憲《湟中八景》,張兆珪《丹噶爾八景》,李協中《時樂樓八景》等。相對本地文人而言,外來文人的寫景紀游詩顯得更為客觀,他們以獨特的眼光觀察理解河湟地區的美景。楊應琚于雍正十一年(1733 年)出任西寧兵備道事,次年轉任臨鞏道。乾隆元年(1736 年)再任西寧道。他的詩歌風格清新雋永,如《樂都山村》:“巨石斜橫碧水涯,石邊松下有人家。春風不早來空谷,四月深山見杏花。” 松下有人家,出言平淡而造景清幽,詩句淺近樸實,渾然天成,塑造出一種和諧、寧靜的意境。申夢璽《雨后西平途中喜作》詩云:“郁郁復蔥蔥,山川爽氣通。麥針全破雨,柳線半穿風。急瀨馴鷗鷺,停云掩 。客游何太數,此景不多逢。” 此詩寫西寧雨后清新秀麗的景色,宛如展開一幅山水畫。全詩語言樸實,風格自然,帶給人雨后清新爽朗的感覺。
反映現實生活明清兩代,一大批文人來河湟地區擔任地方官員,他們用詩歌記錄百姓的生活,表達對勞動人民的關懷。王全臣《初入河境》:“我是河州新使君,停車不忍見鳩群。行來竟日無煙火,到處逢人哭野墳。部落千郊驚旱魃,山川一望盡妖云。從今已任斯民牧,杯水何從為救焚。” 作為知州的王全臣初到河州,看到一路上荒無人煙,頹廢凋敝的景象,心情十分沉重。其《乙酉秋日郊行記事》(四首)更是深入細致地描寫了河州東、西、南、北四鄉人民生活痛苦的景象,可以看做是當時河州人民生活的紀實錄,是研究河州地區政治經濟的重要資料。楊汝楩《湟中牛疫頗甚,早春大雪,其患當止,喜疊大風獨酌原韻》:“冬來苦無雪,農事及春早。牛病遍四野,況復半羸老。舐犢何鳴哀?死者相藉藁。良由結塞多,終鮮降水潦。五出忽翻飛,原田壓茭草。子母秉坤靈,濕濕雙耳好。豈獨凡卉蘇,祲氛為驅掃。我車維我牛,其疾爰可保。把盞謝飛瓊,一杯為卿倒。” 記述了湟中人民當時的生活情況,表達詩人對百姓疾苦的同情,當疫患結束后,詩人的喜悅心情溢于言表。
三、明清河湟詩文創作的文學交融特征
明清時期河湟地區詩文創作十分興盛,其詩文創作帶有鮮明的文學交融特征。外來文人與本地文人相互交往,相互促進,共同推動河湟地區詩文創作的繁榮發展。
(一)河湟地理空間與文本空間的統一
文學是人類認識客觀世界、表現自我情懷的一項特殊精神活動,每一個體成員的文學創作活動都發生在一個具體的時空交匯處,特定的歷史條件和特定的地域空間共同構成了他們的創作背景。“文學地理空間之意義,是‘文學’之于‘地理’的‘價值內化’的結果。所謂‘價值內化’,就是經過文學家主體的審美觀照,作為客體的地理空間形態逐步積淀、超越、升華為文學世界的精神象征意義。” 隨著河湟詩文創作的不斷發展,河湟地理空間與文本空間實現了統一。
一方面,河湟地區獨特的風光與景觀意象拓展了文人的創作題材。純自然景觀由是轉化為被感知、被體驗的自然,它引起作家心靈的激動與情感的回應,在滿足主體生命需要的同時被賦予了美的意義。黃河、雪山、積石山、元朔山、日月山、泄湖峽等自然意象成為文人們樂于吟詠的對象。宗泐遠赴西域求經,途經河湟雪山,欣然賦詩。《雪嶺》:“華戎分壤處,雪嶺白嵯峨。萬古消不盡,三秋積又多。寒光欺夏日,素彩爍天河。自笑經過客,相看鬢易皤。”“雪嶺” 是指青海的日月山,其終年積雪,東側是農業區,西側是草原牧場。宗泐在詩中描寫了日月山的美麗風光,同時指出其 “華戎分壤” 的重要地理意義。自然意象之外,鎮邊樓、禹王廟、白塔寺、太子寺、南禪寺等人文景觀也是詩人筆下的熱點。解縉謫居河州期間,遍游河州境內著名景觀,留下諸多吟詠河州風光的詩篇,如《登鎮邊樓》《寧河城》《冰靈寺》《萬壽寺》《題積石》等。《冰靈寺》云:“冰靈寺上山如削,柏樹龍蟠點翠微。況有冰橋最奇絕,銀虹一道似天梯。”“冰靈寺” 即 “炳靈寺”,詩人采用由近及遠的方式贊美冰靈寺的美景,以夸張的手法寫出冰靈寺奇絕陡峭、如刀削一般的山勢,蒼松翠柏點綴其中,突顯冰靈寺的秀麗,用比喻的手法重點描繪冰靈寺的冰橋這一代表性景致,自然天成,畫面優美。整首詩構思新奇,天馬行空,詩風飄逸瀟灑。
另一方面,河湟地區的地域文化氣質給主流文人的精神思想帶來了升華,影響了主流詩人的詩風轉變。解縉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 年)謫居河州,貶謫的不幸經歷,作為一種強大的內在動力,催生出絢爛的文學之花。“解縉在河州的經歷和詩歌創作對其詩風的轉變和成熟有著重要的影響,因此,探討解縉河州詩的創作內容和藝術風格,對解縉詩的整體研究具有特殊的價值和意義。” 被貶之前的解縉,少年成才,意氣風發,其詩歌創作滿懷豪情壯志,鋒芒畢露,如《早朝賜宴》:“君臣千載共明良,侍宴楓宸錫寵光。烏帽簪花搖翠綠,金盤薦果間青黃。九重天上鳴鈞樂,五色云中進玉觴。丹陛拜飏酬圣主,錦衣猶帶御爐香。” 整首詩充滿著少年得志的豪情。解縉被貶河州,從江南來到西北,遠離家鄉與親人,心中充滿了失落與憤懣,再加上河湟地區遼闊蒼茫的地域環境,使得解縉鋒芒畢露的個性有所收斂,詩歌風格也發生了變化,流露出悲涼與幽怨。如《述懷三首》其二:“聞道西羌路坦夷,三千里外一娥曦。英雄南北尋常事,老大悲傷九十稀。夜月書闈詩興逸,秋風鋒路雁聲遲。儒冠莫恨文章誤,要識儒冠顯晦時。” 這首詩是解縉在貶謫之后仍充滿自信的內心寫照,但詩歌風格已經沒有之前的鋒芒畢露,特殊的地域環境與人物心境造就了解縉沉郁蒼涼的詩歌風格。楊揆,江蘇無錫人,隨軍衛藏,途經河湟地區,使得其詩歌風格更加成熟和精深。吳蘭雪曾說:“荔裳早擅風華,中年從嘉勇公出征衛藏,所歷熊耳山、星宿海諸勝,異境天開,詩格與之俱變。極造幽深,發以雄麗,字外出力,紙上生芒,非摹擬從軍行者所能道其一語。” 古代作家運用邊塞意象表現國家意識和民族情感,在描繪邊塞風物時,刻意選取荒涼、蕭條、凄冷且充滿異域色彩的物象,貫注于自己由 “異” 而 “悲” 的情感體驗,表達自己的民族意識和對國家、故土的熱愛之情。
(二)文人交往與酬唱贈答
明清時期,本地文人與外來文人交往密切,留下了大量的詩文唱和作品,是河湟地區文學交融最生動的寫照。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 年),解縉被貶謫到河州期間常與當地文士翰墨相交,詩文唱和,對當地文風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解縉謫居河州期間,留下了大量詩文作品,其中影響最大的當屬《登鎮邊樓》一詩:“隴樹秦云萬里秋,思親獨上鎮邊樓。幾年不見南來雁,真個河州天盡頭。” 此詩主要抒發作者被貶后思親懷鄉,郁郁不樂的心情,后引來明清兩代數以百計的詩人唱和。僅《河州志》的記載就有 41 人同題唱和,其中馬應龍與何永達兩位本地文人的唱和作品,足以說明解縉振興河湟文風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何永達《鎮邊樓步解大紳學士韻》云:“空度光陰九十秋,夢魂猶憶鳳凰樓。云山久望益迢遞,謾讀經書到白頭。” 這首詩是何永達晚年之作,詩人用 “空度光陰” 總結自己的一生,全詩悲涼的感情基調與解縉《鎮邊樓》詩如出一轍。同題唱和之外,酬唱贈答之作更能直接反映文人間的文學交往活動。康熙《河州志》載:“王武,字彥武,河州衛籍,江西人。博通經史,尤長詩詞。嘗與解學士游,遺文最多。《解文集》內《恒齋記》,是其人也。” 解縉在河州時,與王武交往密切,為好友王武寫了《寄王恒齋》《題恒齋卷為王以中作》《清明日寄以中二首》《和王恒齋四首》等詩。
各民族文人之間的交往唱和尤其值得我們關注。河州馬應龍是明代回族官員,與明代文壇 “前七子” 之一的康海交往密切,馬應龍臨終之前說:“吾平生心事,惟武功康子知之。” 他死后,康海為其撰寫墓志銘,盛贊其德行:“吾已見其文,乃復聞其芬。顯不異操,履無丑云。名德振振,光我雍秦。承休萃祥,允在子孫。貞珉弗磷,萬年永存。” 在《重建莊毅公祠堂記》中,他對已故兵部尚書王竑表達了敬意,稱其 “勛業氣節,卓冠古今。” 河湟李土司家族以軍功起家,在河湟地區煊赫一時。李㺬是會寧伯李英之孫,與當時的文人名士多有交集。明代茶陵派詩人李東陽贊賞李㺬的文章,曾作詩《送李進士㺬還西寧》:“幡戟門前綽楔高,郎君身已著青袍。龍墀有地陳三策,虎帳無心學六韜。歸蜀漫夸題柱早,入關空說棄襦豪。太行云外東西路,去國懷鄉兩意勞。” 李東陽用 “三策”“六韜” 的典故來贊揚李㺬文武雙全的才能,“題柱”“棄襦” 則是說明李㺬的豪情壯志,既有贊賞、勉勵之意,也飽含著送別的不舍之情。清代西寧詩人祁松年《讀李指揮鐵券》:“高陽伯出大明時,樹立功勛四海知。定亂安民連奏捷,封茅列土最相宜。名標史冊光千載,勇壓西陲服眾夷。感動英宗頒鐵券,公然寵愛見乎辭。” 天順元年(1457 年),李文履立軍功,被明英宗封為高陽伯。次年,明英宗賜李文丹書鐵券,以表彰其功勛,這在少數民族人群中是極其少見的。祁松年這首詩講述了丹書鐵券的來龍去脈,高度贊揚高陽伯李文的卓越功勛。此外,李氏家族新修宗祠,著名詩人吳栻為其撰寫記文。可見,李氏家族熱衷于結交當時主流文人,表明其對儒家文化的推崇與向往,而主流文人對李氏家族也不吝贊美之詞,這是文學交融的重要體現。
(三)明清河湟少數民族文人漢語詩文創作
明清時期,少數民族文人漢語詩文創作逐漸增多。馬應龍是河湟地區回族名臣,以詩文盛名,現存詩三首:《馬嶺關有感書兩當公館》《鎮邊樓》《贈都督魯元常》。河湟李土司家族以軍功起家,后注重學習儒家文化,家族成員大都能文。《李氏家譜》中收錄了李氏家族成員撰寫的序跋、碑記、疏文、祭文等共計 34 篇。李完有《重修碾伯城隍廟記》《碾伯重修真武廟記》《請革莊浪參將帶管西寧疏》存世。據《西寧府新志》記載:“李完,會寧伯英后也。中嘉靖戊子科鄉試,任直隸衡水縣知縣。甫釋褐,即以家人產推于兄。生平衣不重采,食無兼味,清苦有冰蘗聲。居官蕭然如水,尋亦解組而歸。杜戶讀書,無間寒暑,閉影公門,人高其節。工古文詞。” 李完一生高風亮節,在《請革莊浪參將帶管西寧疏》中,他仗義執言:“至正德年間,權珰用事,賄賂公行,是以將官希圖剝削,遂使分守莊浪參將帶管西寧職銜,保障之功罔聞,誅求之慘已極。
仰惟皇上登極之初,首革弊政,偏汰天下冗員,今照帶管參將,延今未革者,蓋緣奸貪將官,假以西海未靖為名。虛張猗角之局,陰為漁獵之鉺,徒亂舊章,靡臻實效。臣目擊為地方害,不勝痛憤,是以不揣狂率,謹列其帶管之不可者陳之。” 疏文條理清晰,有理有據,慷慨激昂,飽含對貪官污吏的痛憤之情,革除了莊浪參將代管西寧一事,使西寧地區人心大快。蒙古族詩人郭守邦《皇清郭氏家譜引》:“今而后,前有所考,后有所承,即世遠年湮,亦不致本支莫辨,統系不明,而少紊其昭穆,暗于親疏,爽其隆殺,忘其宗祧也。方且快史學之垂誡,石碣之啟佑,其裨于后人也良深哉。” 詳明世系,教化后人,闡述家譜的重大作用。河湟地區少數民族文人漢語詩文創作不僅是其自身努力的結果,也是文學交融的結晶。他們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不斷加強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同時也使得文學交融得到了長足發展。
四、結語
“文學作為文化的獨特藝術表現形式,與其所處的地域環境關系密切。一定地域內的自然環境特點以及由此所衍生的生產、生活方式,使得不同區域內的文化以及民風民性呈現出不同的審美取向,從而在文學上表現出相異的地域特色。” 文學與地域的關系不僅在于地域影響了文學的基調和整體特色,還在于文學對地域的反作用。河湟地區獨特的地域文化內蘊在作家的精神世界之中,并外化于他們詩文作品里,而河湟詩文中的文學景觀也成為反映河湟地域自然風景、風土人情和社會風貌的歷史鏡像。同時,河湟地區特殊的地理位置為中華各民族交匯融合提供了重要的場域。“各民族在文化上兼收并蓄、經濟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親近的歷史進程中匯聚成強大的中華力量。”
中華文學作為中華文化的重要載體,從來就是中華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過程中凝結而成的共有文化血脈。儒家文化在河湟地區的傳播,推動了河湟詩文創作的發展;外來文人帶來的詩書傳統,促進了河湟詩文創作的繁榮。同時,他們將河湟文化融入自己的筆墨之中,豐富了中華文學的內容。將河湟詩文創作置于中華各民族文化交融的大背景下,對于全面認識交融一體的中華文學具有重要的參考與借鑒意義。
多洛肯;晏慶波,西北民族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部,202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