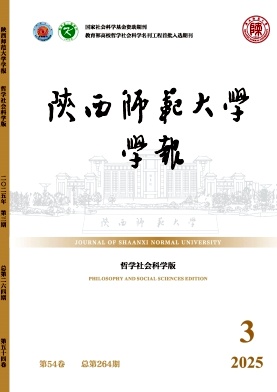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雜志投稿格式參考范文:漢唐時期人們對海岸的觀察與認識
時間:
一、臨山瞰海
所謂臨山瞰海,即觀察者登上鄰近海岸或位于海岸的山丘觀察海陸交界線,是中國古代早期人們觀察、認識海岸及海岸地帶的主要途徑之一。人們通過這種方式所認識的海岸主要是山地丘陵海岸,也包括山前平原地帶。
《史記》卷 6《秦始皇本紀》記秦始皇二十八年(前 219)東巡,上泰山、禪梁父之后,“乃并勃海以東,過黃、腄,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秦德焉而去” ,復南登瑯邪,作瑯邪臺,刻石謂其 “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 ,又述其疆土所至,“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 。二十九年(前 218)東巡,登之罘,刻石云:“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照于海” ,其東觀刻石云:“皇帝春游,覽省遠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臨朝陽” 。成山、瑯邪、之罘,均窮陸臨海,秦始皇登之 “臨照于海”,“昭臨朝陽”,刻石以示疆界所至,當即其時觀念中的海岸所在。
《史記》卷 28《封禪書》綜述秦始皇東巡,謂其 “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其中,三山祠陰主、之罘祠陽主、萊山祠月主 “皆在齊北,并勃海”;成山 “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故祠日主;瑯邪 “在齊東方,蓋歲之所始”,故祠四時主。三山、之罘、萊山、成山、瑯邪 5 座臨海之山,皆位于古代濱海人群漁撈系船的港口附近,用于望風祭海,后來逐漸演變為齊國臨海疆界的標志。《晏子春秋》卷 4《內篇問下》記齊景公之言:“吾欲觀于轉附、朝舞,遵海而南,至于瑯琊。” 轉附、朝舞,亦當為臨海之山。在齊人觀念中,遵海而行,得觀乎轉附(或說即之罘)、朝舞,至于瑯邪。據此,先秦時期的齊人對于山東半島海岸已有基本認識。
《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始皇三十二年(前 215)“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 ,《史記・封禪書》說秦始皇 “游碣石,考入海方士” 。碣石當是燕地方士集聚并由此入海的出發之地。關于碣石的認識,其初當來自燕地的方士。《史記・封禪書》謂:“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高最后皆燕人,為方仙道,形解銷化,依于鬼神之事” ,又謂:“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 。自戰國以來,燕齊海上之方士當頗有來往,他們對于渤海沿岸的認識,當漸融為一體。秦始皇三十二年游碣石,自上郡歸,往途當經由齊地。秦始皇的碣石之行,說明齊、燕關于海岸的認識已經融匯。秦始皇三十五年(前 212),又 “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為秦東門” 。《漢書》卷 28 上《地理志》東海郡朐縣原注:“秦始皇立石海上以為東門闕。”《水經注》卷 30《淮水》謂淮水下游北支游水東北流,歷朐縣與沭水相合,“又逕朐山西,山側有朐縣故城。秦始皇三十五年,于朐縣立石海上,以為秦之東門。崔琰《述初賦》曰‘倚高艫以周眄兮,觀秦門之將將’者也。東北海中有大洲,謂之郁洲。《山海經》所謂‘郁山在海中’者也。言是山自蒼梧徙此,云山上猶有南方草木。今 [青](郁)州治”。朐山東鄰海岸,與郁洲島隔海峽相望,西側有游水流經。秦東門在朐山(今之孔望山)以東、郁洲(今云臺山)以西。碣石門、秦東門闕,都建在海岸上,無論其本來寓意若何,在客觀上都起到了標識海岸的作用。
《史記・秦始皇本紀》記秦始皇三十七年(前 210)東巡,至錢唐,渡浙江,“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 。秦始皇所上之 “會稽”,當即會稽山;其所望之 “南海” 則為今之東海。《越絕書》謂越王勾踐 “東垂海濱” ,敗于夫差后,“保棲于會稽山上” 。《漢書・地理志》會稽郡山陰縣原注:“會稽山在南,上有禹冢、禹井,揚州山。” 勾踐滅吳后,置吳王于甬東,君百家。杜預曰:“甬東,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越絕書》謂勾踐 “行霸瑯邪” ,“越王句踐徙瑯邪…… 楚考烈王并越于瑯邪” 。《山海經》卷 13《海內東經》謂瑯邪臺 “在渤海間,瑯邪之東。其北有山。一曰在海間。” 郭璞注云:“今瑯邪在海邊,有山礁峣特起,狀如高臺,此即瑯邪臺也。瑯邪者,越王句踐入霸中國之所都。”《漢書・地理志》瑯邪郡瑯邪縣原注:“越王句踐嘗治此,起館臺。〔有〕(存) 四時祠。” 會稽山、甬東、瑯邪,是先秦時期越人臨海或遵海而行所至之地。齊人與越人對于海岸的認識,在瑯邪相接,當不晚于春秋后期。
秦始皇離開會稽后,“還過吳,從江乘渡”。江乘,漢屬丹揚郡,張守節《正義》謂:“江乘故縣在潤州句容縣北六十里,本秦舊縣也。渡謂濟渡也。”《宋書》卷 35《州郡志》謂晉成帝咸康元年(335),桓溫領僑置之南瑯邪郡,“鎮江乘之蒲洲金城上,求割丹陽之江乘縣境立郡,又分江乘地立臨沂縣”。秦漢時江乘縣臨江,轄境包括江中之洲。江乘對岸,即赤岸。山謙之《南徐州記》曰:“京江,禹貢北江。春秋分朔,輒有大濤至江乘,〔北〕(此) 激赤岸,尤更迅猛。” 則海潮可上溯至江乘縣。阮敘之《南兗州記》記赤岸山在瓜步山(在六合縣東南 20 里)東 5 里,“濤水自海入江,沖激六七百里,至此岸側,其勢始衰”。山謙之《南徐州記》曰:“京江,《禹貢》北江也。闊漫三十里,通望大壑,常以春秋朔望,輒有大濤,聲勢駭壯,極為奇觀。濤至江北激赤岸,尤更迅猛。” 秦始皇由江乘渡江,正是在溯江而上的海潮潮至線上,自此而下,即被視為大海,故《史記》謂其渡江后 “并海上,北至瑯邪”。枚乘《七發》假托客之言,說他 “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游兄弟,并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其所見之濤 “秉意乎南山,通望乎東海。虹洞兮蒼天,極慮乎崖涘”,劉良注曰:“言濤之秉意,將陵乎南山,而與東海相望也。虹洞,相連貌也。言若與天地相連也。有極盡思慮者,言思至于山崖海涘而不能入其深也”。雖是詩人想象之辭,然曲江之濤,與東海相望,與天地相連,實為時人普遍之觀念。南朝宋劉〔損〕(楨)《京口記》說北固山 “回嶺入江,懸水峻壁”,“北望海口,實為壯觀”。京口北固可北望海口,是望海之山。
秦始皇由江乘渡江后,傍海岸而行(“并海上”),“北至瑯邪”,復自瑯邪北至榮成山,至之罘,射殺一魚,然后 “并海西”。《史記・封禪書》說秦始皇此次出巡,“登會稽,并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 。秦二世元年(前 209),東行郡縣,“到碣石,并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 。這樣,先秦以來燕、齊、越沿海諸國之人沿海航行的經驗及其對于海岸的認識遂得貫通起來。
在今見文獻中,先秦秦漢時期有關浙南閩粵海岸的認識較為模糊。《山海經》卷 10《海內南經》謂:
海內東南陬以西者。甌居海中。閩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閩中山在海中。三天子鄣山在閩西海北。一曰在海中。
觀察敘述者立足于閩西北或閩西的山(或三天子鄣山),看 “在海中” 的閩或閩中山以及 “居海中” 的甌,那么,閩海(以及甌海)的西北岸是山。其言雖模糊迷離,然臨山觀海的視角仍然非常清楚。
《史記》卷 113《南越列傳》記秦末南海尉任囂語龍川令趙佗曰:“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 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初學記》卷 8《州郡部》引《南越志》曰:“番禺縣有番、禺二山,因以為名。”《元和郡縣圖志》謂番山在南海縣東南 3 里,禺山在縣西南 1 里,“尉佗葬于此”。任囂所說 “負山險,阻南海” 的番禺,當即指番、禺二山(或因此二山而得名之番禺縣)。元鼎六年(前 111),漢軍進至番禺,南越王趙建德、丞相呂嘉守城失敗,“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以船西去” ,也說明番禺近海。《水經注》卷 37《泿水》記漢末建安中,步騭到南海,“見土地形勢,觀尉佗舊治處,負山帶海,博敞渺目,高則桑土,下則沃衍,林麓鳥獸,于何不有?海怪魚鱉,黿鼉鮮鱷,珍怪異物,千種萬類,不可勝記…… 騭登高遠望,睹巨海之浩茫,觀原藪之殷阜,乃曰:斯誠海島膏腴之地,宜為都邑。建安二十二年,遷州番禺,筑立城郭,綏和百越,遂用寧集”。步騭所登之山,亦即番山、禺山。步騭在番、禺登高遠望,見巨海浩渺,故以南海郡已臨南海。
碣石、三山、之罘、萊山、成山、瑯邪、朐山、江乘(以及赤岸、瓜步山、北固山)、會稽山、三天子鄣山、番山、禺山等,自先秦秦漢以來,當即人們登臨觀海的海岸山丘,在遵海(并海)航行時也可作為標識,發揮了界定海岸位置的作用,構成了古人觀念中的海岸。
在上述諸山(岸、臺)中,碣石、三山、之罘山、成山、瑯邪臺、朐山都緊臨大海,位于海岸線上,其所在海岸也都是山地丘陵海岸。比如碣石,《尚書・禹貢》謂為冀州山,“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海” 。又謂 “太行王屋,至于碣石,入于海。” 孔安國傳:“碣石,海畔山。” 元封元年(前 110),漢武帝東巡,“自泰山,復東巡海上,至碣石”。文穎謂碣石 “在遼西絫縣。絫縣今罷,屬臨榆。此石著海旁。” 顏師古說:“碣,碣然特立之貌也。” 建安十二年(207),曹操率軍東征烏桓,作《步出夏門行》,謂:“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粲爛,若出其里”。顯然,碣石就在海岸上。宋玉《高唐賦》描述云夢水勢激蕩,謂:“勢薄岸而相擊兮,隘交引而卻會。崪中怒而浮高兮,若浮海而望碣石。” 劉良注:“碣石,海畔山,半在水中。言此水波濤崪然而起爾,如望碣石以浮海也。” 因此,碣石山應當是伸入海中的半島。《水經注》卷 14《濡水》謂濡水東南流,至絫縣碣石山,“漢武帝亦嘗登之,以望巨海,而勒其石于此。今枕海有石如埇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見,立于巨海之中,潮水大至則隱,及潮波退,不動不沒,不知深淺,世名之天橋柱也。狀若人造,要亦非人力所就。韋昭亦指此以為碣石也”。
可是,會稽山、赤岸山、北固山、番山、禺山等,雖然登臨可眺望大海,但是這幾座山下卻并非海岸。赤岸、瓜步山、北固山,固然離長江入海口甚遠,番、禺二山,離珠江入海口也并不近。晉人裴淵《廣州記》曰:“廣州東百里有村,號曰古斗村,自此至海,溟渺無際。”《元和郡縣圖志》卷 34“嶺南道,廣州” 謂廣州正南至大海 70 里,又謂南海在南海縣南,水路百里,“自州東八十里有村,號曰古斗,自此出海,浩淼無際”,海廟即位于其地。而在廣州地區,真正臨海的是古斗村。《太平寰宇記》卷 157“嶺南道,廣州” 記南海縣有靈洲山,引《南越志》云:“肅連山西一十二里,有靈洲焉。其山平原彌望,層野極目”,又有江南洲,《南越志》云:“江南洲,周回九十里。東有荔枝洲,上有荔枝,冬夏不凋。北有雞籠岡,上多蟶蠣”。所以,步騭在番、禺二山登高遠望,所見當是河湖相連、洲澤浩茫、原藪殷阜的珠江三角洲平原,是 “膏腴之地”,并非 “浩淼無際” 的漲海。
秦始皇登臨望海的會稽山,與海岸間也有一定距離。《水經注》卷 40《漸江水》記會稽郡城正南有秦望山,“為眾峰之杰,涉境便見”,“秦始皇登之以望南海”,“自平地以取山頂,七里”,又有會稽之山,在秦望山之南,山下有禹廟,“秦始皇登稽山刻石紀功,尚存山側”。秦望山、會稽山,其西的覆斗山與其東的石匱山、射的山、石帆山構成一道大致東西走向的山巒。在這道山巒前,有一連串的湖泊,覆斗山前(北)是長湖,“湖廣五里,東西百三十里。沿湖開水門六十九所,下溉田萬頃,北瀉長江” 。
二、浮舟觀岸
浮舟觀岸包括兩種方式:一是從內地順河入海,即沿著河流入海,觀察、描述河流下游兩岸及入海口兩側海岸的地理面貌;二是由海入河,即從海上乘船溯河口而上,進入內河,沿途觀察河口海岸及河流三角洲地區。這是漢唐時期人們認識海岸的又一途徑,其所認識的河口海岸主要是平原海岸,包括河流入海口受到海潮頂托而形成的沙堤、沙洲與澙湖等。
(一)順河入海的觀察
《元和郡縣圖志》卷 10“河南道,青州” 記濟水流逕博昌縣,東北流入海,其入海之處在縣東北 280 里,“水口謂之海浦”。敘述者從博昌縣出發,順著濟水,來到濟水入海口,觀察海浦(水口)。
漢代臨淮郡(下邳國)領有淮浦縣。《水經注・淮水》謂 “淮水東至廣陵淮浦縣入于海。” 酈注引應劭曰:“浦,岸也。蓋臨側淮噴,故受此名。”《山海經・海內東經》謂淮水出朝陽東余山,“入海,淮浦,北”。《漢書・地理志》南陽郡平氏縣原注:“《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東南至淮〔浦〕(陵) 入海,過郡四,行三千二百四十里,青州川。” 這些敘述,都是沿著淮水,從其源頭,直到入海處,淮浦即當位于淮水入海口。
南方河流大多可以通航,沿著河流入海的描述主要來自乘船沿河航行的觀察。《吳都記》謂:“松江東瀉海口,名曰扈瀆”,敘述的角度是順著松江而下進入海口。《輿地志》解釋扈瀆之得名,謂:“扈業者,濱海漁捕之名。插竹列于海中,以繩編之,向岸張兩翼。潮上即沒,潮落即出,魚隨潮,礙竹不得去,名之云扈”。觀察者顯然是立身于舟船去看岸邊排列的竹編,故謂其 “向岸張兩翼”。
《漢書・地理志》會稽郡毗陵縣原注:“江在北,東入海,揚州川。” 吳縣原注:“南江在南,東入海,揚州川。” 丹揚郡蕪湖縣原注:“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揚州川。” 其中,中江至陽羨所入之 “海”,實為具區澤(震澤,今太湖);在吳縣南、東流入海的南江,一般認為即后世之松江;流經毗陵縣北之江,據《續漢書・郡國志》吳郡毗陵縣原注,又被稱為 “北江”,當即大江。“三江” 是 3 條水路,相關敘述反映了沿著水路航行的觀察。王充《論衡》卷 4《書虛篇》說傳言伍子胥被殺恚恨、驅水為濤、以溺殺人,“今時會稽丹徒大江,錢唐浙江,皆立子胥之廟。蓋欲慰其恨心,止其猛濤也”。是以潮濤可上溯至丹徒(今鎮江)。毗陵(今常州)在丹徒之東,《漢書・地理志》以之為大江入海口南岸地。《漢書・地理志》臨淮郡海陵縣原注:“有江海會祠”,大江當在海陵縣南入海。因此,漢代毗陵、海陵二縣分處大江入海口的南北兩岸,皆以 “陵” 為稱,反映出大江入海口兩岸地勢略高,當即后世長江三角洲地區所謂 “高地”。岸上高地稱為 “陵”,正說明觀察者身在江中舟上。今本《水經注》卷 29《沔水》經文謂北江過毗陵縣北,注文稱:“丹徒縣北二百步有故城,本毗陵郡治也。舊去江三里,岸稍毀,遂至城下。城北有揚州刺史劉繇墓,淪于江”。當是漢晉六朝間,丹徒江岸受到沖刷,逐步南移。敘述者雖立足于丹徒故城,但 “岸稍毀,遂至城下” 一語仍反映出其來自江面的視角。
今本《水經注・沔水》述松江 “上承太湖,東逕笠澤”;自湖東北流 70 里,有水口(謂之三江口),分流:“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與松江而三也”。此種敘述,當來自乘船由太湖至水口、分途入海的觀察記錄。《元和郡縣圖志》卷 25“江南道,蘇州” 說松江在吳縣南 50 里,經昆山入海。《太平寰宇記》卷 91“江南道,蘇州” 謂松江自太湖出海,“屈曲七百里,出鱸魚”;又說松江一名吳江,出太湖,東 260 里入大海。凡此,均當出自沿不同水路入海的觀察、描述。《太平寰宇記》卷 91“江南道,蘇州” 記吳縣東北 100 里有袁山松故城,筑于東晉隆安四年(400),在滬瀆江邊,“今為陂湖所沖,已半毀江中。山松城東三十里夾江有二城相對,闔閭所筑,以備越處”。袁山松城、闔閭城,皆在滬瀆下游近海處,地勢低洼。袁山松城 “已半毀江中”,闔閭城 “夾江二城相對”,都是從江中向岸上觀察所得的認識。據《水經注・沔水》所載,由三江口分水東南入海的東江,即谷水(又稱長水),東南流,逕由拳故城下、嘉興縣城西、鹽官縣故城南、馬皋城,在海鹽縣出為澉浦,“以通巨海。光熙元年,有毛民三人,集于縣,蓋泛于風也”。澉浦是東江(谷水)入海之口。關于谷水的敘述是順水而下直至海口。注文謂海鹽縣馬皋城乃晉時司鹽都尉城,“吳王濞煮海為鹽,于此縣也”。海鹽縣治 “后淪為柘湖,又徙治武原鄉,改曰武原縣,王莽名之展武。漢安帝時,武原之地,又淪為湖,今之當湖也,后乃移此” 。海鹽縣治屢次淪陷為湖,說明其所處海岸頗不穩定,是典型的侵蝕海岸。
《漢書・地理志》丹揚郡黝縣原注:“漸江水出南蠻夷中,東入海”,不言其入海之地。石城縣原注:“分江水首受江,東至余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 在石城分江之水,無以東至余姚入海,故歷來論者,均懷疑分江水之存在。在余姚入海之江,只能是漸(浙)江水。故合二注,或當作 “漸江水出南蠻夷中,東至余姚入海”。今本《水經注・漸江水》經文 “北過余杭,東入于海” 句下注文乃酈道元裁剪拼接所見地方史志相關記載而成,然其基本脈絡,仍然是順水而下以至于海,故仍可見出浙江水入海口的若干地理面貌。《水經注・漸江水》注文述浙江東逕靈隱山,山下有錢唐故縣,浙江逕其南,防海大塘在縣東 1 里許,縣南江側有明圣湖,“縣東有定、包諸山,皆西臨浙江。水流于兩山之間,江川急浚,兼濤水晝夜再來,來應時刻,常以月晦及望尤大,至二月、八月最高,峨峨二丈有余”。據此,定、包諸山在浙江東岸,控扼錢塘潮。《水經注》接著記浙江北合詔息湖,“湖本名阼湖,因秦始皇帝巡狩所憩,故有詔息之名也”。《初學記》卷 7《地部》謂 “錢塘有明圣湖、淮湖、承湖。承湖一名詔息湖。” 又引《錢塘記》:“去邑十里有詔息湖。古老相傳:昔秦始皇巡狩,經途暫憩,因以詔息為名。”《水經注》接著說:
浙江又東,合臨平湖。《異苑》曰:晉武時,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 傳言此湖草穢壅塞,天下亂;是湖開,天下平。孫皓天璽元年,吳郡上言:臨平湖自漢末穢塞,今更開通……《錢塘記》曰:桓玄之難,湖水色赤,熒熒如丹。
從靈隱山、防海塘、浙江潮,到詔息湖、臨平湖,敘述的順序沿著浙江入海口北岸,自西南向東北展開。臨平湖壅而復開事,見于《三國志》卷 48《吳書・三嗣主傳》,謂孫皓天璽元年(276)“吳郡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更開通。長老相傳,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蓋臨平湖與浙江水(杭州灣)之間的自然堤,為大潮沖決,故岸崩湖開。
北方有的河流航行不便,或不能通航,關于此類河流入海口的記述,應主要來自沿著河岸的觀察;對于能夠通航河流的記述,則可能來自乘舟航行時的觀察。由于河流尾閭大都地勢低洼,土壤鹽鹵成份較高,不便墾殖,居民較少,而以鹽民為主,所以,相關描述多與海鹽生產、運銷相關,反映的也多是平原海岸地貌。
《漢書・地理志》瑯邪郡邞縣原注:“膠水東至平度入海。”《水經注》卷 26《膠水》記膠水下 游北逕平度縣,“縣有土山。膠水北歷土山,注于海。海南,土山以北,悉鹽坈相承,修煮不輟。北眺巨海,杳冥無極,天際兩分,白黑分明,所謂溟海者也”。觀察者應當是沿著膠水河岸,到達膠水入 海口的土山,“北眺巨海”,見溟海杳冥;近觀山北海南 “鹽坈相承,修煮不輟”。這里所描述的,是典型的平原海岸地貌。
《漢書・地理志》北海郡桑犢縣原注:“覆甑山,溉水所出,東北至都昌入海。” 瑯邪北海郡都昌縣原注:“有鹽官。” 都昌縣的產鹽區,當即在溉水入海口兩側。《水經注・巨洋水》記溉水出桑犢亭東覆甑山,北逕斟亭西北、寒亭西,合白狼水。白狼水東北流逕平壽城東,“西入別畫湖,亦曰朕懷湖。湖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東北入海”。其中,別畫湖(朕懷湖)“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應當是指湖岸的長寬。所以,這里的敘述,也是行走于陸地上的觀察。別畫湖位于白狼水下游,湖水東北入海,應當是受海潮頂托形成的濱海湖泊。
《漢書・地理志》千乘郡博昌縣原注:“時水東北至鉅定入馬車瀆,幽州浸。” 齊郡廣縣原注:“為山,濁水所出,東北至廣饒入鉅定。” 臨朐縣原注:“石膏山,洋水所出,東北至廣饒入鉅定。” 鉅定縣原注:“馬車瀆水首受鉅定,東北至瑯槐入海。” 據此,時水、濁水、洋水均流入鉅定澤(巨淀湖),澤水出為馬車瀆水,東北流,至瑯槐縣境入海。諸水均圍繞鉅定澤,以鉅定澤為中心形成一個水網體系,相互間可以通航。《水經注》卷 26《淄水》記濁水、女水并注巨淀,北流為馬車瀆,北流,合淄水、時澠水。“淄水入馬車瀆,亂流東北,逕瑯槐故城南,又東北逕馬井城北,與時澠之水,互受通稱,故邑流其號。又東北至皮丘坈入于海。故晏謨、伏琛并言淄澠之水合于皮丘坈西。《地理志》曰:馬車瀆至瑯槐入于海,蓋舉縣言也。” 皮丘坈是產鹽地。伏琛《齊地記》曰:“齊有皮邱坑,民煮坑水為鹽,石鹽似之。” 鉅定澤以北濱海地域,海濱多有鹽坈分布,也是典型的平原海岸。《水經注》卷 26《巨洋水》記巨洋水西北流,注于巨淀,自湖東北流,逕壽光縣故城西,合堯水;復東北流,逕望海臺西,“或言秦始皇升以望海,因曰望海臺”,“又東北注于海”。其地平衍,須升臺方得望海。
巨淀(鉅定)湖之北,就是黃河下游泛濫區。王莽時,大司空掾王橫上言治河方略,謂:“河入勃海,勃海地高于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當洪水時節,華北平原東部河流漫溢,河海相連,漫無天際,難辨海岸。河水下游漫溢橫流,既不便沿岸而行,舟行水中也往往難辨河湖,故時人對于河水尾閭,往往僅得言其大概,不得詳述。
《水經注》卷 5《河水》經文記河水 “東北過蓼城縣北,又東北過甲下邑,濟水從西來注之,又東北,入于海。” 注文記黃河下游東流,逕千乘城北之后,分為二水:枝津東逕甲下城南,東南歷馬常坈,注濟水;正流東北流,逕甲下邑(即倉子城)北,又東北流,入于海。《水經濟》卷 8《濟水》經文謂濟水下游東北流,“過甲下邑,入于河。” 注文記濟水東北流,逕甲下邑南,東歷瑯槐縣故城北,又東北,納河水枝津,又東北入海。河水枝津與濟水均東流經甲下邑南,然后在馬常坈合流,東北流入海。馬常坈當是河濟入海處的湖澤洼地。
《水經注》卷 9《淇水》記淇水(清河)下游東北流,枝分出無棣溝,東流,逕南皮縣故城南、樂亭北、新鄉城北、樂陵郡北、苑鄉故城南、高城縣故城南,東北流,過功城、鹽山,東北入海。清河(淇水)主流東北逕南皮縣故城西、北皮城東,左會滹沱別河故瀆,復東北流,枝分浮水故瀆。浮水在浮陽縣境內分清河,東北流,逕高城縣之苑鄉城北,東逕章武縣故城南、篋山北、柳縣故城南,“浮瀆又東北,逕漢武帝望海臺。又東注于海。應劭曰:浮陽,浮水所出,入海。潮汐往來日再。今溝無復有水也。” 其下文又說:清河枝津(當即浮水)“東逕漢武帝故臺北。《魏土地記》曰:章武縣東一百里,有武帝臺。南北有二臺,相去六十里,基高六十丈。俗云,漢武帝東巡海上所筑。又東注于海。” 按:《魏書》卷 160 上《地形志》滄州浮陽郡章武縣原注:“治章武城。有漢武帝臺。漳水,入海。有沾水。大家姑祠,俗云海神,或云麻姑神。” 潮汐可溯浮水而上,直到章武、浮陽,其地勢甚為低洼。漢武帝望海臺,在章武縣東 100 里,而章武縣距海岸更遠。《水經注》又記清河東北流,逕纻姑邑南、窮河邑南;又東流,“逕漂榆邑故城南,俗謂之角飛城。《趙記》云:石勒使王述煮鹽于角飛,即城異名矣。《魏土地記》曰:高城縣東北 100 里,北盡漂榆,東臨巨海,民咸煮海水,藉鹽為業。即此城也。清河自是入于海”。從章武縣到漢武帝望海臺,高城縣到角飛城,都還有 100 多里,海岸更在其東。高城以東濱海地帶民戶多煮鹽為業,則其地勢也甚為低洼,潮水方可上溯較遠。相關描述皆關注潮至點的位置,反映出鹽民的視角。
《漢書・地理志》漁陽郡漁陽縣原注:“沽水出塞外,東南至泉州入海,行七百五十里。”《水經注》卷 12《巨馬河》述巨馬河在泉州縣西南,合八丈溝水,“亂流東注”;在平舒城北,入于虖池水,“同歸于海”。漯水東至漁陽雍奴縣西,入笥溝(潞河)。“漯水東入漁陽,所在枝分,故俗諺云,高梁無上源,清泉無下尾。蓋以高梁微涓淺薄,裁足津通,憑藉涓流,方成川甽。清泉至潞,所在枝分,更為微津,散漫難尋故也。”
(二)由海入河的觀察
西漢會稽郡領有回浦縣,東漢前期廢為鄞縣回浦鄉,東漢章和元年(87)復立為章安縣。《續漢書・郡國志》會稽郡章安縣下劉昭注引《晉太康記》曰:“本鄞縣南之回浦鄉,章帝章和元年立。” 東漢后期至南朝章安縣在今臺州市椒江區章安鎮(鎮中仍有地名為 “回浦村”),“回浦” 之名,本當指靈江(臨海江,今椒江)彎曲的入海口。《漢書》《續漢書》等早期文獻均不言靈江源流,“回浦” 之謂,當是指由海上進入靈江所見河口沿岸,頗多彎曲。
漢武帝元鼎六年(前 111)置合浦郡、合浦縣。其地,唐宋時分屬廉、欽二州。《武經總要前集》卷 20《邊防》記欽州臨漲海,沿海有咄步水口、抵棹水口、如洪水口,均為入海路,至交趾潮陽鎮;廉州 “地控海口”,有象鼻沙大水口、譚家水口、黃標水口、藏涌水口,西陽水口、大灣水口、大亭水口,并入海之路;又說 “舊從康淥場陸行,至舊廉州六程,有海湧,共六處水口”。其所說之 “水口”,當即欽江、合浦江(今南流江)下游各分流入海之口。合浦之名,或即得之于諸水口之海浦。對上述水口的認識,應當來自沿海航行的觀察。
漢九真郡治胥浦縣。《水經注》卷 36《溫水》引《林邑記》曰:“義熙九年,交趾太守杜慧期造九真水口,與林邑王范胡達戰”,胡達遁;五月,“慧期自九真水歷都粟浦,復襲九真。長圍跨山,重柵斷浦”,《水經注》接著即引《漢書・地理志》,謂:“九真郡,漢武帝元鼎六年開,治胥浦縣”。都粟浦即漢代胥浦,在九真水(今越南馬江)南,當即胥水(今越南朱江)入海口。杜慧期從海上進入九真水口,擊敗胡達;復轉入都粟浦(胥浦),進攻九真郡(治胥浦縣)。“長圍跨山,重柵斷浦”,是在浦口立柵阻斷水路。《水經注・溫水》謂交趾郡有南都官塞浦,越安定黃岡心口,“至鑿口,馬援所鑿,內通九真浦陽”,又引《交州記》曰:“鑿南塘者,九真路之所經也,去州五百里。建武十九年,馬援所開”。其下文則謂:“郁水又南,自壽泠縣注于海。昔馬文淵積石為塘,達于象浦,建金標為南極之界”。馬援所鑿之塘之性質若何、究在何處,史書所言不詳,后世學者眾說紛紜。《太平寰宇記》卷 171 “嶺南道” 愛州軍寧縣 “鑿口” 條謂:“即馬援開石道處。按《廣州記》云:‘馬援鑿九真山,即石為堤,以遏海波,自是不復遇海漲’”。上引馬援所鑿南塘,當自海岸鑿通水道,通達九真浦陽。九真浦,當即九真水入海之口(九真水口);九真山,亦當在九真水之側。然則,馬援所開鑿口,即在九真水與胥水之間,是溝通九真水與胥水的運河。馬援昔年領軍,蓋由九真口進入九真水,開鑿口溝通九真水與胥水,轉入都粟浦。
胥浦之南,有朱吾縣浦。朱吾亦漢縣,屬日南郡。《續漢書・郡國志》日南郡朱吾縣劉昭注補引《交州記》曰:“其民依海際居,不食米,止資魚。” 是朱吾縣瀕海。《水經注・溫水》引《林邑記》曰:“渡比景至朱吾。朱吾縣浦,今之封界。”“縣南有文狼究,下流逕通。”“朱吾浦內通無勞湖,無勞究水通壽泠浦。” 蓋文狼究即無勞究,水北入無勞湖,湖水復東入海,即為朱吾縣浦。“無勞究水通壽泠浦”,當是指由無勞究入海口可航海至壽泠浦。
四會浦在朱吾縣浦之南。《水經注・溫水》記四會浦水 “上承日南郡盧容縣西古郎究,浦內漕口,馬援所漕。水東南屈曲通郎湖,湖水承金山郎究,究水北流,左會盧容、壽泠二水”。郎湖,下文又作狼湖,謂其浦口有秦時象郡墟域,“自湖南望,外通壽泠,從郎湖入四會浦”。又謂 “自四會南入,得盧容浦口”。康泰《扶南記》曰:“從林邑至日南盧容浦口,可二百余里。從口南發,往扶南諸國,常從此口出也。” 晉永和七年(351),督護滕畯率交廣兵討范佛,“進軍壽泠浦,入頓郎湖”。劉宋元嘉二十三年(446),交州刺史檀和之從日南征林邑,“從四會浦口,入郎湖,軍次區粟,進逼圍城”,斬區粟王范扶龍首。根據這里的記載,盧容浦、壽泠浦、郎究浦當分別是盧容、壽泠、金山郎究水入郎湖之口,而四會浦則當是郎湖水入海之口。《水經注・溫水》引《林邑記》謂其地 “地濱滄海,眾國津逕”。《宋書》卷 97《夷蠻傳》記元嘉八年(431)林邑王范陽邁 “遣樓船百余寇九德,入四會浦口”,交州刺史阮彌之遣隊主相道生三千人赴計,攻區粟城不克,引還。《水經注・溫水》記此役由阮謙之率領劉宋軍隊 7000 人,“先襲區粟,以過四會,未入壽泠,三日三夜,無頓止處。凝直海岸,遇風大敗”,后又與楊邁(當即陽邁)軍在壽泠浦中相遇,暗中混戰,各有損失,謙之引軍還渡壽泠。區粟城在盧容、壽泠二水之間,即漢時西卷縣故址,去林邑步道 400 余里,“三方際山,南北瞰水,東西澗浦,流湊城下”。“林邑兵器戰具,悉在區粟。” 林邑王范陽邁(楊邁)、阮謙之、檀和之均由海上進入四會浦,復由四會浦進入壽泠浦,然后由壽泠浦進至區粟城下。《林邑記》《宋書・夷蠻傳》的有關記載,都是由海上進入海浦(水口)的描述。
四會浦之南,有阿賁浦、林邑浦。《水經注・溫水》記東晉升平三年(359),溫放(又作溫放之)征林邑王范佛,“入新羅灣,至焉下,一名阿賁浦。入彭龍灣,隱避風波,即林邑之海渚”。溫放蓋由交州沿海航行,過四會浦后,到新羅灣,至焉下,進入阿賁浦。復南行,至彭龍灣,入林邑浦。《水經注・溫水》記元嘉二十三年,檀和之破區粟后,“飛旌蓋海,將指典沖,于彭龍灣上鬼塔,與林邑大戰,還渡典沖。林邑入浦,令軍不進,持重故也。浦西即林邑都也,治典沖,去海岸四十里。處荒流之徼表,國越裳之疆南,秦漢象郡之象林縣也。東濱滄海,西際徐狼,南接扶南,北連九德”。其下文又記在典沖入海之水名淮水,典沖城 “西南際山,東北瞰水,重塹流浦,周繞城下”。林邑國都所臨之浦,當即淮水入海之口。《水經注・溫水》引竺芝《扶南記》曰:
自扶南去林邑四千里,水步道通。檀和之令軍入邑浦,據船官口城六里者也。自船官下注大浦之東湖,大水連行,潮上西流。潮水日夜長七八尺,從此以西,朔望并潮,一上七日,水長丈六 七。七日之后,日夜分為再潮,水長一二尺。春夏秋冬,厲然一定,高下定度,水無盈縮,是為海運。亦曰象水也,又兼象浦之。《晉・功臣表》所謂 “金潾清逕,象渚澄源” 者也。
酈注于此段注文前,謂:“其水又東南流逕船官口,船官川源徐狼”。“其水” 當指淮水,則 “邑浦” 當即林邑浦,亦即林邑之海渚。蓋淮水入海口被稱為大浦,又稱彭龍灣,應當是喇叭形的海灣。東湖在大浦之內,接納船官川水。《續漢書・郡國志》日南郡象林縣下劉昭注補引《交州記》曰:“有采金浦。” 據上引《水經注・溫水》,漢象林縣即在林邑浦西,則《交州記》所說之采金浦,當即林邑浦。檀和之在四會浦攻陷區粟城后,沿海南來,到彭龍灣,進入林邑浦(當即象浦、采金浦)。淮水、船官水均注入林邑浦。檀和之宋軍溯淮水而上,進至浦西 40 里的典沖城。
四會浦是郎湖水入海之口,由四會浦可進入郎湖,再由郎湖可入壽泠浦、郎究浦;林邑浦乃淮水入海之口(大浦、彭龍灣、象浦),由林邑浦可進入東湖、船官口,進至林邑都城下。朱吾浦是無勞究水入海之口,浦內有無勞湖,與壽泠浦相通。胥浦為胥水入海口,九真浦為九真水入海之口;胥浦與九真浦之間有馬援所開之鑿口,可以通聯。凡此,都是從海上進入河流的通道;關于上述諸浦的觀察與描述,是從海上乘船進入河流進行的,故側重于港灣、河口湖泊、入湖河流等,較詳細地描述出河口海岸的地貌特征。
唐代賈耽《皇華四達記》所記 “登州海行入高麗渤海道”,也是從 “海行” 的角度記錄的。其文曰:
登州東北海行,過大謝島、龜歆島、末島、烏湖島三百里。北渡烏湖海,至馬石山東之都里鎮二百里。東傍海壖,過青泥浦、桃花浦、杏花浦、石人汪、橐駝灣、烏骨江八百里。乃南傍海壖,過烏牧島、貝江口、椒島,得新羅西北之長口鎮。又過秦王石橋、麻田島、古寺島、得物島,千里至鴨淥江唐恩浦口。
大謝島、龜歆島、末島、烏湖島,均在登州北,今渤海海峽;都里鎮,在馬石山(今鐵山)東,當即今旅順港。海壖,即海岸。自都里鎮傍海岸東北行,即沿今遼東半島東岸東北行,到烏骨江。青泥浦、桃花浦、杏花浦及貝江口、長口、鴨淥江唐恩浦口,也都是河流入海口(海浦);對這些浦、口的記述,也是從航海角度進行的。
三、居城望海
《元和郡縣圖志》卷 11“河南道,萊州” 又說大海在即墨縣東 43 里,“大勞山、小勞山在縣東南三十八里”,則即墨縣東南沿海有大、小勞山,是山地海岸。密州(治諸城縣)東至大海 160 里(或 150 里),諸城縣東南 130 里濱海 “有鹵澤九所,煮鹽,今古多收其利” 。瑯邪山則在縣東南 140 里,臨海,山上有瑯邪臺。據此,諸城縣東南沿海瑯邪山一帶是山地海岸,突出于海中;其北則有一個海灣,沿海有鹵澤,當是平原海岸。顯然,觀察者非常關注海岸的具體形態,以及海岸地帶的資源。
有關州(郡)縣治所與海岸間距離的記錄,反映出海岸位置的變化。垂拱四年(688)由蒲臺縣北境分置的渤海縣治所本來東距大海 110 里,而到天寶五年(746),“以土地咸鹵,自縣西移四十里,就李邱村置。大海,在縣東一百六十里”,即新縣治東距大海 160 里。換言之,自垂拱四年至天寶五年的 58 年間(688—746),蒲臺、渤海二縣境內的海岸向東推進了 10 里左右。當時黃河主泓正在二縣境內入海,這個淤積速度可以看作為黃河三角洲頂端的沉積速度。《元和郡縣圖志》卷 18 “河北道滄州” 記滄州(治清池縣)東距大海 180 里,《太平寰宇記》卷 65 “河北道滄州” 記滄州東北至海口 250 里。那么,在一百六七十年(約 813—979)的時間里,滄州境內的海岸向東推移了大約 70 里。
海岸向前推進之后,濱海地貌必然發生相應變化。《元和郡縣圖志》卷 17“河北道,棣州” 記大海在蒲臺縣東 140 里,黃河在縣東北 75 里,傳聞秦始皇筑以望海的蒲臺在縣北 30 里,“海畔有一沙阜,高一丈,周回二里,俗人呼為關口淀,是濟水入海之處,海潮與濟相觸,故名。今淀上有甘井可食,海潮雖大,淀終不沒,百姓于此下煮鹽”。關口淀應當是在濟水入海處,河流挾帶的泥沙受到海潮頂托而堆積形成的一道沙壩。《元和郡縣圖志》卷 18“河北道,滄州” 謂清池縣在浮水之陽,東有仵清池,縣因池而得名。《太平寰宇記》卷 65“河北道,滄州” 謂仵清河在清池縣東南 19 里,“其水澄味咸,未嘗枯涸。《輿地志》云:‘浮陽城南有大連淀,魏延興二年水溢注,破仵清村,因以為池。池內時有鯔魚,言與海潛通’”。大連淀本當是澙湖,延興二年(472)溢注,當是海水內浸,導致澙湖擴大。
較晚形成的海岸受海潮頂托,堆積成沙堤,地勢較高,舊海岸地帶被隔在沙堤內,地勢低洼,形成更多的湖澤。《太平寰宇記》卷 65“河北道,滄州” 謂大象二年(580)所置之長蘆縣在參戶故城,后移置于永濟渠西。開元十四年(726),“大雨,城邑漂沈,十六年移于永濟渠東一里”。《元和郡縣圖志》卷 18“河北道,滄州” 與《太平寰宇記》卷 65“河北道,滄州” 均記長蘆縣北 15 里有薩摩陂,“周回五十里,有蒲魚之利”。可知長蘆一帶地勢低洼,湖澤廣布。《元和郡縣圖志》卷 18“河北道,滄州” 記魯城縣東距大海 90 里,郭內有平魯渠。平魯渠當即平虜渠。《太平寰宇記》卷 65“河北道,滄州” 又謂平虜渠在縣南 200 步,“魏建安中于此穿平虜渠,以通軍漕,北伐匈奴,又筑城在渠之左”,大海在縣東 14 里。“乾符元年,縣東北有野稻、水谷,連接二千余頃,東西七十里,南北五十里,北至燕,南及魏,悉來掃拾,俗稱圣米,甚救濟民。” 據此,唐時魯城縣東 10 余里當即為湖澤,湖澤東西寬 70 余里,其東才是海岸。
《元和郡縣圖志》卷 18“河北道,滄州” 記鹽山縣東南 80 里有鹽山。《太平寰宇記》卷 65“河北道,滄州” 記鹽山縣東南 40 里有篋山(峽山),東南 90 里有闊山,并引《郡國縣道記》曰:“此山及鹽山二山并低小,無峰巒樹木”,大海在縣東北 120 里,而縣東 70 里有咸土,“東西南北一百五十里。地帶濱海,其土咸鹵,海潮朝夕所及,百姓取而煎之為鹽”。可知無鹽縣境東南地勢略高,東北當略低,“海潮朝夕所及”,很容易形成海水倒灌。《元和郡縣圖志》卷 18“河北道,滄州” 記無棣縣南臨無棣溝。《太平寰宇記》卷 65“河北道,滄州” 謂無棣溝東流,經無棣縣理南(在縣西南 300 步),又東流與鬲津枯溝合而入海。“隋末,其溝廢。唐永徽元年,薛大淵為刺史,奏開之,引魚鹽之利于海,百姓歌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達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跨駟,美哉薛公德滂被’”。無棣溝下游亦當受海潮頂托而致淤淺堵塞,須開新河方得通舟楫之利。無棣縣東界有月明沽,“西接馬谷山,東濱海,煮鹽之所”,應當也是潮汐所及的咸鹵之地。后周顯德六年(959)置立的乾寧軍永安縣(后改為乾寧縣)在永濟渠下游。《太平寰宇記》卷 68“河北道,乾寧軍” 謂御河(永濟渠)在乾寧軍城南 10 步,河南 70 步則有盧臺軍古城。御河從滄州南界流入乾寧軍界,東北 190 里入潮河,合流向東 70 里,于獨流口入海。“每日潮水兩至” 乾寧軍城。乾寧軍 “潮水所浸,惟生蒲葦”。海潮溯河而上 200 余里,到達乾寧軍城,正說明乾寧軍所在永濟渠下游兩岸地勢低洼,也容易形成海水倒灌。
實際上,自漢代以來,人們即已認識到海水漫溢及海潮沖刷侵蝕海岸所造成的破壞。為防止海潮侵刷海岸或漫溢,從東漢中后期開始,主要由郡(州)縣官府或地方豪強的主持,在部分海岸段筑起堤防。《水經注・漸江水》記浙江水經過錢唐縣,引《錢唐記》曰:“防海大塘在縣東一里許,郡議曹華信家議立此塘,以防海水。始開募,有能致一斛土石者,即與錢一千。旬月之間,來者云集,塘未成而不復取。于是載土石者皆棄而去,塘以之成,故改名錢塘焉”。按:錢唐縣廢于兩漢之際,復置于漢順帝永和六年(141)至漢桓帝延熹年間(158—167)。《世說新語・雅量篇》注引《錢唐縣記》曰:“縣近海,為潮漂沒,縣諸豪姓,斂錢雇人,輦土為塘,因以為名也”。華信等錢唐縣豪姓主持興筑防海塘,當在錢唐復縣之后。錢唐復縣后,新縣治位于明圣湖之北(“縣南江側有明圣湖”)。海塘在縣東(南)1 里,顯然是為了保護縣治。在此之前,漢順帝永和五年(140),會稽太守馬臻主持修筑會稽、山陰二縣境內的鏡湖塘堤,或即有部分堤段瀕臨海岸。在此之后,孫吳時楊哀明在山陰東北境白鹿山北的潟湖邊 “開瀆作埭”,亦或屬于海塘性質。
《北齊書》卷 24《杜弼傳》記北齊天保間(551—559),杜弼被徙為臨海鎮將,復行海州事,“于州東帶海而起長堰,外遏咸潮,內引淡水”。東魏海州治在朐山戍以南的龍沮戍,海州之東帶海處,當 即龍沮戍至朐山戍之間的濱海地帶。《新唐書》卷 38《地理志》海州 “朐山” 縣原注云:“東二十里有永 安堤,北接山,環城長十里,以捍海潮。開元十四年,刺史杜令昭筑。”《太平寰宇記》卷 22“河南 道,海州” 述其事稍詳,謂:“唐開元十四年七月三日海潮暴漲,百姓漂溺,刺史杜令昭課筑此堤,北接 山,南環郭,連綿六七里”。永安堤北接山(當即朐山),南環海州城郭,應當位于朐山東南濱海 處,與杜弼所修海州長堰并不相連接。《太平寰宇記》卷 22“河南道,海州” 記東海縣有東西兩道捍海堰:西捍海堰在縣城北 3 里,“南接謝祿山,北至石城山,南北長六十三里,高五尺”,隋開皇九年(589)縣令張孝征主持修筑;東捍海堰,在縣東北 3 里,“西南接蒼梧山,東北至巨平山,長三十九里。隋開皇十五年,縣令元曖造,外足以捍海潮,內足以貯山水,大獲澆溉”。隋、唐、北宋的東海縣位于郁洲島 上。這兩道捍海堰保護郁洲島西部與北部地勢較低的濱海地帶,使之發展成為良疇美田。
《舊唐書》卷 115《李承傳》謂大歷中,李承 “為淮南西道黜陟使,奏于楚州置常豐堰以御海潮,屯田瘠鹵,歲收十倍,至今受其利”。《新唐書》卷 41《地理志》楚州山陽縣原注:“有常豐堰,大歷中, 黜陟使李承置以溉田。” 常豐堰大致相當于后世范公堤的北段,它以灌溉為主要功能,兼及捍御 海潮,位置比潮位線略高。常豐堰筑成后,射陽湖被隔在堰內,成為內湖,并逐步縮小。《太平寰宇記》卷 124“淮南道,楚州” 說射陽湖在山陽、鹽城、寶應三縣交界地帶,在山陽縣東南 80 里、寶應縣東 60 里、鹽城縣西北 120 里,“大歷三年,與洪澤并置官屯”。同時,漢代以來的產鹽區則被隔在堰外。《太平寰宇記》卷 124“淮南道,楚州” 記鹽城監所管鹽場 9 所,在鹽城縣南 50 里至北 30 里,“俱臨 海岸”。這樣,常豐堰(特別是后世的范公堤)遂將農耕區與鹽產區分隔開來:堰內為農耕區,堰 外為鹽產區。
如上所述,杭州灣北側海岸一直受到潮濤沖刷,形成塌岸。《新唐書・地理志》杭州鹽官縣原注:“有捍海塘堤,長百二十四里,開元元年重筑。” 鹽官捍海塘于開元元年(713)重筑,則其始筑必 在此前。南宋嘉定十五年(1222),鹽官縣海塘沖決。浙西提舉水利劉垕報告說:鹽官縣城本來距海岸有 40 余里,“數年以來,水失故道,早晚兩潮,奔沖向北,遂致縣南四十余里盡淪為海。近縣之南,元有捍海古塘亙二十里。今東西兩段,并已淪毀,侵入縣兩旁又各三四里,止存中間古塘十余里”。其所說之 “古塘” 當即唐代所修鹽官捍海塘,其地當在鹽官縣城東南 40 余里。捍海塘筑成后,在一段 時間內穩定了杭州灣北側海岸。《新唐書・地理志》福州閩縣原注:“東五里有海堤,大和二年令李茸筑。先是,每六月潮水咸鹵,禾苗多死,堤成,潴溪水殖稻,其地三百戶皆良田。” 長樂縣原注:“東十里有海堤,大和七年令李茸筑,立十斗門以御潮,旱則潴水,雨則泄水,遂成良田。” 則李茸在大和間先后任閩縣、長樂縣令,主持修筑海堤,堤上各立有斗門。斗門之作用,當是在滿潮時閉,以御潮水;潮退時啟,以泄河湖之水。
總之,由治城看海岸治所,觀察者首先關注海岸的位置,特別是其與州縣治所間的距離、相對方位;其次關注海岸地帶的地理面貌及其變化,特別是海岸因淤積向前延伸或者受到海潮沖刷而退縮,其所認識的海岸地帶,一般是所屬州(郡)縣的偏遠地帶,故謂之為 “海隅之地”。從對海岸及其變化的觀察、認識出發,人們注意濱海地帶的資源及其利用,為防止海水漫溢、維護受沖刷侵蝕的海岸,在部分海岸段建筑堤岸,從而形成人工海岸。
四、人們對海岸形態的分類與認識海岸的意義
《爾雅・釋丘》釋岸,謂 “望厓灑而高”。郭璞注:“厓,水邊;灑,謂湥也。視厓峻而水湥者曰岸。” 郝懿行疏云:“此釋厓岸之名也。《說文》云:岸,水厓而高者。又云:厓,山邊也。是山邊亦名厓。此則指水邊而言也。” 按照這里的解釋,岸看上去很高峻,其下水勢激蕩。《說文》釋厓,謂 “山邊也。從廠,圭聲”。廠,謂:“山石之厓巖,人可凥。象形,凡廠之屬,皆從廠”。段注:“厓,山邊也。巖者,厓也。人可居者,謂其下可居也。屋其上則謂之廣。” 岸則從屵。《說文》釋屵,謂:“岸高也。從山、廠。廠,亦聲。凡屵之屬,皆從屵”。段注:“屵之言 然也。《廣韻》:高山狀。” 崖亦從屵,“高邊也”。那么,厓岸或崖岸都是指水邊由山巖構成的岸,亦即巖岸。
《爾雅・釋丘》釋漘,謂 “夷上灑下,(不)漘”。郭璞注:“厓上平坦而下水湥者,為漘。不,發聲。”《說文》:“漘,水厓也。” 段注:“《魏風傳》:漘,厓也。《爾雅》曰:厓夷上灑下,漘。按:夷上,謂上平也。灑下,謂側水邊者斗峭。” 那么,漘是一種上面平坦而下臨湍流的岸。班固《東都賦》說天子 “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稜。西蕩河源,東澹海漘,北動幽崖,南曜朱垠”。呂向注云:“海漘,海畔也。崖、垠,皆畔岸也。” 海漘,應當是較為平坦的海岸。《爾雅・釋丘》又謂:“岸上,滸。” 郭璞注:“岸上地。”《爾雅・釋水》中則謂:“滸,水厓。” 郭璞注:“水邊地。” 兩相結合,可知滸當是水邊平坦的土地,亦即表現為緩坡的岸。《爾雅・釋丘》又見有 “重厓,岸”。郭璞注:“兩厓累者為岸。” 洪頤煊謂:“岸上見岸,即是重厓。” 岸有多重,當是表現為多層緩坡疊累的岸。
《爾雅・釋丘》謂:“墳,大防。” 郭璞釋 “防” 為 “隄”。大防,當即高大的隄岸。防、隄皆從 。《說文》釋 “ ”,謂:“大陸也。山無石者,象形。凡之屬皆從 。” 所以,隄、防當是以土構成的人工護岸設施。
《爾雅・釋丘》釋 “隩隈”,謂:“厓內為隩,外為隈”。郭璞注:“別厓表里之名。” 據此,厓(岸)的兩邊,分別稱為隩(內)、隈(外)。隩、隈亦皆從 。
魯西奇,復旦大學歷史學系,202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