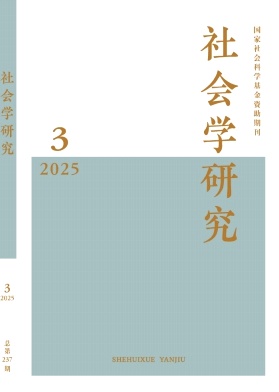社會學研究雜志投稿格式參考范文:財政社會學的起源、發展與啟示
時間:
一、問題的提出:財政社會學是什么?
被稱為 “財政社會學之父” 的魯道夫・葛德雪(Rudolf Goldscheid)不僅創造了 “財政社會學” 這一名稱,還系統地闡述了財政社會學的學科屬性和研究對象。在《財政問題的社會學研究路徑》一文中,他鮮明地指出,財政社會學是一門用社會學方法分析歷史和現實經驗中的財政問題的學科。他認為社會學方法就是從 “社會事實”①出發,用 “貼近調查事物為什么是這個樣子” 的 “社會學方法” 去直面事物的原因和后果(葛德雪,2015)。除了強調基于社會事實的研究方法外,葛德雪還特別注重從 “社會結構” 的角度來分析財政收支之間的關系。在他看來,財政社會學的關注重點不在于稅收的種類和數量,而是它們的運用。他強調要從 “社會結構” 的角度告訴人們國家 “怎樣以及從何處獲得財政收入”,“從社會中哪個階級身上取得稅收”,這些收入 “花在哪里”,哪些人受益,“需要多大及什么樣的公共管理工具”(葛德雪,2015:262)。他認為,透過財政收支,我們不僅能看到社會,還能窺見國家的性質以及國家與社會的關系(Goldscheid,1925,2018)。財政絕不僅僅是一堆經濟數據,更是一個關于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綜合性問題,因此需要使用社會學的整體主義方法來研究。
① 譯者將其翻譯為 “社會實在”。本文依據涂爾干的《社會學方法的準則》和國內社會學界通用的翻譯,改用 “社會事實” 這一譯法。
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對葛德雪的財政社會學極為贊賞,稱 “葛德雪的不朽貢獻在于,他是恰當地強調運用社會學方法分析財政史的第一人”(熊彼特,2018:181)。正如熊彼特所言,“所謂的社會學方法,就是收集堅實、未經修飾的事實,將其置于社會學領域中”。而 “財政是社會調查的最好起點之一,尤其是在調查并不排斥它所包含的政治生活時更是如此。在用于研究社會轉折點或新階段之時,從財政入手的研究方法效果更為顯著”(熊彼特,2018:181-182)。熊彼特認為財政社會學 “特別有吸引力的地方在于,它可以讓我們從財政角度來考察國家,探究它的性質、形式以及命運”(熊彼特,2018:183)。他運用財政社會學方法對稅收國家進行研究,指出自由經濟塑造了稅收國家并決定了稅收國家的命運。
弗里茨・卡爾・曼(Fritz Karl Mann)從方法論意義上肯定了財政社會學,認為財政社會學是研究 “財政對社會的影響” 和 “社會對財政的影響” 的最佳路徑,它能成功地探討國家、財政系統與社會秩序之間的關系(Mann,1943,1947)。此后,財政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對象被許多學者沿用,財政社會學被認為是 “社會學的一個分支”(Ducros,1982),主要研究稅收和公共支出如何對政治、經濟、文化、制度和歷史等產生影響,反過來又如何被這些力量所形塑(Campbell,1993;Martin et al.,2009;馬丁等,2023a),重點關注財政事實、國家和社會之間的關系(Leroy,2017:833-837)。
然而,在財政社會學的傳播和發展中,“財政社會學” 這一術語被不同研究者使用,尤其經常被那些不擅長社會學的研究者挪用(井手英策,2022:3)。《財政社會學和財政學理論》①的作者理查德・E. 瓦格納(Richard E. Wagner)便是其中人物之一。瓦格納的 “財政社會學” 其實與葛德雪所倡導的財政社會學毫無關系,他的 “財政社會學” 中的 “社會” 指市場社會,即一個交易的場所,由國家與市場這兩個結構組成。在瓦格納這里,國家不是一個外在干預的實體組織,而是和市場一樣,是在社會互動中自然生成的 “秩序”。由于經濟和政治被同時置于社會的交易之中,財政行動就像市場的其他行動一樣,也是交易性行為,財政現象在交易過程中生成。正如瓦格納所說,“就這里所追尋的社會理論取向的財政學來說,國家不是一個干預主體,而是一個人們進行互動的舞臺或過程,這些人追求著各自的目標,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受到構成那些關系的各種制度的支配。因此,財政現象是生成性的”(Wagner,2007:180)。
① 該書已由劉志廣翻譯,但尚未出版。本文的引用參考了其譯本。
顯然,瓦格納 “社會取向” 中的 “社會” 與社會學所理解的 “社會” 全然不同。社會學所指的 “社會” 并非一個交易場所,而是一個 “把個體連接在一起的具有內在相互關系的系統”;在這個系統中,個體是在 “共同文化造就的結構化的社會關系中被組織起來的”,個體的選擇不是孤立的,而是被其所在的文化和制度環境塑造(吉登斯,2003:20)。確切地說,社會學所說的 “社會” 不是一個由理性人或經濟人基于個人利益而形成的集合,而是由共同的價值觀念和社會規范凝聚在一起的系統(費孝通,1996:202;迪爾凱姆,2009)。總之,瓦格納的財政社會學其實是制度經濟學,與社會學關系不大。
然而,瓦格納對 “財政社會學” 這一術語的挪用一定程度上誤導了財政社會學在我國的傳播和發展。國內最早使用和傳播 “財政社會學” 一詞的是瓦格納著作的譯者劉志廣。受瓦格納的影響,他認為葛德雪和熊彼特所說的財政社會學是 “社會科學” 意義上的而非 “社會學” 意義上的,并將財政社會學視為 “經濟社會學的一個分支”(劉志廣,2012:52)。劉志廣(2012)的《新財政社會學研究:財政制度、分工與經濟發展》一書就是從 “經濟人” 假設出發,運用個體主義的分析方法和財政收入最大化、議價能力、分工、市場、交易費用等理論或概念分析財政制度和經濟發展問題。無論從研究方法還是研究對象來看,這本書都不能被歸入財政社會學,而應該被視作以理性選擇為理論和方法的制度經濟學專著。
除經濟學者對財政社會學這一術語的挪用外,國內一些財政史學者將 “財政社會學” 誤用成 “財政政治學”(劉守剛,2015;李煒光、任曉蘭,2013;史錦華,2016)。例如,劉守剛(2015,2022)將其組織翻譯的一系列財政社會學論著命名為 “基于財政政治學的文本選擇” 或 “財政政治學視界論叢”。他認為 “財政社會學” 就是 “財政政治學”,正如他在叢書的卷首語中所說,“在《財政政治的視界》系列圖書選譯(編)的論文中,大家會看到有很多學者在研究中使用的是‘財政社會學’而非‘財政政治學’,但這并非是我們‘移花接木’或‘張冠李戴’,而是從創立者的意圖和所使用的方法來說,二者在很多場合下可以作為同義詞來使用”(劉守剛、劉志廣主編,2022:1)。
從《主編后記》中我們得知,他們之所以將財政社會學等同于財政政治學,主要原因在于財政社會學 “以國家為中心” 這一研究主題。他們認為,傳統財政學的研究重心是 “國家”,但 “遺憾的是,在中國目前的財政學研究中,恰恰丟掉了國家”,“因此,與政治學界曾經呼吁‘找回國家’相應,‘財政政治學’的發展實際上就是在財政學領域‘找回國家’的智識努力”(劉守剛、劉志廣主編,2022:432)。
因為財政社會學的研究主題中包含 “國家”,就將財政社會學草率地等同為財政政治學,是對財政社會學的嚴重誤用。財政社會學的獨特之處不在于研究議題,而在于研究方法。正如兩位創始人所說,財政社會學是從 “社會事實” 出發,用 “社會調查的方法” 來研究財政。事實上,財政社會學不僅關注 “國家”,也關注 “社會”,更關注財政、國家和社會之間的關系。
由于財政社會學被不擅長社會學的研究者挪用和誤用,國內學者在傳播和討論財政社會學時常常出現學科不清、方向不明和研究對象不清等問題。本文認為,有必要對財政社會學 “正本清源”,闡明財政社會學的學科定位、研究方法、研究對象和研究主題。與此同時,對財政社會學的梳理也旨在呈現財政社會學所帶來的啟示,回應我國財政研究的 “經濟化” 問題(即只將財政作為一個經濟問題來研究),滿足國家提出的 “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 之理論需求。
二、基于社會學的財政社會學
葛德雪并非在 “社會科學” 這樣模糊的學科范疇上來建立財政社會學,而是在 “社會學” 這一清晰的學科領域內闡明了財政社會學的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事實上,葛德雪不僅跟隨著名的經濟學家阿道夫・瓦格納(Adolph Wagner)學習過財政學,而且系統學習過社會學,著名社會學家齊美爾便是他的導師之一。不僅如此,他以創始人的身份于 1907 年組織并參加了維也納社會學會,并同齊美爾、韋伯等人于 1909 年創建了德國社會學會,是當時德國極為活躍的學者、學術活動組織者和馬克思主義者(Peukert,2009;Bammé,2018)。
葛德雪關于財政社會學的基本理念發表于 1917 年出版的《國家社會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一書中。作為系統學習過社會學專業并關注財政問題的學者,葛德雪用涂爾干的 “社會事實” 來明確財政社會學的研究路徑。在他看來,財政問題研究的嚴重缺陷在于缺乏社會學基礎。“只有社會學才能說明,社會條件是怎樣決定公共需要的,怎樣決定滿足公共需要的方式的(以更直接或更間接的手段),以及社會模式與演進進程是怎樣最終決定性地塑造公共支出與公共收入之間的內在聯系的”(葛德雪,2015:262)。正是由于將財政問題置于國家和社會現實中,葛德雪才著重強調財政社會學的重要性。他認為,歷史學、社會學和統計學是財政學的三根支柱,三者結合才能讓財政理論不至于完全脫離現實。換言之,財政社會學誕生于葛德雪的跨學科視野中,而葛德雪之所以將其命名為 “財政社會學”,是因為社會學的方法是財政研究中 “最為重要” 的 “基本支柱”(葛德雪,2015)。“單獨運用它,就可以揭示財政收入的源泉及其構成在社會整體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財政收入對民族命運和個人命運的影響”(葛德雪,2015:267)。
正是基于社會學的視野,葛德雪為財政社會學奠定了以下基礎。首先,確定了財政社會學的學科屬性,即財政社會學是以社會學為基礎的交叉性學科;其次,明確了財政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即財政社會學是用社會學的整體主義方法,研究財政和國家、社會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最后,提出了一系列頗具啟發性且富有深遠意義的財政社會學議題,包括社會條件與公共需要的關系,財政與國家起源、性質、能力和國家發展的關系,財政與社會結構、社會沖突、社會變遷、社會制度的關系(他重點提了民主憲政制度),財政與公共管理的關系,以及財政與公共資源、私人資本之間的關系,等等。
然而,在財政社會學此后的發展中,葛德雪的洞見及其所開創的議題并未受到應有的關注和重視。由于語言的限制,葛德雪的大部分作品在英語世界中流傳極少,而移居美國的熊彼特則以其在哲學、經濟學和政治學方面的思想觀點,在多個學科領域擁有崇高的學術威望和諸多追隨者。被視為當代財政學奠基人的理查德・A. 馬斯格雷夫(Richard A. Musgrave)是熊彼特的學生之一,他將熊彼特的《稅收國家的危機》稱為 “一篇財政社會學論文”,進行了專門的介紹和討論,從而使 “財政社會學” 傳播甚廣,以致于后來的諸多研究者都在 “致敬熊彼特”(Musgrave,1980)。他們對財政社會學的解讀和構建幾乎都以熊彼特的稅收國家理論為起點,并將熊彼特視作財政社會學的創始人。
雖然馬斯格雷夫對熊彼特財政思想的介紹主要集中于 “稅收國家” 理論而非 “財政社會學”,但他十分明確地強調 “熊彼特對稅收國家的看法是他的社會學而不是經濟學的產物”(Musgrave,1992)。熊彼特不僅用社會學方法研究了稅收國家的危機,而且用社會學方法分析了帝國主義(1919 年)和階級社會(1927 年)(Schumpeter,1966)。正如馬斯格雷夫所言,熊彼特的社會學研究不應該僅被視為他的一種業余愛好,因為他具有像馬克思一樣的研究氣魄和視野(Musgrave,1992)。
在財政社會學的復興和發展過程中,雖然學者們認為財政社會學研究處于 “襁褓期”,研究存在 “碎片化”“邊緣化” 和 “包羅萬象” 等問題(Campbell,1993;Mclure,2009;Backhaus,2002;Martin et al.,2009;Martin & Prasad,2014),但相關研究普遍運用了社會學方法來研究財政、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相互關系。正如坎貝爾(John L. Campbell)所說,“不同于其他方法,財政社會學直接關注復雜的社會互動、制度環境和歷史情境,國家和社會在這樣的環境和情境中發生關聯,其關聯方式對財政政策及其效果產生影響”(Campbell,1993:164)。艾薩克・威廉・馬丁(Isaac William Martin)等人主編的《新財政社會學》進一步明晰了財政社會學的學科性質和研究主題。雖然他們在闡述 “新財政社會學” 的起源和發展時將其界定為一個跨學科的領域,認為 “新財政社會學” 不專屬于社會學系,其知識貢獻來自多個學科,但他著重強調了新財政社會學對社會學方法的繼承。
他們在解釋為何取名 “新財政社會學” 時說,“我們選用‘財政社會學’這一名稱,是為了向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致敬”(馬丁等,2023a,2023b:2)。顯然,馬丁等人認為財政社會學的發展源于熊彼特,而非葛德雪。事實上,“新財政社會學” 不僅繼承了葛德雪所提倡的跨學科和社會學的研究方法,還討論了他所提出的那些富有洞見的研究議題。只是,相對于強調財政支出的葛德雪而言,“新財政社會學” 更關注稅收及與稅收相關的政治或社會問題,如稅收遵從、社會不平等、家庭、性別、種族、全球化等(Campbell,2005;利伯曼,2023;Martin,2008,2015;麥克卡費里,2023;O'Brien,2017;Leroy,2017;Pacewicz & Robinson III,2021)。事實上,自 1990 年以來,稅收幾乎成為財政社會學的唯一主題,因此有人直接用 “稅收社會學” 來指稱財政社會學(Leroy,2008)。這就是 “新財政社會學” 之所以 “新” 的地方。
三、財政危機:財政社會學興起的主題
葛德雪和熊彼特倡導建立財政社會學時,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戰爭加劇了原本沉重的國家債務,歐洲各國均面臨嚴重的財政危機。財政危機不僅構成財政社會學產生的背景,還成為財政社會學研究經久不衰的主題。
(一)葛德雪:“國中之國” 與財政危機
在回答 “稅收國家的危機是如何產生的” 以及 “如何化解危機” 時,兩位創始人的答案截然不同。葛德雪認為財政危機的主要原因是國家擁有越來越多的 “負資本”,這使得作為公共債權人的資本家有機會剝削國家,而國家從勞動階級身上獲取的稅收主要服務于這些公共債權人。他認為,財政危機是現代國家特有的問題。古代社會之所以不會發生財政危機,是因為國家不僅有充足的財產,而且時常擁有巨額財產。然而,“在憲政政府時代,國家和財產分離了。在憲政政府成長時,在大規模私人企業可從不受限制的經濟中獲取權力時,企業家們就嫉妒性地嘗試阻止國家在經濟領域內與自己競爭”,導致 “今天的稅收國家卻沒有財產,并且事實上總是深陷于債務之中”(葛德雪,2015:263-266)。
在葛德雪看來,正是由于與國家相分離的財產落入私人資本家和金融寡頭集團手中,國家成為私人資本和強大利益集團的玩物,進而形成 “國中之國”,導致發生財政危機。他指出,化解危機的首要任務是處理 “國中之國” 的問題,同時建設和鞏固 “人民的財政學”。不然,財政學仍然停留在與社會的真正需求相脫節的狀態中。至于 “國中之國” 這一問題如何解決,葛德雪給出的方案是 “把財產還給國家”。而將財產還給國家的具體方案便是國家資本主義,即建立國家公營企業。這樣一來,國家的財政需求將不再依賴于資本家,而是取決于國家公共資本所創造的剩余價值。他堅信,“只有富裕國家,才會是一個正義國家”(葛德雪,2015:271)。但葛德雪的資本重組計劃只是接管大型企業三分之一的股權,不針對中小企業;另外,他十分看重企業家精神,認為國家公營企業應當交給職業經理人來管理,而不是由國家機關管理(Goldscheid,1917)。
(二)熊彼特:自由經濟與 “稅收國家的危機”
熊彼特的稅收國家是相對于工業革命之前歐洲封建領主經濟及其封建社會結構而言的。他認為,國家是 “封建領主和資產階級之間沖突和妥協的產物”(熊彼特,1999:260),“‘稅收’與‘國家’的關系至深,以至于‘稅收國家’這樣的表達形式幾乎可以被看作贅語”(熊彼特,2018:192)。但他并非只是簡單地從 “財政收入的形式” 進行分析,而是從經濟制度及與其相關的 “私人領域”(社會)與 “公共領域”(國家)之間的關系來論述稅收國家的本質。他認為歐洲傳統封建國家以 “領主經濟” 為基礎,而領主經濟由于不存在以個體自由為基礎的私人經濟,所以領主國家的財政是一種不具有公共性的家財式財政。稅收國家的經濟制度以自由經濟或私人經營為基礎,其財政收入來自私人經營的稅收所得,所以稅收創造了一個以公共領域為活動范圍的國家,因而具有公共性。熊彼特認為,傳統社會主義國家 “不是私人占有和經營企業,而是由國家當局控制生產資料”(熊彼特,1999:25),因此不是稅收國家。
在熊彼特看來,只要私人企業和自由經濟仍然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稅收國家就不會崩潰。但當資本主義完成了其歷史使命,社會的發展就會超越稅收國家,進入社會主義。事實上,他提出的 “稅收國家一定會崩潰嗎” 這一問題,與他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一書中所問的 “資本主義能存在下去嗎” 意涵相同。這更直接地表明,他所關心的問題其實就是:資本主義經濟秩序必定崩潰嗎?會不會被社會主義替代?對于這兩個問題,他給出的答案也是類似的,即認為資本主義最終會過渡到社會主義,但這種過渡不是因為資本主義本身的經濟問題,即自由經濟的失敗,而是不斷 “革新生產技術” 和 “創造性的破壞” 的 “進化” 帶來的結果,是 “成熟狀態下的社會主義化”,而非 “不成熟狀態下” 的革命帶來的結果。他認為,“在資本主義體系內的逐步社會主義化,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最明顯可以期望的事情”(熊彼特,1999:339)。
因此,熊彼特反對葛德雪所主張的 “把財產還給國家” 的做法,而是相信自由經濟和私人企業能應對稅收國家的危機。他認為,只要推動社會發展的仍然是以個人利益為動力的自由競爭經濟,稅收國家便不會崩潰。反之,如果自由經濟本身失敗了,那么稅收國家就可能失敗。正如他所說,“如果稅收國家能夠拯救自己,但經濟卻在這一過程中趨于毀滅或注定陷入悲慘境地,那么所做的一切都是無用功”(熊彼特,2018:207)。
(三)奧康納:國家職能與財政危機
繼葛德雪和熊彼特的財政社會學研究后,財政社會學一度陷入沉寂,①直到 1973 年美國學者詹姆斯・奧康納(James O'Connor)的《國家的財政危機》(The Fiscal Crisis of the State)問世后,財政社會學研究方才迎來復興。雖然該書出版后,學界評價褒貶不一,“但不管怎樣,他們全都表示欣賞筆者論述了一個財政社會學問題,而且約瑟夫・熊彼特在很早以前就曾表示,這是一個大有前途的研究方向。但在《國家的財政危機》問世以前,這個‘大有前途的研究方向’一直是社會理論和社會科學研究最欠缺的領域之一”(奧康納,2017:序言:14)。
① 只有曼在 1947 年發表了《革命中的財政因素:基于財政社會學的分析》一文(Mann,1947)。
奧康納認為財政危機主要源于兩個相互矛盾的國家職能,即資本積累職能和政治合法化職能。這兩項職能分別對應社會資本支出和社會費用支出。由于國家的社會資本支出所產生的利潤被私人壟斷資本占有,國家資本成本社會化和利潤的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不斷凸顯,進而導致國家財政支出和收入之間產生 “結構性缺口”,即財政赤字,最終引發財政危機。奧康納認為,財政赤字只是國家財政危機的表現,財政危機的根源是資本主義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具體表現在壟斷部門和國家部門之間的關系之中。在他看來,私人資本為了增加和鞏固其利潤,不僅剝奪了國家的直接生產性資本(即國有企業賺錢的營生),而且通過借貸(向國家提供貸款形成的公債)擴張和壯大了自己的力量,同時造就了一個 “食利金階層” 和 “金融貴族”。最后,國家在經濟與政治層面都成為私人資本的附庸,同時有求于銀行家、投資人和其他貨幣經紀人階級(奧康納,2017:177-178)。
奧康納指出,財政危機的實質是一種社會危機,其不僅使經濟和政治上對立的勞資雙方劍拔弩張,還分化了勞動階級。根本而言,這一危機是由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導致的,解決這種危機的 “唯一永久性方法就是社會主義”,暫時的方法是發展 “社會 — 工業綜合體”,即通過提高壟斷部門和國家部門的生產率來緩解財政危機(奧康納,2017:210)。
顯然,奧康納繼承了葛德雪的馬克思主義分析方法,從社會階級的角度剖析了國家財政危機的根源和解決之道。雖然熊彼特的分析與他們不同,但熊彼特也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演化模型。基于此,財政學家馬斯格雷夫將三位學者的危機財政社會學稱為 “馬克思主義財政社會學”(Musgrave,1980)。
四、稅收秩序:財政社會學發展的主題
繼奧康納之后,奧地利傳統的財政社會學雖有零星的研究發表,卻再無系統性的研究文獻出現(Backhaus,2002,2005)。①馬丁主編的《新財政社會學》雖然是一本論文集,但它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自奧康納之后 “財政社會學的碎片化” 問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① 在此期間雖然有一些文獻討論了財政社會學的研究視角及相關議題,但大多數是對熊彼特觀點的總結和歸納,比如馬斯格雷夫 1980 年的《財政危機理論:一篇財政社會學論文》和 1992 年的《熊彼特的〈稅收國家的危機〉:一篇財政社會學論文》(Musgrave,1980,1992)。
(一)作為政治議題的減稅和抗稅
在 20 世紀 50、60 年代的美國,無論是政治精英還是普通公眾,都很少將稅收看作一個政治議題。直到政治精英在參與競選時,將對稅收的不滿當作籌碼與賣點,并展開頻繁的公共討論,稅收才真正地成為政治議題,公眾對稅收的態度也由此受到影響。政治精英對稅收的政治化又進一步強化了公眾與稅收之間的關聯,“人們在評價政黨時,不管是喜歡還是厭惡,都越來越多地與稅收相聯系”(坎貝爾,2023:80)。
弗雷德・布洛克(Fred Block)從意識形態的角度進一步討論了美國的減稅或者說 “永久抗稅” 問題是如何成為政治議題的(布洛克,2023)。在布洛克看來,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的政治精英接受了激進的經濟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認為,無論是 19 世紀的濟貧制度還是 21 世紀的福利制度,均會損害工人的勞動積極性,培養懶惰并因而降低生產效率;個人必須對自己的命運負責,參與到達爾文主義的自然法則的競爭中。與此相對立的宗教保守派則堅持認為,當現實過于沉重和無法好轉時,應該將重點放在來世的宗教上,通過個人救贖(如個人的善舉、責任和自律)來對自己的命運負責。此外,市場原教旨主義和宗教保守派聯盟主張減稅,反對家庭以外的社會責任,進而阻擋了各種社會和經濟變革,尤其阻擋了具有保護 “社會” 功能的福利政策的變革。布洛克認為,市場原教旨主義和宗教保守派否定 “社會” 的主張通過撒切爾夫人和里根的執政在社會范圍內得到了廣泛宣傳與貫徹,并被普通民眾所接受,從而造就了美國的永久抗稅運動。
(二)稅收遵從
與永久抗稅運動相反,也有很多國家的民眾具有較強的納稅意識。因此,“為什么人們會同意納稅” 便成為財政社會學討論的議題之一。傳統財政學很少關注這一問題。原因在于,傳統財政學以國家財政為理論基礎,認為國家是財政運行的主體,是公共利益和公共需求的代表。國家扮演著家長的角色,為實現社會福利的最大化進行合理的資源配置。但財政學轉為公共經濟學后,國家和民眾都被視為具有自身利益考量的理性人。那些代表國家的統治者及政治精英追求稅收收入的最大化,民眾則看緊自己的口袋,不愿自己創造的資源被統治者剝奪。那么,為什么理性的個人會同意國家征稅呢?馬丁等認為,這是因為國家有意設計了不容易被民眾感知的稅收政策。通過民眾的認識偏差和愚民政策宣傳,國家獲得了稅收遵從(馬丁等,2023b)。當詹姆斯・M. 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的公共選擇理論被引入財政學后,稅收被視為利益集團、政治精英、政黨和民眾之間博弈的對象。與此同時,一種以個體主義為基礎的稅約契約關系成為解釋納稅人同意的主要依據,并被用來回答為何納稅人會同意某一特定的均衡(布坎南、圖洛克,2017)。
新財政社會學則認為,納稅人同意 —— 包括政治層面的接受與法律層面的遵守 —— 取決于一種 “社會” 的而非 “個人” 的契約(馬丁等,2023b:26)。因為納稅人的計算不只是基于自利的考慮,還將受到整個社會的影響,從而考慮集體的善。例如,埃文・S. 利伯曼(Evan S. Lieberman)認為納稅遵從實質上是一種 “犧牲”(sacrifices),即把個人資源轉換成公共資源,稅收進而成為國家供給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務的公共資源。相對于征兵或其他為了公共的善而約束、改變私人行為的政策(如禁止吸毒、限制吸煙、限速駕駛等)所帶來的犧牲,納稅這類犧牲是最為持久的犧牲。利伯曼指出,在公共政策層面,基于成本和收益的計算是不成立的,因而不能用短期的、個人的、以消費為基礎的市場邏輯去理解這類為公共利益所做出的犧牲行為。由于與市場交換邏輯不同,“社會” 不僅存在合作與集體行動,而且存在 “作為一個共同體的成員要作出貢獻” 的道德規范,即 “共享的集體觀念”(利伯曼,2023:130)。這種共享觀念表現為身份邊界和群體認同的情感。如果納稅人相信他們的稅款是讓 “我們”,即由 “群體內部” 受益時,那么他們便有動力為共同體成員作出犧牲。他還以南非和巴西這兩個國家在應對艾滋病時所采取的不同稅收政策為例,說明了群體認同和納稅人同意之間的關系。
(三)稅收的社會影響
在呈現 “稅收的社會后果” 時,《新財政社會學》進一步探討了稅收對國家能力、民主化和社會不平等方面的影響。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在其《汲取與民主》(Extraction and Democracy)一書中分析了國家汲取財政的方式對民主化的影響。他以俄羅斯的政治轉型為例指出,戈爾巴喬夫的民主化不僅沒有實現國家能力,反而產生了搶占國家財富的經濟寡頭,由此衍生了大量的有組織犯罪、貪污以及社會不平等。蒂利指出,1999 年,普京執政后就通過國家資源的重新國有化使國家重新掌握了國家財富,從而有效地扭轉了國家能力弱化的趨勢,但由此而來的代價是 “民主” 被擠出了。在他看來,國家從民眾身上直接汲取財政資源的方式會開啟 “干預 - 抵抗 - 鎮壓 - 討價還價” 的制度循環,從而促進國家與民眾之間的協商,走向成熟的民主化之路。而那些資源型國家(如依靠石油等資源獲取財政收入的國家),或直接掌握國家資源的生產型國家,由于無需從民眾手中直接獲得稅收,無需獲取民眾的納稅同意,因而難以產生民主。蒂利認為,從長遠視角看,只有當統治者依賴公民的納稅遵從并將其作為統治手段時,民主化才會產生(Tilly,2009)。
總體而言,蒂利對于國家資源與國家能力關系的認識在很大程度上延續和印證了葛德雪和奧康納的論點,即只有掌握了資源的國家才具有國家能力。但他關于汲取方式與民主的論述卻不符合中國經驗,因為中國自古以來都是從民眾手中直接征稅的。換言之,從國家汲取財政的方式看,傳統中國一直屬于稅收國家,卻并未走向蒂利所言的西方式民主。其原因在于,傳統中國 “納稅遵從” 觀念的形成不同于西方 “權利、抗爭與妥協” 的邏輯,而是源自儒家 “家國一體” 的文化觀。
在討論稅收制度的社會基礎問題時,埃德加・凱瑟(Edgar Kiser)和奧黛麗・薩克斯(Audrey Sacks)以非洲為案例說明,在監控能力十分薄弱的條件下,非洲國家的稅收管理體制改革經常受到新公共管理理論和代理人理論的影響,致力于模仿發達國家的 “現代化” 管理體制,結果不但沒有提升國家能力,反而導致了腐敗和低效率。他們認為,不顧組織運行的制度環境所進行的 “過度模仿” 和 “復制” 往往是組織無效運行的根源(凱瑟、薩克斯,2023)。
五、財政社會學的啟示
從經濟、政治和社會之間的實踐關系(而非抽象的理論假設)出發,探討財政、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是財政社會學帶來的啟示。在這一啟示下,我們將嘗試重構公共物品理論,進而討論社會秩序與現代公共財政,以及財政與國家之間的關系,以回應我國財政研究的 “經濟化” 問題和 “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 之理論需求。
(一)社會:公共物品供給的主體
現代公共財政學的起點是市場失靈理論和公共物品理論。然而,國內外財政學者普遍認為,公共物品只有在純理論邏輯上才成立。“對于這一事實,經濟學不僅早已熟知,而且將完全具備非競爭性和非排斥性的公共產品稱作為純公共產品,以區別于其他被稱作為準公共產品的公共產品。盡管如此,但大部分理論分析卻并沒有介意這樣的區分,而是以純公共產品為前提來探討政府的公共產品提供”(山田太門,2020:37)。這種理論邏輯上成立的公共物品在現實中幾乎找不到相對應的物品。例如,有些物品和服務(如醫療、教育和住房等)在一些國家屬于公共物品,在另一些國家卻不屬于公共物品,即不同國家公共物品供給的類型不同;即使是同一個國家,在不同時期供給的公共物品類型也不同。基于公共物品概念無法與現實對應的尷尬困境,呂冰洋(2018)借用了布坎南對公共物品的定義,即 “人們觀察到有些物品和服務是通過市場制度實現需求與供給的,而另一些物品與服務則通過政治制度實現需求與供給,前者被稱為私人物品,后者則稱為公共物品”(布坎南,2009:1)。雖然布坎南所言的政治過程主要是指 “可行的一致同意” 這一規則而非具體的國家或公共組織,但其啟示性意義在于,人們可以從公共物品供給的 “主體”,而不是僅從公共物品的 “物品屬性” 來區分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本文認為,一般情況下,由公共組織(國家或社會組織)供給的物品和服務都屬于公共物品,通過市場購買的物品和服務都屬于私人物品。
一旦從公共物品供給主體出發來討論需求與供給的關系,我們就會發現,公共物品的供需關系和市場失靈并無直接關系,而是與人類對公共物品的需求相關。人類對公共物品的需求主要基于三個原因。“一是個人或社會基本單位無力從事,只能由社會力量方能實現的事務;二是對個人或社會基本單位無直接利益或利益極少而不愿辦,又是社會存在與發展所必需的事務;三是唯有社會為主體去舉辦,方能有效地協調相關社會成員各個方面利益的事務。這三點既是區分社會再生產諸多事務中哪些屬于社會共同需要事務的標準,也是界定財政職能范圍的依據”(何振一,2005:13-14)。雖然何振一沒有詳細闡述 “社會力量” 或 “社會” 是什么,但在他看來,提供公共物品的 “社會” 是一個外在于 “個人” 的合作集體,是一種超越于個人力量的共同體力量。在關于財政起源的論述中,這個“社會” 既是原始社會的 “氏族” 或 “原始公社”,也是后來的 “國家”,即獨立于個人的團體或公共組織,它們構成了公共物品供給的 “主體”(何振一,2005:35-45;吳才麟,2016)。
(二)社會失序:現代公共財政的產生
在國家這種超大規模的群體組織和社會單元產生之前,人類的所有公共需要和公共物品都是由家庭、氏族、部落等 “社會” 單元來滿足和供給的。在原始采集社會,“大多數智人部落不斷遷移,隨著季節變化、動物每年的遷移、植物的生長周期,人類也不斷追逐著食物,從一地前往另一地”(赫拉利,2017:48)。他們現采現吃,無論是保存食物還是儲存食物都不是普遍的事情。因此,原始社會幾乎沒有多余的食物和剩余產品。當時人類最主要的公共物品就是安全和食物,氏族或部落共同合作應對危機四伏的動物世界,一起打獵、采集以獲取食物,并共同分享食物。
農業革命使人類定居下來,人類有了一個固定的活動中心 —— 家園。隨著生產力和儲存技術的發展,家庭、氏族等親屬團體的剩余勞動產品也越來越多。如何分配這些剩余的勞動產品,也即公共物品的供給問題,是家庭、氏族等親屬團體需要面對的重要問題。與此同時,定居下來的農民需要共同合作的事務也日益增多,房屋的搭建、農田水利的修建等都是極其重要的公共事務。即使進步至農業社會,在家庭、家族或氏族中,也仍然存在由家長或族長負責親屬團體內部的生產、分配及秩序這一情況(恩格斯,2018;摩爾根,2012;韋伯,2006:41)。簡言之,在西方現代國家產生之前,人類的公共物品需求主要由作為 “共同體” 的家庭、氏族、部落、村社、封建領主和教會組織等 “社會” 主體來滿足。
自由市場的確推動了現代公共財政的產生,但其背后的邏輯并非源于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非競爭性等屬性所導致的市場失靈,而是由于自由市場及其相伴隨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引發了前所未有的社會秩序問題。波蘭尼(2013)稱之為 “巨變” 或 “大斷裂”,涂爾干、馬克思、韋伯等社會學家稱之為 “社會大轉型”,歷史學家則稱之為 “一個史無前例的冷酷時期”(霍布斯鮑姆,2017:228)。在這一時期,隨著自由市場和工業革命的出現,資本主義生產開始取代農民家庭手工業和其他自給生產領域,農民與土地開始分離,家庭、社群和其他初級 “社會” 組織逐步瓦解,人們不得不終結自己原有的生產和生活方式,走出山區和農村,進入城市和工廠,成為市場上的 “商品”。他們除了其勞動力之外,一無所有,無依無靠。與此同時,傳統倫理道德和社區共同體的互助制度也被市場經濟瓦解,人們陷于世風日下、道德淪喪的深淵,許多人面臨他們無法理解的社會災難,如貧困、無家可歸,以及前所未有的健康和公共衛生問題。同時代的作家在《霧都孤兒》《雙城記》《賣火柴的小女孩》和《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等作品中,對當時民眾的苦難生活和社會秩序進行了詳細描述與深刻揭示。失業、赤貧、壓迫和無助導致勞工運動與社會暴動不斷爆發。面對愈發嚴重的社會問題和日益混亂的社會秩序,政府實施了一系列改善公共秩序、穩定社會的舉措,出臺了涉及公共衛生、公共保障、公共事業建設的公共政策。現代公共財政便是伴隨這些公共政策的產生而產生的。
(三)國家與社會關系中的財政
雖然現代公共財政產生于工業革命和市場經濟之后的 “社會大轉型”,但 “財政” 有悠久的歷史。它伴隨著國家的產生而產生,是國家治理的基礎。然而,在現代公共財政學中,國家要么只是彌補市場失靈的 “有形之手”,與市場這一 “無形之手” 一樣具有資源配置功能(馬斯格雷夫,2003);要么只是一個追求 “一致同意” 的 “政治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國家與市場上的其他理性人一樣,只是公共選擇的主體之一(布坎南、圖洛克,2017)。總之,現代公共財政學將國家抽象成了一種 “制度集合”,或是一個沒有歷史經驗和文化的理性人。
正是因為現代公共財政理論無法解釋我國國家與財政之間的實踐關系,國家才將財政重新定義為 “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財政與國家治理的關系主要指涉財政在治國理政中所發揮的作用與功能,而財政的性質與功能恰是由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所塑造的。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并不是抽象或邏輯演繹的,而是在具體的歷史與現實經驗中形成的。
財政契約:西方 “稅收國家” 的產生
葛德雪和熊彼特對財政與國家的關系的討論便是基于歷史唯物主義的視角,認為國家是為了滿足某種公共需求而產生的。熊彼特所謂的稅收國家其實就是他后來所說的資本主義國家,也即學界普遍所說的西方現代民族國家。稅收國家的成長過程其實就是西歐現代國家的成長過程(埃利亞斯,2009;蒂利,2007;曼,2007),其成長的主要動力即熊彼特所說的 “自由經濟” 和 “市民社會”(因現代工商業興起的商人群體)。國王需要打破封建格局以獲得更多的人口和土地,而以商人群體為主的市民社會也需要打破封建領土的藩籬,以建立統一的自由市場;但國王無法支付統一戰爭所需的資金,因此需向有錢的市民社會借款。然而,握有資本的市民社會并不愿意無條件地滿足國王的稅收需求,于是 “無代表、不納稅” 成為市民社會的政治訴求和交換條件,并最后形成了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的 “財政契約” 模式。
綜上所述,西歐從封建領主國家轉向稅收國家的過程實質是國王、貴族僧侶和市民社會之間的斗爭過程,即國王與市民社會合作瓦解封建社會的過程。隨后,市民社會又認為基于 “血統” 的國家權力沒有合法性,要求限制王權,實施憲政,由此產生了政黨和議會制度。這種國家與社會關系塑造了稅收國家的基本特性:國家與社會以稅收為交換媒介,形成了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和購買者的市場交換關系,并通過政黨政治來表達雙方的需求。作為顧客的公民為了減稅以及爭取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務不斷與國家進行博弈和抗爭,而代表國家的政黨為了獲取政治權力,也不斷地承諾減稅并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稅收國家由此陷入不斷循環的財政危機之中。
2. “家國共同體”:財政治理的社會基礎
雖然我國在秦代之前也是封建國家,但其經濟基礎并非歐洲的莊園經濟,社會結構也不是農奴制(錢穆,2013:13-17)。我國古代封建時期實施井田制,只有中間公田的收成為封建地主所有,私田的收成則歸農戶所有。公田的收成除了供養封建地主之外,也要用于為農民提供公共設施、安全、救濟等公共服務。井田制被廢除之后,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郡縣制國家逐漸形成,農民無論田地多少,只需交賦稅,此即所謂 “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錢穆,2013:16)。以賦稅為主要形式的財政收入由戶部專門管理,用于公共物品供給。國家的 “公共性” 也由此彰顯。此外,以皇室封地為基礎的 “皇家財政” 由 “內務府” 管理,主要用于皇室家族支出。傳統中國由此形成了 “公私并存” 的財政制度。新中國成立以來,1949—1978 年的國家財政建立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基礎之上,國家領土內的所有資源都構成了國家財政收入的來源。民眾的大部分需求也都經由國家供給的公共物品來滿足,即 “對公民從生下來直到死亡的許多需要都由政府統包”(何振一,2005:17)。改革開放后,我國形成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經濟結構。國家財政收入既來自公有制的國有企業,也來自集體所有制的鄉鎮企業,還來自私人經濟和個人收入。因此,無論是熊彼特的以自由經濟為基礎 “稅收國家”,還是以莊園經濟為基礎的領地國家,都無法概括我國自秦漢以來 “公私并存” 的國家財政特性。
我國公私并存的財政特性是基于國家與社會之間相互融合的關系。自秦漢以來,我國便形成了所謂 “家庭與國家組織的同構體” 的關系(金觀濤、劉青峰,2010:50;許紀霖,2017:2)。相較于 “個人本位” 的西方社會,中國社會屬于以 “倫理” 組織的社會(梁漱溟,2018:94;錢穆,2019b:26),或 “倫理本位” 的社會,即 “國家消融在社會里面,社會與國家相渾融”,“它沒有邊界,不形成對抗。恰相反,它由近以及遠,更引遠而入近;泯忘彼此,尚何有于界劃?自古相傳的是‘天下一家’,‘四海兄弟’”(梁漱溟,2018:94-96、191);群己、公私之間的界限是相對而非絕對的。如梁漱溟(2018:96-98)所言:
倫理社會中,夫婦、父子情如一體,財產是不分的。而且父母在堂,則兄弟等亦不分;祖父在堂,則祖孫三代都不分的,分則視為背理(古時且有禁)—— 是曰共財之義。不過倫理感情是自然有親疏等差的,而日常生活實以分居為方便;故財不能終共。于是弟兄之間,或近支親族間,便有分財之義。初次是在分居時分財,分居后富者或再度分財于貧者。親戚朋友鄰里之間,彼此有無相通,是曰通財之義。通財,在原則上是要償還的;蓋其分際又自不同。然而作為周濟不責償,亦正是極普通情形。還有遇到某種機會,施財亦是一種義務;則大概是倫理上關系最寬泛的了。要之,在經濟上皆彼此顧恤,互相負責;有不然者,群指目以為不義。此外,如許多祭田、義莊、義學等,為宗族間共有財產;如許多社倉、義倉、學田等,為鄉黨間共有財產;大都是作為救濟孤寡貧乏和補助教育之用。這本是從倫理負責觀念上,產生出來的一種措置和設備,卻與團體生活頗相近似了。
再與西洋對照來看,像英美等國常有幾百萬失業工人,整年從國家領取救濟金維持生活,實為過去中國所未聞。在他們非獨失業問題如此,什么問題來了,都是課問政府。因為西洋原是團體負責制。中國則各人有問題時,各尋自己的關系,想辦法。而由于其倫理組織,亦自有為之負責者,因此,有待救恤之人恒能消納于無形。此次抗戰,在經濟上支撐八年,除以農村生活偏于自給自足,具有甚大伸縮力外,其大量知識份子和一部分中上階級之遷徙流離,卒得存活者,實大有賴于此倫理組織。中外人士固多有能察識及此,而道之者。
這些論述足以說明 “家國一體” 的中國社會如何 “彼此顧恤,互相負責”,“守望相助、疾病相扶”。許倬云則用 “親緣組織” 和 “類親緣組織” 等具體的 “主體”,說明了 “互幫互助、共渡難關” 的中國 “社會共同體” 是如何為社會成員提供公共物品的(許倬云,2018:210-215)。
3. “國泰民安”:財政治理的功能
當社會能為人們提供大部分公共物品時,國家財政的主要功能則是國防和社會穩定,即 “國泰民安”。但實現 “國泰民安” 并非只是一個財政問題,更是一個國家治理問題。例如,我國賦稅制度從漢朝的田租、賦稅發展到唐朝的 “兩稅法”,再到明朝的 “一條鞭法” 乃至清朝的 “攤丁入畝”,國家所要解決的不僅僅是國家的供養問題,更是土地問題、農民問題,以及 “士農工商” 之間的社會關系問題。國家將 “農” 置于 “工商” 之上,主要是因為人口占絕大多數的農民是社會穩定的基礎,保障 “農” 這個社會基礎,就能實現 “民安” 的目標。為此,國家一方面實行輕徭薄賦,另一方面避免土地的大規模集中,推行 “耕者有其田”,保證小農充分就業,以避免大規模的流民引發社會秩序問題。為了實現 “國泰” 這一目標,國家控制鹽鐵等可獲大利的工商業,從中獲得主要的財政收入用于國防。也正是因為國家的主要財政收入來源于國家控制的自然資源,國家才能給小農以輕徭薄賦。而國家對主要資源的控制基于儒家 “節制資本”“重農抑商” 的治理理念,通過限制工商業的發展,保持 “士農工商” 之間的平衡。如果國家因官僚體制的腐敗無法從重要資源中獲得財政收入,就只能對小農課以重稅,因而極有可能導致士農關系的失衡,甚至引發農民起義,“民安” 亦無從談起。而一旦土地、鹽鐵等重要資源集中于私人手中,不僅會出現嚴重的貧富分化,而且國家將陷入葛德雪所說的 “國中之國” 的困境,因此喪失自主性,“士農工商” 平衡的社會秩序將無法維持,“國泰民安” 的目標也無法實現。因此,我國國家治理與財政關系的獨特性在于,國家并非一味地追求其財政利益的最大化,而是如何通過財政來平衡政治、經濟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實現 “國泰民安”。正如錢穆所說,中國的傳統經濟理想是孔子所說的 “貧而樂、富而好禮”,即社會雖然無法達到 “均貧富” 的境界,但力圖在某種限度內保持其平等,要讓窮人能夠獲得一些快樂,富人知禮守禮。“禮便是一種生活的節制與限度”,“亦即是一種均產的理想,這一種理想的執行人就是‘士’”(錢穆,2019a:58-59)。
20 世紀以后的中國雖然也被納入到了現代民族國家體系之中,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并沒有演變出西方式的國家與社會關系。相反,社會主義理念與優秀傳統文化相通,現代中國不僅繼承了傳統 “家國一體” 的國家與社會關系,正如一些歌詞表達的那樣,“我們都有一個家,名字叫中國”,“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還繼承了傳統 “貧而樂、富而好禮” 的發展理念,例如執政黨始終將 “共同富裕” 作為社會發展的遠景目標。“共同富裕” 也不是均富,而是強調社會群體之間的平衡發展。如果說 “富裕” 是一個經濟學問題,“共同” 是一個社會學問題(馮仕政,2022),那么 “共同富裕” 則是一個典型的財政社會學問題。“共同富裕” 是對人類社會發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平等現象進行反思和調適,將經濟發展和社會公平作為社會發展的雙重目標。
六、結論
本文遵循財政社會學創始人葛德雪的傳統,對財政社會學進行了 “正本清源”,強調了財政社會學的學科屬性。國內學者對財政社會學之所以出現不同的理解,一方面是由于財政社會學興起于國外,而國外學者對此也缺乏系統的梳理,財政社會學沒有專門的教材,只有少量零散且簡短的綜述性文獻(Campbell,1993;Backhaus,2002,2005,2013;Mclure,2009);另一方面是由于財政社會學本身具有跨學科的性質,不同學者根據自己的學科視角或研究議題來解讀財政社會學。這不僅導致財政社會學在國內出現學科不明、方法不明和研究對象不明等問題,也使國外的財政社會學議題極為寬廣,而且產生了不同的流派(Leroy,2011)。正因為財政社會學議題之廣泛、研究之碎片化,本文無法窮盡所有文獻,而是依據 “財政” 與 “稅收” 這兩條主線來梳理代表性研究和核心主題。
關于如何應對我國財政研究中的 “經濟化” 問題,以滿足國家提出的 “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 之理論需求,財政社會學給予了重要啟示。財政研究的 “經濟化” 不僅是英美主流財政理論的基本格局,也影響著我國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中國財政學科的體系框架(馬珺,2015)。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 “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 后,國內財政學界掀起了一場以國家治理為主題的財政學基礎理論本土化的大討論,認為財政學是一門綜合性學科,應該脫離西方經濟學的理論邏輯,回歸我國歷史與社會的視野(李煒光、任曉蘭,2013;高培勇,2014,2017;李俊生,2012;李俊生、姚東旻,2018;于海峰,2018;孫開,2018;陳志勇,2018;馬海濤等,2020)。然而,大多數學者停留于 “呼吁” 層面。雖然有一些學者試圖從公共風險(劉尚希等,2018)和公共秩序(呂冰洋,2018,2021)的角度構建國家治理財政論,但囿于學科邊界,仍然無法擺脫其 “經濟化” 問題。
歐陽靜,江西財經大學財稅與公共管理學院,202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