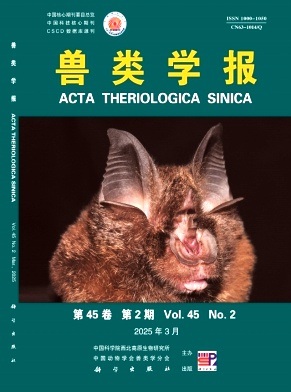獸類學(xué)報(bào)雜志投稿格式參考范文:祁連山豺的分布現(xiàn)狀及適宜棲息地預(yù)測
時(shí)間:
引言
豺(Cuon alpinus)是一種大型社會(huì)性犬科動(dòng)物,具有較強(qiáng)的環(huán)境適應(yīng)性,偏好捕食大中型有蹄類。在其所處多種類型的生態(tài)系統(tǒng)中,豺均是頂級(jí)捕食者之一,通過營養(yǎng)級(jí)聯(lián)對整個(gè)生態(tài)系統(tǒng)造成影響。豺曾經(jīng)廣泛分布于亞洲的中部、南部和東部,但現(xiàn)在已經(jīng)從其約 80% 的歷史分布區(qū)中消失,現(xiàn)存種群也被嚴(yán)重分割,并仍呈下降趨勢 ,被世界自然保護(hù)聯(lián)盟(IUCN)受威脅物種紅色名錄評(píng)估為瀕危(EN)物種。目前,豺的野生種群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威脅,包括偷獵、獵物資源匱乏、棲息地喪失和破碎化、人獸沖突、疫病等。歷史上豺曾在我國大陸的大部分省區(qū)有分布,然而其種群現(xiàn)狀和分布并不確定,有極大可能已經(jīng)從大部分歷史分布區(qū)消失。國家林業(yè)和草原局與農(nóng)業(yè)農(nóng)村部 2021 年發(fā)布的《國家重點(diǎn)保護(hù)野生動(dòng)物名錄》中,將豺的保護(hù)等級(jí)由國家二級(jí)重點(diǎn)保護(hù)野生動(dòng)物提升為一級(jí)。
國外對豺野外生態(tài)學(xué)與種群分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南亞和東南亞。由此可見,豺的棲息地利用隨地區(qū)和環(huán)境的不同而變化。但總體而言,相較于虎(P. tigris)、豹等長期被作為旗艦物種的大型食肉動(dòng)物,豺的野外研究仍十分有限。對豺的研究不足使這一物種成為了最鮮為人知的捕食者之一。相較于其他大型食肉動(dòng)物,缺乏研究的情況也使豺受到的保護(hù)和關(guān)注不足,與其受威脅和瀕危嚴(yán)重程度之間存在明顯落差。
在我國,相比于其他大型食肉動(dòng)物,如虎、豹、雪豹(P. uncia)、狼(Canis lupus)等,關(guān)于豺的野外研究匱乏,尤其未系統(tǒng)性地進(jìn)行過該物種分布與種群現(xiàn)狀的全面總結(jié)。隨著紅外相機(jī)技術(shù)在野生動(dòng)物監(jiān)測與生物多樣性本底調(diào)查中的大范圍應(yīng)用,在青藏高原周邊山地及云南南部的部分地區(qū),近年來在野外調(diào)查中偶爾有記錄到豺的報(bào)道,但其中絕大部分均為紅外相機(jī)調(diào)查中的 “兼捕(by-catch)” 記錄,而以豺?yàn)橹饕P(guān)注對象的針對性調(diào)查,以及區(qū)域尺度和全國尺度的系統(tǒng)評(píng)估都還十分缺乏。
綜上,本研究聚焦近年來有較多豺出現(xiàn)記錄的祁連山,以該地區(qū)作為我國西北至中亞廣大區(qū)域豺的干旱、半干旱棲息地的典型代表,在區(qū)域(山系)尺度對豺的分布現(xiàn)狀和棲息地適宜度進(jìn)行系統(tǒng)評(píng)估和預(yù)測。本研究通過全面收集紅外相機(jī)調(diào)查和公共新聞報(bào)道中豺的確認(rèn)出現(xiàn)記錄,利用集成物種分布模型(Ensemble species distribution model)預(yù)測豺的適宜棲息地分布,辨識(shí)重要棲息地斑塊和調(diào)查空缺,為該物種后續(xù)的監(jiān)測、科學(xué)研究和保護(hù)規(guī)劃等提供基線數(shù)據(jù)與支持。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區(qū)概況
本研究以祁連山為研究區(qū)域,參考 Duan 等(2021)的研究,并結(jié)合全球山脈生物多樣性評(píng)估(Global mountain biodiversity assessment,GMBA)發(fā)布的全球山脈數(shù)據(jù)集(Snethlage 等,2022),劃定祁連山范圍(北緯 35°48′~40°06′,東經(jīng) 93°24′~104°06′)。研究區(qū)位于中國西北部甘肅省和青海省交界處,總面積約為 2.4×10⁵ km²。作為青藏高原東北緣面積最大的山脈系統(tǒng),祁連山由多條西北 — 東南走向的平行山脈和寬闊的山谷組成,平均海拔在 3500m 以上。研究區(qū)內(nèi)冰川廣布,具有典型的大陸性高寒半濕潤山地氣候,年均溫為 0.6~2℃(Duan 等,2021),降水量從東南向西北遞減,并隨海拔升高而增加。研究區(qū)內(nèi)主要植被類型為草地、裸地和森林。草地和森林主要分布在研究區(qū)的中部和東部地區(qū),裸地主要位于西部地區(qū)。研究區(qū)內(nèi)棲息有雪豹、荒漠貓(Felis bieti)、兔猻(Otocolobus manul)、棕熊(Ursus arctos)和豺等珍稀瀕危野生動(dòng)物(Zhang 等,2018;薛亞東等,2019;胡大志等,2022)。
1.2 數(shù)據(jù)收集和處理
系統(tǒng)收集 2016—2024 年研究區(qū)域內(nèi)豺的出現(xiàn)位點(diǎn),數(shù)據(jù)來源:(1)紅外相機(jī)調(diào)查位點(diǎn),包括作者主持和參與的調(diào)查及其他團(tuán)隊(duì)發(fā)表的紅外相機(jī)調(diào)查;(2)野外目擊位點(diǎn),包括作者實(shí)地調(diào)查和對新聞報(bào)道的系統(tǒng)檢索。從紅外相機(jī)調(diào)查數(shù)據(jù)中提取豺的拍攝記錄,并從中提取每條記錄的拍攝時(shí)間和精確的坐標(biāo)信息。同一個(gè)位點(diǎn)上多次紅外相機(jī)拍攝只保留一條記錄。對于野外目擊位點(diǎn),除作者實(shí)地調(diào)查獲得的位點(diǎn)外,使用 “豺”“豺犬”“亞洲野犬”“紅狗” 和 “紅狼” 作為搜索詞,在百度和微信中,系統(tǒng)檢索 2016—2024 年研究區(qū)域內(nèi)豺的目擊或出現(xiàn)的新聞報(bào)道。篩選同時(shí)包含豺目擊或出現(xiàn)的具體地點(diǎn)信息和豺的照片或視頻的新聞報(bào)道作為可用記錄。通過核查所有豺的野外目擊記錄中的照片或視頻等實(shí)證性證據(jù)進(jìn)行物種確認(rèn),然后提取記錄地點(diǎn)、位置(經(jīng)緯度坐標(biāo))和時(shí)間等信息。同一個(gè)位點(diǎn)上多次目擊只保留一條記錄。
1.3 棲息地適宜性分析
為避免空間模型在出現(xiàn)點(diǎn)聚集地區(qū)過度擬合 ,在構(gòu)建物種分布模型之前,使用 R 語言程序包 “spThin” 對所有豺出現(xiàn)位點(diǎn)進(jìn)行空間疏化處理,疏化距離為 1km。同時(shí),在研究區(qū)內(nèi)除出現(xiàn)位點(diǎn)之外的 1km×1km 網(wǎng)格中,隨機(jī)生成 5000 個(gè)背景點(diǎn)作為偽缺失(pseudo-absence)數(shù)據(jù)。疏化后剩余的出現(xiàn)位點(diǎn)(出現(xiàn)數(shù)據(jù))和背景點(diǎn)(偽缺失數(shù)據(jù))直接用作后續(xù)構(gòu)建物種分布模型的輸入數(shù)據(jù)集。
選取四類可能影響豺棲息地適宜度的變量,包括地形變量、氣候變量、植被變量和人類活動(dòng)變量。地形變量為崎嶇度(RUG),基于分辨率 30m 的數(shù)字高程模型(DEM),使用 ArcMap 10.8 中地形崎嶇度指數(shù)工具計(jì)算 3×3 矩形內(nèi)中心點(diǎn)海拔與周圍柵格海拔差值的平均值,反映地形的起伏程度。氣候變量包括從世界氣候數(shù)據(jù)庫下載的 19 個(gè)氣候因子(Bio1~Bio19)。植被變量包括歸一化植被指數(shù)(NDVI)和森林覆蓋度(ForestCov)。NDVI 使用 2015 年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 MODIS 來源的 500m 分辨率逐月的 NDVI 數(shù)據(jù),并使用最大合成法在 ArcMap 10.8 中合成年度植被指數(shù)數(shù)據(jù)集。ForestCov 基于歐洲空間局發(fā)布的 2021 年全球土地利用數(shù)據(jù)集進(jìn)行計(jì)算,提取森林所在的柵格分類,計(jì)算其在 1km 分辨率柵格內(nèi)的森林占比(%)。人類活動(dòng)變量有家畜密度(Livestock)、人類修飾指數(shù)(HM)和國內(nèi)生產(chǎn)總值(GDP)。其中,人類修飾指數(shù)是一個(gè)用于量化評(píng)估人類活動(dòng)對陸地生態(tài)系統(tǒng)功能影響的綜合指標(biāo),基于 13 種人類活動(dòng)因素通過空間模型計(jì)算得出。使用 ArcMap 10.8 提取以上變量在研究區(qū)范圍內(nèi)的圖層,將所有數(shù)據(jù)重采樣到分辨率為 1km×1km(坐標(biāo)系為 Albers conic equal area)。
為避免多重共線性對物種分布模型的影響,計(jì)算每對變量之間的 Pearson 相關(guān)系數(shù),保留相關(guān)性系數(shù)小于 0.7 的所有環(huán)境變量,以及相關(guān)性大于 0.7 的兩個(gè)或多個(gè)變量中更具有生態(tài)學(xué)意義的一個(gè)。最終獲得 7 個(gè)環(huán)境變量用于后續(xù)的模型構(gòu)建,分別是崎嶇度(RUG)、年平均氣溫(Bio1)、歸一化植被指數(shù)(NDVI)、森林覆蓋度(ForestCov)、家畜密度(Livestock)、人類修飾指數(shù)(HM)和國內(nèi)生產(chǎn)總值(GDP)。
使用集成物種分布模型對研究區(qū)內(nèi)豺的棲息地適宜度進(jìn)行建模。該模型綜合了多種建模方法,可以顯著提高預(yù)測結(jié)果的穩(wěn)定性和精確性,近年來被廣泛用于物種分布預(yù)測研究中。為了得到最終的集成模型,本研究使用了 3 種基于回歸的模型,即廣義線性模型(GLM)、廣義相加模型(GAM)和多元自適應(yīng)回歸(MARS),以及 4 種機(jī)器學(xué)習(xí)算法:梯度提升機(jī)(GBM)、隨機(jī)森林(RF)、人工神經(jīng)網(wǎng)絡(luò)(ANN)和最大熵模型(MaxEnt)。使用 80% 隨機(jī)選擇的出現(xiàn)位點(diǎn)和所有背景點(diǎn)作為訓(xùn)練數(shù)據(jù)進(jìn)行模型擬合,使用剩余 20% 的出現(xiàn)位點(diǎn)作為測試數(shù)據(jù),通過計(jì)算受試者工作特征(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線下面積(Area under the curve,AUC)和真實(shí)技巧統(tǒng)計(jì)值(The true skill statistic,TSS)來評(píng)估模型的性能。對每個(gè)單獨(dú)的模型運(yùn)行 10 次,然后選取 AUC≥0.8 的模型,根據(jù) AUC 值進(jìn)行加權(quán)平均,得到最終的集成模型。模型的構(gòu)建與評(píng)估使用 R 語言程序包 “biomod2” 完成。
此外,使用 R 語言程序包 “biomod2” ,根據(jù)標(biāo)準(zhǔn)預(yù)測值(擬合值)和使用隨機(jī)排列的變量預(yù)測值之間的 Pearson 相關(guān)性計(jì)算得到各個(gè)變量的相對重要值(Relative importance),以評(píng)估每個(gè)預(yù)測變量的相對重要性。基于集成模型繪制各變量的響應(yīng)曲線,以探究各個(gè)環(huán)境變量和豺棲息地適宜性之間的關(guān)系。最后,在 ArcMap 10.8 中使用 De Smith 等(2024)提出的自然間斷點(diǎn)法,將豺適宜棲息地預(yù)測結(jié)果按照各個(gè)像元的棲息地適宜度值劃分為四類,分別定義為不適宜棲息地 [0,0.109)、低適宜棲息地 [0.109,0.285)、中適宜棲息地 [0.285,0.518)和高適宜棲息地 [0.518,1)。分別計(jì)算各類棲息地的面積,并將其與研究區(qū)內(nèi)的保護(hù)地邊界范圍進(jìn)行疊加,計(jì)算各類別在保護(hù)地內(nèi)、外的面積及占比。此外,祁連山國家公園是研究區(qū)內(nèi)面積最大的保護(hù)地,且是國家重點(diǎn)規(guī)劃項(xiàng)目。為了更好地為國家公園建設(shè)提供服務(wù)和支持,本研究統(tǒng)計(jì)了國家公園內(nèi)、外豺的出現(xiàn)位點(diǎn)數(shù)量和來源,并對該范圍內(nèi)高適宜棲息地的分布進(jìn)行具體描述。
2 結(jié)果
2.1 祁連山豺分布現(xiàn)狀
經(jīng)審核和去重,2016—2024 年在祁連山研究區(qū)內(nèi)共收集到 90 個(gè)豺的出現(xiàn)位點(diǎn),其中 76 個(gè)來自紅外相機(jī)調(diào)查,14 個(gè)來自目擊報(bào)道。在 90 個(gè)位點(diǎn)中,有 61 個(gè)在祁連山國家公園內(nèi):甘肅片區(qū)的酒泉管轄片區(qū)記錄最多(n=38),其次是張掖管轄片區(qū)(n=18);青海片區(qū)最少(n=5,其中 4 個(gè)來自紅外相機(jī)調(diào)查,1 個(gè)來自目擊報(bào)道)。在祁連山國家公園外有 29 個(gè)豺的出現(xiàn)位點(diǎn),其中 19 個(gè)來自紅外相機(jī)調(diào)查,10 個(gè)來自目擊報(bào)道。
豺的分布位點(diǎn)集中在研究區(qū)北部和西北部的玉門南山、大雪山、疏勒南山、野馬南山、托勒南山與走廊南山,共 86 個(gè),占全部位點(diǎn)總數(shù)的 95.6%。研究區(qū)西部的黨河南山與小哈爾騰區(qū)域、東部的冷龍嶺與達(dá)坂山區(qū)域和南部的宗務(wù)隆山區(qū)域僅有零星記錄(各 1 個(gè)),而研究區(qū)中部和東南部沒有記錄。在時(shí)間上,78.9% 的記錄(71 個(gè)位點(diǎn))來自 2020—2024 年。
通過核對出現(xiàn)記錄的照片和視頻,在祁連山國家公園外,酒泉管轄片區(qū)東北部的邊界外曾 7 次目擊到由 1~9 只個(gè)體組成的不同豺群,紅外相機(jī)記錄到的最大豺群由 12 只個(gè)體組成。在祁連山國家公園內(nèi),張掖管轄片區(qū)有 3 處紅外相機(jī)曾分別捕獲到 14 只個(gè)體、4 只個(gè)體和 2 只個(gè)體,此外,在此片區(qū)還曾目擊到 3 只個(gè)體。在青海片區(qū)南部曾目擊到 1 只個(gè)體的殘骸。
2.2 豺在祁連山的適宜棲息地分布
經(jīng)過空間疏化處理,最終有 73 個(gè)豺的出現(xiàn)位點(diǎn)用于棲息地模型的構(gòu)建。根據(jù) AUC 和 TSS 指標(biāo),集成模型得到 AUC=0.974,TSS=0.864,表明模型預(yù)測準(zhǔn)確度高,預(yù)測結(jié)果可靠。用于構(gòu)建集成模型的所有單模型的預(yù)測準(zhǔn)確度和區(qū)分度也都足夠高(AUC>0.8,TSS>0.6,其中 MaxEnt 模型 AUC 和 TSS 值均最高 AUC=0.917,TSS=0.763)。
集成模型中,變量的平均相對重要性分析結(jié)果顯示,崎嶇度、家畜密度和年平均氣溫是影響豺棲息地適宜度的主要因素。響應(yīng)曲線顯示,豺更偏好崎嶇度較高(平均海拔落差 300~700m)、年平均氣溫適中(−5℃)、家畜密度較低(<70 ind./km²)的地區(qū)。植被歸一化指數(shù)和森林覆蓋度的響應(yīng)趨勢均較為平緩,其中當(dāng)植被歸一化指數(shù)為 0.3 時(shí),豺的棲息地適宜度最高。隨著人類修飾指數(shù)和國內(nèi)生產(chǎn)總值增加,豺的棲息地適宜度降低。
根據(jù)集成模型預(yù)測結(jié)果,研究區(qū)內(nèi)豺的不適宜棲息地、低適宜棲息地、中適宜棲息地和高適宜棲息地面積分別為 1.34×10⁵ km²、5.81×10⁴ km²、2.99×10⁴ km² 和 1.85×10⁴ km²,分別占研究區(qū)面積的 55.8%、24.1%、12.4% 和 7.7%。中、高適宜棲息地主要分布在肅北北山、大雪山、玉門南山、托勒南山、走廊南山、疏勒南山和宗務(wù)隆山等區(qū)域。研究區(qū)南部的大通山和托勒山雖然迄今未有豺的確認(rèn)分布記錄,但也預(yù)測有較大面積的適宜棲息地或較高水平的棲息地適宜度。
在所有中適宜棲息地和高適宜棲息地中,分別有 40.3%(1.21×10⁴ km²)和 40.5%(7.50×10³ km²)被自然保護(hù)地所覆蓋。豺的適宜棲息地總面積約為 1.06×10⁵ km²,其中 36.8%(3.91×10⁴ km²)分布于祁連山國家公園范圍內(nèi)。
在研究區(qū)內(nèi)的自然保護(hù)地中,豺的高適宜棲息地主要分布在祁連山國家公園內(nèi)部(具體為甘肅片區(qū)酒泉管轄片區(qū)的黨河南山、野馬河?xùn)|段、貫穿甘肅酒泉和青海片區(qū)的疏勒河流域以及張掖管轄片區(qū)全境)、祁連山國家公園甘肅片區(qū)的酒泉管轄片區(qū)外的西北部和東北部、柴達(dá)木梭梭林國家級(jí)自然保護(hù)區(qū)東部地區(qū)和北部的宗務(wù)隆山。在祁連山國家公園甘肅片區(qū)酒泉管轄片區(qū)外的西北部和東北部、柴達(dá)木梭梭林國家級(jí)自然保護(hù)區(qū)東部地區(qū)和北部宗務(wù)隆山以及連城國家級(jí)自然保護(hù)區(qū)內(nèi)部,雖然豺的確認(rèn)分布位點(diǎn)較少,但模型預(yù)測的適宜度較高。
3 討論
豺歷史上曾廣泛分布于東亞、東南亞、南亞至中亞的大片區(qū)域,但自二十世紀(jì)中后期以來,其分布范圍發(fā)生了劇烈縮減。在我國,豺曾分布于大陸大部分省區(qū),但二十世紀(jì)末期以來,可能已從東北、華北、華東、華中等多地消失。2000 年以來,其確認(rèn)分布記錄主要來自西南及西北部分地區(qū)。由于缺乏系統(tǒng)調(diào)查與監(jiān)測,目前對我國豺分布狀況的了解存在諸多空白和錯(cuò)誤,在 IUCN 評(píng)估報(bào)告中,祁連山曾被認(rèn)為是豺分布的空白區(qū)域。本研究證實(shí)了豺在祁連山的分布,增加了其確認(rèn)分布區(qū)域,且祁連山擁有可自我更新的豺種群和較大面積的適宜棲息地,對中國西部干旱、半干旱區(qū)豺種群保護(hù)意義重大。
然而,祁連山豺種群的長期續(xù)存面臨挑戰(zhàn)。目前,祁連山豺可能以小集群形式分布在破碎化的斑塊化棲息地中,集群規(guī)模明顯小于熱帶與亞熱帶地區(qū)的豺群。雖然無法準(zhǔn)確評(píng)估其種群數(shù)量,但相較于歷史時(shí)期,其總數(shù)可能較低。二十世紀(jì)六七十年代,豺在祁連山廣泛分布,八九十年代種群數(shù)量卻急劇下降,原因尚無定論。此外,盡管祁連山豺的適宜棲息地總面積較大,但受地形、基礎(chǔ)設(shè)施和人為活動(dòng)影響,棲息地破碎化程度高。大型食肉動(dòng)物對棲息地破碎化較為敏感,如何維持和改善斑塊之間的連通性,保護(hù)目標(biāo)物種的集合種群,是大型食肉動(dòng)物區(qū)域保護(hù)規(guī)劃的關(guān)鍵問題,因此,祁連山豺種群的保護(hù)和恢復(fù)工作任重道遠(yuǎn)。
在祁連山豺的適宜棲息地中,部分已被自然保護(hù)地覆蓋,但仍有必要在山系尺度制定種群監(jiān)測和保護(hù)規(guī)劃。甘肅 — 青海邊界兩側(cè)的豺棲息地多被祁連山國家公園覆蓋并受到嚴(yán)格保護(hù),但國家公園外仍有一些高適宜度棲息地斑塊,如甘肅肅北縣縣城周邊山地、玉門市南部旱峽 — 石油河區(qū)域以及青海宗務(wù)隆山脈。目前,祁連山國家公園部分區(qū)域和玉門市南部開展過豺的調(diào)查,但國家公園外多數(shù)區(qū)域的調(diào)查仍需加強(qiáng)。對于該區(qū)域豺種群的進(jìn)一步調(diào)查和監(jiān)測,建議基于國家公園管護(hù)體系和雪豹種群監(jiān)測計(jì)劃評(píng)估公園內(nèi)部豺種群狀況,同時(shí)結(jié)合地方項(xiàng)目和社會(huì)資金開展公園外豺種群的專項(xiàng)調(diào)查。在保護(hù)方面,建議制定跨省合作保護(hù)規(guī)劃,協(xié)同開展反盜獵、緩解人獸沖突等措施,并創(chuàng)新保護(hù)策略,將豺和雪豹列為祁連山國家公園的雙旗艦物種。
本研究采用集成物種分布模型預(yù)測豺的適宜棲息地,結(jié)果與對研究區(qū)內(nèi)豺分布的認(rèn)識(shí)較為吻合。后續(xù)研究可從多方面提升模型預(yù)測的精確性和可靠性。豺的分布受生物學(xué)習(xí)性、關(guān)鍵獵物分布、種間相互作用和人類活動(dòng)等多種因素影響,目前的模型因缺乏獵物資源數(shù)據(jù),未加入關(guān)鍵獵物分布這一重要變量,這也是區(qū)域內(nèi)雪豹等物種棲息地研究面臨的局限。后續(xù)研究可聯(lián)合其他團(tuán)隊(duì),匯總調(diào)查數(shù)據(jù),量化評(píng)估關(guān)鍵有蹄類獵物和其他大型食肉動(dòng)物的種群與分布,并將其納入豺的物種分布模型。此外,還可參考引入新的技術(shù)框架和分析方法,如整合多源數(shù)據(jù)與空間標(biāo)記重捕、占域模型等,更精細(xì)、準(zhǔn)確地評(píng)估祁連山豺的種群分布。
劉炎林;王一丹;李祎斌;余辰星;王忠驊;胡大志;馬存新;王大軍;李晟,青海師范大學(xué)生命科學(xué)學(xué)院;北京大學(xué)生命科學(xué)學(xué)院;北京大學(xué)生態(tài)研究中心;甘肅鹽池灣國家級(jí)自然保護(hù)區(qū)管護(hù)中心;甘肅張掖國家級(jí)自然保護(hù)區(qū)管護(hù)中心;祁連山國家公園青海省管理局,202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