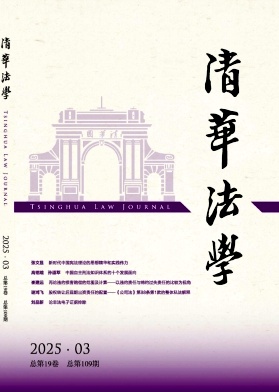清華法學雜志投稿格式參考范文:完善刑事證據制度若干重要問題探討
時間:
證據是司法公正的基石,刑事證據制度作為刑事訴訟制度的關鍵部分,對刑事訴訟活動意義重大。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中證據制度規定較為粗略,可操作性不強,雖有相關規范補充,但仍無法滿足實踐需求,冤錯案件的出現也暴露了其存在的問題。《刑事訴訟法》即將迎來第四次修改,借此契機探討刑事證據制度的建設,對促進其進一步改進具有重要意義。
一、形式完善:應大幅增加刑事證據制度的法律條文
我國《刑事訴訟法》自 1979 年頒布后歷經三次修改,但刑事證據制度立法一直較為單薄。1979 年《刑事訴訟法》“證據” 一章僅 7 個條文,1996 年第一次修改后為 8 條,變化不大。2012 年第二次修改雖對刑事證據制度有所完善,但 “證據” 一章也只有 16 個條文。2018 年第三次修改未涉及證據部分內容,仍延續 2012 年的立法規定。相比之下,大陸法系諸多國家的刑事訴訟法中,刑事證據制度條文數量都多于我國,如《意大利刑事訴訟法》“證據編” 有 85 條,“南京國民政府” 時期《刑事訴訟法》“證據” 章也多達 66 條規定。
在刑事司法實踐中,單薄的刑事證據制度難以滿足復雜刑事案件證據收集和審查的需求。為此,最高司法機關和公安部出臺司法解釋、部門規章予以完善,像《高法解釋》證據一章有 78 個條文,《高檢規則》有 20 個條文,《公安部規定》有 19 個條文。然而,這些解釋性規范存在問題,一方面部分條文突破《刑事訴訟法》規定,如《高法解釋》中 “專門性問題報告”“事故調查報告” 作為證據使用的規定;另一方面部分條文與《刑事訴訟法》重復,造成文件龐大冗雜,破壞了刑事證據制度的統一性。
有學者提出此次刑事訴訟法修改應將證據制度由獨立成章發展為獨立成編,或在現行 “證據” 一章下分節規定。本文作者建議,此次修法應在法典化基礎上,大幅增加刑事證據制度條文數量,至少將現有 16 個條文增加一倍至 32 個條文,爭取實現證據獨立成編。因為現行相關規范為修法提供了成熟經驗,增加條文數量具有可行性,若此次修法不把握機會,將錯失完善刑事證據制度的良機。
二、完善刑事證據制度基本原則問題
刑事證據制度的基本原則在刑事證據立法與運用中具有基礎性地位,是整個刑事證據運行機制的指導思想。但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未專門確立證據制度的基本原則,學者們雖有理論歸納,但部分存在照搬國外原則或未體現刑事證據制度特性的問題。作者就確立刑事證據制度基本原則提出以下建議:
確立證據裁判原則:證據裁判原則指訴訟中認定案件事實必須依據證據,刑事訴訟中認定犯罪事實尤其要依據證據。該原則是刑事司法制度發展的產物,從世界范圍看,刑事訴訟證明方式歷經神明裁判、口供裁判到證據裁判階段。其源于歐洲大陸法系國家,雖德、法等國現行《刑事訴訟法》未直接規定,但部分條文有所關聯,日本在立法中直接確立該原則,英美法系國家在理念上認同并通過證據規則體現。我國立法和司法遵循這一原則,不過目前僅在司法解釋中確立,未在《刑事訴訟法》中完整規定,僅有相關條文體現其精神。為促進程序公正,增強司法人員證據意識,應在《刑事訴訟法》“證據” 一章增加條文直接確立證據裁判原則。
貫徹不得強迫自證其罪原則:不得強迫自證其罪是公民基本憲法權利,具有豐富內涵,適用于提供言詞證據的人,核心要義是非強制性,且需配套法律保障機制。該原則歷經數百年發展成為國際通行的人權準則和刑事司法原則,聯合國公約及許多國家法律都有相關規定。我國 2012 年《刑事訴訟法》修改時增加 “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 的規定,意義重大,但與國際通行原則存在差異,如不得強迫作證范圍較窄,證明活動表述易造成誤解,且現行法保留犯罪嫌疑人如實回答義務,影響該原則保障。因此,應修正相關表述,并刪除犯罪嫌疑人如實回答義務的規定。
增加直接言詞原則:直接言詞原則要求審判法官在法庭上審查原始證據材料、親臨法庭審理案件、訴訟各方以言詞形式開展質證辯論。該原則起源于德國學者提出的 “口頭原則”,我國古代周朝就有類似審理方式。《德國刑事訴訟法》有相關規定體現該原則價值。我國 2012 年確立證人、鑒定人出庭制度,標志著該原則精神開始被吸收,但尚未完全確立。完善該原則需從兩方面著手:一是完善證人、鑒定人出庭制度,目前證人、鑒定人出庭率低,根源在于立法缺陷,如出庭條件限制和不出庭時證言使用規定不合理,應刪去不合理限定條件,修改證人不出庭時證言使用的規定;二是明確其適用范圍,考慮到我國 “輕罪時代” 的現狀及 “案多人少” 的矛盾,在被告人認罪認罰的輕罪案件中,證人原則上可以不出庭。
三、完善刑事證明標準問題
刑事證明標準是刑事訴訟中認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所要達到的程度,我國表述為 “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但理論界和實務界理解不一致,需要厘清其與 “排除合理懷疑” 的關系。
“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 與 “排除合理懷疑” 的關系:我國 “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 的證明標準有歷史傳承,經歷了封建時期強調定罪 “明白”“無疑”,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注重證據 “確實”“充分”,到 1979 年《刑事訴訟法》正式確立。2012 年《刑事訴訟法》修改時引入 “排除合理懷疑” 解釋 “證據確實、充分”,但二者存在問題。語義上,“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 要求司法人員根據證據達到主觀上對犯罪事實認識清楚,達到確定性程度,這與 “排除合理懷疑” 存在重疊。程度上,我國證明標準要求對主要犯罪事實證明達到確定性、唯一性,而英美法系對 “排除合理懷疑” 的主流觀點否定刑事證明能達到 “確定性”“唯一性”,二者標準存在差異,同時 “排除合理懷疑” 在我國法律體系中不協調,司法實踐中也較難把握,法官在刑事判決書中往往不采用。
增設 “確定性” 的刑事證明標準:刑事證明標準與錯案率呈反比例關系,我國現有證明標準較難把握,缺乏可操作性。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司法公正,為刑事證明標準改進指明方向。有學者建議采用 “排除合理懷疑” 作為獨立證明標準,作者認為我國應遵循訴訟文化傳統,增設 “確定性”(即 “唯一性”“排他性”)的證明標準。“確定性” 標準要求對案件定罪和量刑等關鍵事實證明達到 “確定性”,包括犯罪行為是否發生、犯罪主體是誰、加重刑罰的犯罪情節等,其他事實可適度降低證明標準。對關鍵事實證明達到 “確定性” 能保證司法案件事實認定符合客觀真相,避免冤假錯案,且在部分案件中完全可能達到。該標準應適用于刑事訴訟各個程序階段。
認罪認罰從寬案件的證明標準:2018 年刑事訴訟法確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2022 年適用該制度的犯罪嫌疑人占比達 88.17%,審判中適用簡易程序、速裁程序的案件占比 72.7%。有觀點認為可適當降低此類案件證明標準,作者認為對關鍵事實達到 “確定性” 的證明標準應適用于各類刑事案件,包括認罪認罰從寬案件。《刑事訴訟法》規定適用簡易程序、速裁程序的前提是 “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司法實踐中不能為提高效率犧牲公正,若關鍵事實證明無法達到 “確定性” 標準,即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認罰,也應依法作出相應處理。因此,應刪除 “排除合理懷疑” 表述,調整相關條款為 “綜合全案證據,對關鍵事實可得出確定性的結論”。
四、結語
我國刑事證據制度正逐步發展。期待通過刑事訴訟法的第四次修改,在立法機關、司法機關以及學者們的共同推動下,我國刑事證據制度能夠更加完備,更好地契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要求。
陳光中;魏家淦,中國政法大學,202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