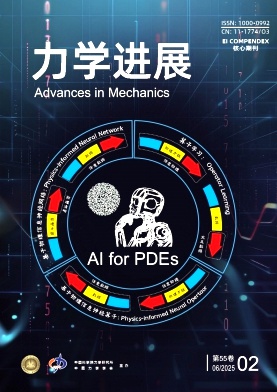力學進展雜志投稿格式參考范文:細胞核生物力學研究進展
時間:
為更深入地認識生理和病理狀態下細胞核的力學特性,揭示其在細胞命運決定中的作用和機制,本文總結了細胞核生物力學相關的研究進展,重點介紹了細胞核骨架、核孔復合體和染色質的物理結構、力學響應過程、各組分的相互作用以及用于細胞核生物力學研究的技術進展,最后總結了細胞核與早衰綜合癥、神經退行性疾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關系,并對細胞核生物力學未來發展進行了展望。
1 引言
作為真核細胞的標志,細胞核是遺傳物質儲存、復制和基因轉錄發生的中心,也是細胞響應外界物理、化學刺激的重要細胞器。細胞核直徑約為 5~15μm,被兩層磷脂雙分子膜組成的核膜所包裹,在空間上將遺傳物質和細胞質分隔開來,形成核內特殊的微環境。根據其位置不同,核膜分為胞質側的外核膜(outer nuclear membrane, ONM)與核質側的內核膜(inner nuclear membrane, INM),兩層核膜間具有 20~50nm 的間隙。ONM 向胞質側與內質網連通,向核質側與 INM 融合;在 INM 與 ONM 的融合處嵌入核孔復合體(nuclear pore complex, NPC),通過其中央的環形通道介導了胞質與核內物質的選擇性交換。
細胞核內貼近 INM 處分布著致密的核骨架蛋白纖維網−核纖層,是維持細胞核剛度的主要結構。細胞核膜上還存在跨越 ONM 和 INM 的細胞核 - 細胞骨架連接(linker of nucleus and cytoskeleton, LINC)復合體,該復合體由含有 KASH(Klarsicht, ANC-1 and Syne homology)結構域蛋白的 Nesprin(nuclear envelope spectrin repeat protein)和 SUN(Sad1-UNC84 homology)兩類蛋白組成。LINC 復合體在物理結構上連接了細胞骨架和細胞核,將細胞外的力學刺激經由細胞骨架傳遞至核內,進而影響染色質定位和基因表達。
細胞內機械力沿細胞骨架 - LINC 復合體傳遞的速度遠快于生物化學信號傳遞的速度。施加在細胞膜表面的機械力沿著細胞骨架以約 30m/s 的速度傳播,而細胞質中通過擴散作用移動的小分子物質(如鈣離子)的移動速度約為 2μm/s,細胞質中基于馬達轉運機制運輸的生物大分子,移動速度僅為 1μm/s。相比之下,傳遞 50μm(近似于從細胞膜到細胞核表面),鈣離子等小分子擴散需 25s,基于分子馬達運輸需 50s,而機械應力沿細胞骨架傳遞僅需 2μs。因此,細胞外機械力不僅可以激活細胞膜上 Piezo、整合素(Integrin)等力學感受器開啟細胞內級聯的生化事件,還可以通過細胞骨架 - LINC 復合體 - 核纖層這一系列物理連接結構直接被傳遞入細胞核,迅速地將物理信號轉化為核內生物事件。
細胞核是細胞中最硬的細胞器,其彈性模量約為 5000N/m²,是細胞質的 2~10 倍;細胞核也表現出一定的黏性特征,其黏性約為細胞質的 2 倍。對游離細胞核的體外拉伸實驗表明,在 < 30% 的形變范圍內細胞核對外力的抵抗由染色質主導,而對較大形變的抵抗則由核纖層蛋白 Lamin A/C 主導。對于低變形狀態的細胞核而言,染色質組蛋白修飾狀態和組成是決定細胞核力學性質的主要因素。通過使用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劑增加常染色質、使用組蛋白甲基轉移酶抑制劑減少異染色質或者干擾連接體組蛋白 H1,均導致細胞核變軟和更多的細胞核出泡事件。
撤去外力后,拉伸的細胞核以黏彈性的方式松弛,并表現出一定的延遲效應。例如,Neelam 等應用微吸管技術以 6nN 的吸力拉伸細胞核發現,撤銷吸力后形變的細胞核約 1.7s 后恢復至初始形狀,體現了細胞核的黏彈性特征。這種黏彈性特征的維持需要核纖層、LINC 復合體、染色質等核內組分的參與。新的證據還提示,染色質和核膜之間通過形成一個相互連接的網絡進一步增加細胞核剛度。細胞核的力學特性由核纖層蛋白、染色質和其他核成分之間的復雜耦合關系決定,而數值隨檢測方式、施加力的大小或被檢測成分的變化而變化。
此外,由于細胞骨架與核骨架之間的密切聯系與相互連接,胞質內各組分對細胞核力學特性的貢獻也并非單一存在。例如,細胞骨架紊亂、細胞骨架與核骨架解耦,可導致細胞核硬度改變以及細胞核不能對應力 / 應變做出適當響應。
細胞核的結構、組裝和力學特性對于細胞功能至關重要,如影響細胞的基因表達、分裂分化過程和疾病的進展。在臨床診斷方面,細胞核結構的異常已逐漸成為癌癥診斷 “金標準” 之一,包括細胞核形態大小的變化、核仁大小和數量的變化以及染色質形態等。因此,細胞核在機械信號轉導和細胞功能調控中的作用日益引起研究者的重視。本文主要介紹了細胞核內 3 種主要組分−細胞核骨架、NPC 和染色質的組成結構以及在生物力學領域的相關研究進展,進而關注各組分在力學刺激響應過程中的相互作用,同時總結了用于表征細胞核生物力學特性的技術進展,并對與細胞核相關的疾病進行了介紹,最后討論了細胞核生物力學研究的挑戰與前景,以期為從生物力學交叉的視角理解機體生理功能、揭示疾病發生發展新機制和尋找臨床轉化新靶點提供啟示。
2 細胞核骨架與生物力學
細胞核骨架是位于細胞核內的蛋白網架體系,包括跨核膜的 LINC 復合體、位于核漿內的致密網狀核纖層及相關蛋白。細胞核骨架不僅為細胞核提供穩定的力學支撐,而且在細胞機械信號轉導、基因轉錄調控中也具有重要作用。本章對細胞核骨架蛋白的主要組分 Nesprin、SUN、Emerin 和 Lamins 進行概述,并對其力學特性和參與的機械信號轉導過程進行介紹。
2.1 細胞核骨架蛋白概述
2.1.1 Nesprin 家族
Nesprin 蛋白錨定于 ONM,是 LINC 復合體中的重要組分之一,包含 Nesprin1、Nesprin2、Nesprin3 和 Nesprin4 共 4 種亞型,在結構上均含有長度可變的骨架蛋白重復序列(spectrin repeat, SR)和 C 末端高度保守的 KASH 跨膜結構域。
Nesprin1 又稱 Syne-1、Enaptin 或 Myne-1,是在尋找血管平滑肌細胞收縮表型特異性分化標記物的過程中發現的,也是首個被確認的 Nesprin 蛋白,其特征是存在多個成簇的血影蛋白重復域、2 個核定位序列(nuclear localization signal, NLS)和一個保守的 C 端單一跨膜結構域,在平滑肌和心肌細胞的 ONM 上高表達。
Nesprin2 又稱 Syne-2 或 NUANCE,其序列與 Nesprin1 有 60% 以上的同源性,在多種細胞的 ONM 表達,并且有少部分存在于核漿中。Nesprin1 和 Nesprin2 的 N 端均包含能與細胞骨架 F-actin 結合的鈣結合蛋白同源結構域(calponin homology domains, CHD),而 Nesprin3 和 Nesprin4 不包含 CHD 結構域。
Nesprin 的 4 種亞型與細胞骨架蛋白的結合能力和方式不同。Nesprin1 和 Nesprin2 通過 N 端 CHD 結構域與細胞骨架 F-actin 直接結合;Nesprin3 通過銜接蛋白 Plectin 與中間絲相互作用;Nesprin1、Nesprin2 和 Nesprin4 分別通過馬達驅動蛋白 Kinesin 和 Dynein 與微管相互作用。此外,4 種 Nesprin 亞型 C 端的 KASH 結構域在 ONM 和 INM 的間隙中與 SUN 結構域相互作用。通過上述連接結構,位于 ONM 的 Nesprin 蛋白將胞漿中的細胞骨架與細胞核緊密連接在一起。
2.1.2 SUN 家族
SUN 蛋白又稱 Sad1/UNC-84 蛋白,是一種廣泛分布于酵母、線蟲等真核生物的膜蛋白,主要定位于 INM 以及內質網。由于在酵母中發現 SAD1 突變后會影響紡錘絲的形成與功能,現象與線蟲中 UNC-84 突變的表型相似,并且兩種基因編碼蛋白的 C 端有近一半的序列同源,因此將 Sad1 蛋白與 UNC-84 蛋白名稱結合而得名 SUN 結構域。此后發現,包含 SUN 結構域的同源蛋白在真核生物中廣泛存在且高度保守,如酵母的 Sad-1、線蟲的 UNC-84 和 SUN1、果蠅的 Klaroid 和 Dm、動植物細胞內的 SUN1 和 SUN2 等同源蛋白。
到目前為止,已被確認的哺乳動物 SUN 蛋白有 5 種,包括 SUN1、SUN2、SUN3、SPAG4 和 SUN5。其中,SUN1 和 SUN2 蛋白是哺乳動物中最先被確認的 SUN 蛋白家族成員,具有保守的 SUN 功能結構域,并在體內廣泛表達,而 SUN3、SPAG4 和 SUN5 僅在睪丸中表達。
SUN1 和 SUN2 均為 Ⅱ 型跨膜蛋白,在核膜間隙內 SUN 結構域與 Nesprin1 和 Nesprin2 蛋白的 KASH 結構域形成穩定的物理連接。SUN 蛋白在調節細胞核的胞內遷移和錨定、DNA 損傷修復等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最近的研究結果表明,抑制 SUN2 的表達,可以有效減少機械牽張引起的細胞骨架 - 細胞核解偶聯和細胞核軟化,從而增加核的可變形性,提示 SUN2 通過調節細胞核力學特性在應力誘導的細胞核損傷中發揮重要作用。
2.1.3 Lamins 蛋白
Lamins 屬于第 V 類中間纖維(type V intermediate filament),位于 INM 下方并構成核周的致密蛋白纖維網絡結構,為細胞核結構提供了穩定支撐。組成核纖層的蛋白主要包括 A 型(Lamin A 和 Lamin C)和 B 型(Lamin B1 和 Lamin B2)。Lamin B1 和 Lamin B2 分別由 LMNB1 和 LMNB2 基因編碼,在所有哺乳動物細胞類型中普遍表達;Lamin A 和 Lamin C 均由 LMNA 基因編碼,是 LMNA 基因選擇性剪接的產物。
Lamins 的基本結構較為相似,主要包括 N - 端的頭部、雙螺旋中心結構、NLS 序列以及 Ig 折疊結構域(Immunoglobulin (Ig)-fold domain)的 C - 端尾部。Lamins 蛋白與 SUN 蛋白之間存在相互作用,從而將 LINC 復合物錨定到核纖層。
真核細胞胞質內的中間纖維(包括 Keratin 纖維、Vimentin 纖維、結蛋白纖維、神經纖維)往往首先形成同向二聚體,隨后形成反向錯位四聚體,四聚體再次螺旋纏繞形成 10nm 纖維束。而核骨架蛋白 Lamins 形成直徑 3.5nm 左右的四聚體纖維束,與典型的中間纖維的形成方式存在差異。雖然在體外 Lamin A/C 可形成異源二聚體,但在體內只形成同源二聚體。
原子力顯微鏡(atomic force microscope, AFM)研究表明,Lamins 在較低拉伸力(<500pN)下發生可逆形變;隨后在較大拉伸力下過渡到非線性應變硬化狀態,并在大于 2nN 的力下發生斷裂。在拉伸力低的狀態下,形變的可逆性可能是由于 Lamins 中 α 螺旋圈的展開引起的;而在拉伸力較大的條件下,纖絲的應變增強則是由于 α 螺旋向 β 折疊的結構轉變引起。該研究進一步表明,Lamins 蛋白可承受高達 2.5 倍的變形,這一數據與其他類型的中間纖維相當。
通過對 Lamins 蛋白的重復施力測量其滯后能,實驗表明 Lamins 蛋白在承受不同壓縮力時具有顯著的吸收能量的能力。因此,Lamins 蛋白具有顯著高于彈性蛋白(2MJ m⁻³)、肌腱膠原蛋白(7.5MJ m⁻³)或碳纖維(25MJ m⁻³)的拉伸韌性,其韌性值約為 147MJ m⁻³,與羊毛、尼龍和蠶絲(60~150MJ m⁻³)相當。Lamins 蛋白獨特的柔韌性使其成為維持細胞核剛度和完整性的核心要素,是保護基因組的最佳材料。
由 Lamins 形成的四聚體纖維束也存在細微差別,Lamin A/C 形成的網絡致密,而 Lamin B 形成的網絡存在較大間隙,當 Lamin B 缺乏時,細胞核呈現出泡結構。Bruce Nmezi 研究表明,Lamin A/C 和 Lamin B 形成互相獨立的網絡,分布于不同層面,Lamin B 緊貼 INM,而 Lamin A/C 位于其下側靠近核質,這種差異是由于 Lamin B 末端修飾的法尼基與 INM 互作引起的。Lamin A/C 作為細胞核中密度最高、機械強度最大的中間纖維,表達水平和組裝狀態是決定核硬度和黏彈性的最關鍵分子。
研究顯示,Lamins 不僅在維持細胞核結構和穩定性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同時還能直接或間接調控基因轉錄,參與核內 DNA 復制、基因表達和染色體構建等一系列核功能調控,并在癌癥、心肌和骨骼肌疾病中發揮關鍵作用。
2.1.4 Emerin 蛋白
Emerin 是一種由 EMD 基因編碼的 Ⅱ 型膜蛋白,其 N 端位于核漿,有 1 個包含 43 個氨基酸殘基的球狀結構域,該結構域在維持 Emerin 穩定性中具有重要作用。Emerin 蛋白有多種結合蛋白,不僅能與 Lamin A、SUN1、SUN2 和 Nesprin1 蛋白結合,還能與轉錄因子 BAF、GCL、Btf、Lmo7 和 β-catenin 等結合。
研究發現,Lamin A 與染色質的相互作用是基于 Emerin 實現的,Emerin 可以阻止染色體上有絲分裂末期 BAF 介導的 Lamin A 異常聚集,從而允許核膜擴張和核纖層的正常形成。Guilluy 等的研究結果顯示,對游離細胞核直接施加機械刺激引起的細胞核形態變化,能夠調控 Emerin 和 Lamin A 表達、分布和磷酸化。
雖然 Emerin 廣泛表達在人體的各個組織,但其突變引起的 Emery–Dreifuss 肌營養不良(Emery–Dreifuss muscular dystrophy, EDMD)顯示出組織特異性表型,主要導致肘部、頸部和跟腱的攣縮,并逐漸發展為骨骼肌的萎縮,最嚴重者會由于心肌傳導系統缺陷導致心跳停止。
Emerin 缺失引起 EDMD 疾病的機制并不完全清楚,推測可能是由于其磷酸化異常導致的功能改變。例如,臨床數據顯示,大量患有 EDMD 病人體內 Emerin 蛋白發生磷酸化修飾的第 59 位酪氨酸(Tyr59)位點均有缺失,而 Tyr59 位點的磷酸化能抑制轉錄因子 GCL、Btf、Lmo7 與 Emerin 的結合,并影響其各自的靶基因。
2.2 細胞核骨架與機械信號轉導
由 LINC 復合體、核纖層及相關蛋白構成的細胞核骨架作為貫穿雙層核膜、為細胞核提供穩定力學支撐的重要結構,在感受細胞外機械刺激和調控基因轉錄中發揮重要作用,是目前生物力學研究的熱點之一。
Guilluy 等的研究為細胞核通過細胞核骨架蛋白直接感受應力 / 應變刺激提供了重要的證據,應用 Nesprin-1 抗體包被的磁珠對 Hela 細胞分離出的細胞核直接施加應力刺激,在引起細胞核形態變化的同時迅速通過 Src 激酶引起核骨架蛋白 Emerin 酪氨酸磷酸化,調控核自身剛度變化。
Tajik 等應用 3D 磁扭轉細胞術對單個活細胞施加牽張應力,可迅速上調特定基因轉錄,該過程不依賴于胞漿內信號轉導,但依賴于細胞骨架和跨核膜的 LINC 復合體,而打斷 LINC - 核纖層結構誘導細胞骨架 - 細胞核解偶聯,在引起細胞骨架排列異常的同時,還能夠引起細胞核結構和硬度異常以及 DNA 損傷。上述研究有力地證實了應力 / 應變力學刺激可以通過細胞骨架 - LINC 復合體 - 核纖層這一系列物理連接結構,直接傳遞入細胞核,迅速地將物理信號轉化為核內生物化學信號。
目前,關于 Lamins 蛋白如何調控細胞功能存在 2 種假說。其中,基因調控假說認為,異常的 Lamins 蛋白可能通過對細胞核內表觀遺傳、轉錄調控和信號通路的激活或沉默統籌細胞活動;而結構假說則認為 Lamins 蛋白的表達變化可影響細胞核的剛度、韌性等力學參數,從而改變細胞核的力學敏感性。兩種假說相互獨立,且互為補充。例如,Lamins 蛋白異構體的缺失或敲低使小鼠胚胎成纖維細胞的核硬度由 15pN/μm 下降至 6pN/μm,并降低了表觀遺傳關鍵分子 H3K9me3 和 H3K27me3 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蛋白質表達水平變化外,Lamins 蛋白還存在復雜的剪切成熟和翻譯后修飾變化。在 LaminA 蛋白成熟過程中至少包含 C 端 Cys-Ser-Ile-Met 氨基酸序列 Cys 巰基的法尼基化修飾,Cys 甲基化和 CAAX 異戊二烯蛋白酶(Zmpste24)切割 C 端 15 個氨基酸 3 個步驟,而成熟后的 LaminA 除形成經典的 INM 下致密蛋白纖維網架外,在多種激酶作用下發生可逆性磷酸化修飾進而溶解形成核漿內的游離態 Lamin A 單體。
Lamin A的聚集和溶解狀態轉換受其磷酸化狀態調控,未磷酸化的 Lamin A 形成核纖層纖維蛋白網絡存在于 INM 下層,以響應外部張力或收縮力,進而增加核硬度,而磷酸化的 Lamin A 溶解并分布于核漿內。已有研究顯示,基質剛度等細胞外力學環境變化可以調控細胞 Lamin A 第 22 位絲氨酸(Ser22)的可逆性磷酸化修飾。
細胞收縮力與 Lamin A/C 的磷酸化狀態之間存在反比關系,例如在軟基質上培養的細胞中,細胞骨架收縮力降低會增加 Lamin A/C 的磷酸化,導致蛋白質溶解度增加。在對細胞核施加剪切應力的研究中發現,Lamin A/C 的 Ig 結構域中一個隱蔽的半胱氨酸殘基的可及性增加,而在沒有剪切應力的情況下該殘基的可及性要低得多,提示細胞核骨架張力的增加也會導致 Lamin A/C 結構的改變,降低細胞核基底側的特異性 Lamin A/C 表位的可及性。
除此之外,通過細胞核骨架傳遞的力會直接作用于染色質,特別是染色質核纖層相關結構域(lamina-associated domains, LADs),在真核生物基因組中,與核纖層接觸的區域被定義為 LADs。力學作用導致的 Lamin A/C 變化誘導染色質空間 / 時間動力學的改變,這一相互作用將在后續章節中進一步討論。
綜上所述,2 類核骨架蛋白 Lamins 蛋白和 LINC 復合物的相互作用在細胞核力學特性調控和機械信號轉導中發揮重要作用,決定了細胞外力學信號如何影響細胞的行為和命運。Lamins 蛋白感受應力 / 應變刺激后,可能通過自身表達、翻譯后修飾和結構變化直接調控核內染色質分布和基因轉錄,而 Lamins 異常也損害 LINC 復合體的結構與功能,引起細胞骨架 - 核骨架解偶聯,進而導致機械信號轉導缺陷和下游染色質功能障礙,參與早衰、腫瘤轉移等疾病發生發展。進一步深入系統地研究特定核骨架蛋白在細胞核力學特性、機械力傳遞和應力信號級聯傳導中的作用,可能有助于開發與核骨架蛋白相關的疾病精準診斷、再生修復和靶向治療新方法。
2.3 核內肌動蛋白 actin 概述
除上述細胞核骨架蛋白外,細胞核的結構和功能維持還離不開核內 actin 的參與。actin 作為真核細胞中含量豐富且高度保守的蛋白質之一,最初發現于兔子的骨骼肌中,后來的研究表明 actin 也是非肌肉細胞的重要組成部分。actin 是一種關鍵的細胞骨架蛋白,在細胞質中常以聚合形式存在并參與細胞的形態維持、細胞運動、內質網運輸等多種細胞力學過程。
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揭示細胞質 actin 的結構和功能,雖然早在 20 世紀 60 年代就有研究對細胞核中的 actin 進行了描述,但直到 21 世紀初,核內 actin 結構及其在調節真核細胞結構、功能、穩態等方面的重要性才逐漸引起研究者重視。
長期以來研究人員認為核內 actin 僅以單體的 G-actin 形式存在,但現有的研究已確定細胞質和細胞核內 actin 的組成和結構是相似的,都是由 G-actin 單體及其動態組裝的 F-actin 構成,其中核內 F-actin 組裝對于細胞核形態維持等事件具有重要作用。例如,非洲爪蟾卵母細胞具有較大的細胞核,需要核內 F-actin 的額外支持來穩定核結構。
細胞核內 actin 的可視化研究進一步支持了其可以組裝成絲的觀點。Baarlink 等使用了一種帶有 NLS 序列的 Lifeact 探針(該探針是源于出芽酵母蛋白 Abp140 的小肽探針,可結合 G-actin 和 F-actin),首次證明了血清誘導的 actin 蛋白在細胞核內的組裝。細胞質和細胞核內 actin 結構的不同之處在于,核內 F-actin 不會形成長的絲狀結構而是多以寡聚絲的形式存在,這可能是為了防止過長的 F-actin 干擾染色質而抑制轉錄等過程。
近年來,核內 actin 聚合在 DNA 損傷應答中的作用受到廣泛關注。Mullins 團隊證明了核內 F-actin 的形成參與了 DNA 損傷的核內氧化過程。另一項研究表明,磷脂酰肌醇在 DNA 損傷位點聚集并募集 formin 蛋白 mDia2 進而促進核內 F-actin 組裝,介導 DNA 修復蛋白 ATR 定位到損傷部位。Gautier 團隊的研究表明,Arp2/3 復合體也參與核內 actin 的聚合過程,而 F-actin 是受損染色質進行同源定向修復所需的。這些研究表明,核內 actin 的聚合對于 DNA 損傷應答過程是十分必要的。
此外,核內 actin 轉錄調節中具有重要功能。在體外實驗中,Actin 蛋白組分可增加 RNA 聚合酶 II 的活性,提示核內 actin 是形成轉錄起始復合物的必要條件。Wei 等證明細胞核內 N-WASP/Arp2/3 誘導 actin 的從頭聚合,促進 RNA 聚合酶 II 復合體的形成,提示核內 actin 聚合在轉錄調節過程中發揮作用。此外,在血清刺激下核內 G-actin 迅速形成 F-actin 網絡,促進了 MRTF-A 轉錄因子的核內滯留,從而響應血清反應因子調節轉錄。
目前,已經明確核內 actin 參與 DNA 損傷應答、轉錄調控等重要的核內生物過程,但具體機制仍有待深入研究。并且 actin 不斷穿梭于細胞核內外,細胞質與細胞核之間 actin 的平衡受到嚴格調控,但其調控機制尚不清楚。
3 NPC 與生物力學
NPC 是真核細胞細胞質與細胞核之間物質選擇性交換的精密納米通道,介導了離子和大分子物質快速和高選擇性的核 - 質雙向運輸,尤其在分子量大于 50 kDa 生物大分子進出細胞核過程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迄今為止,NPC 復雜而微妙的幾何結構以及核 - 質運輸的精細時空分辨率解析仍然存在巨大研究空白。研究人員應用連續介質力學、粗粒度布朗動力學、分子動力學、統計熱力學以及生物信息學等方法在 NPC 的結構和功能以及核質物質運輸的動力學等方面進行了探索。本章對 NPC 的基本結構進行概括,重點介紹 NPC 主導的核 - 質物質轉運過程以及 NPC 在機械信號轉導過程中的作用。
3.1 NPC 的基本結構
NPC 是鑲嵌在 ONM 和 INM 融合處的大型蛋白復合體。每個 NPC 由約 30 種核孔蛋白(Nups)以多拷貝的形式組成,總蛋白數約 500~1000 個,總分子量約為 110 MDa,這使得 NPC 成為細胞中最大的組裝復合體。核孔蛋白在 NPC 中組成亞復合體,具體分為結構支架、中央通道、細胞質絲和核籃。
NPC 結構支架核心包括內環和外環,它們通過跨膜核孔蛋白錨定在核膜上,并為中央通道、細胞質絲和核籃提供結構支撐。所有的 NPCs 亞復合體的核孔蛋白組成成分高度保守:結構支架中的外環主要包含 Elys、Nup37、Nup43、Nup85、Nup96、Nup107、Nup133、Nup160、Sec13 和 Seh1;內環包含 Nup35、Nup93、Nup155、Nup188 和 Nup205;中央通道包含 Nup54、Nup58、Nup62 和 Nup98;胞質絲包含 Nup88、Nup214 和 Nup358;核籃包含 Nup50、Nup153 和 Tpr。
3.1.1 結構支架
結構支架由 8 個相同的輻條(spoke)構成,它們圍繞 NPC 的中軸旋轉對稱排列,這一結構使每個輻條的彎曲剛度最大化,并穩定整個支架,防止結構扭曲變形。輻條呈放射狀連接形成平行于 NPC 赤道面的同心圓亞復合體,包括 4 個同軸的環狀結構:2 個外環分為位于胞質側的外環(cytoplasmic ring)和核質側的核環(Nuclear ring),位于 2 個外環之間的內環(inner ring),以及穿插于雙層核膜內部的腔環(lumen ring)。
內環是結構支架中結構最保守的單元,其組成蛋白由 N 端 α 螺旋或 β 螺旋、C 端 α 螺旋組合而成,這為內環結構的靈活性和可變性提供了基礎。內環直徑隨細胞能量狀態的改變在 40~60 nm 范圍內變化。研究顯示,在細胞能量耗盡和高滲透壓條件下,細胞核體積減小,核膜張力降低,NPC 內環直徑收縮至 40 nm。內環中央通道側,為富含苯丙氨酸(F)和甘氨酸(G)結構域(FG)的核孔蛋白提供了結合位點,游離于中央通道的 FG 基序構成了大分子通過 NPC 的重要選擇性屏障。NPC 通過腔環與核膜的結合,這一結合是通過插入細胞核磷脂雙層膜的兩親性短氨基酸序列(Membrane-binding motifs, MBMs)介導的。
外環的大小和構象在不同物種之間存在顯著差異,酵母 NPC 的外環直徑約為 98 nm,而人類的外環直徑約為 120 nm。如前所述,外環分別存在于核質和胞質側,分別連接核籃和細胞質絲。外環通過 MBMs 與核膜相連,并調節 ONM 和 INM 融合處的膜曲率。外環的核心結構為 Y 復合物,主要由 α 螺旋和 β 螺旋這兩種結構域構成,8 個 Y 復合物頭尾排列形成環狀結構。這些環狀亞復合體通過由部分核孔蛋白內在無序結構域構成的短線性基序網絡(short linear motifs, SLiMs)連接在一起。雖然單一 SLiMs 介導的相互作用較弱,但多重的相互作用也賦予了結構支架靈活性和完整性。
3.1.2 中央通道
中央通道是由結構支架包圍的直徑為 40~60 nm 的管道,分子通過中央通道進行核 - 質轉運和擴散。富含 FG 基序的核孔蛋白一端與結構支架相連接,另一端充滿中央通道在通道內自由擺動。無序的 FG - 核孔蛋白形成 NPC 選擇性屏障,允許特定的轉運蛋白通過。
在 NPC 中有 200~300 個含 FG 基序的核孔蛋白,它們共同形成了轉運體結構。由于 FG - 核孔蛋白的展開特性,它的整體形狀和內部密度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轉運體有 “開放” 和 “關閉” 兩種構型狀態,在這兩種狀態下,FG - 核孔蛋白分別聚集在通道壁附近或通道中心軸周圍。轉運體通過熱波動完成不同構象間的切換,并選擇性地允許分子通過中央通道。
FG - 核孔蛋白長度約為 0.43 nm,表現為具有高度柔韌性的聚合物,其柔性在調節選擇性分子運輸時起著關鍵作用。FG 基序本身是疏水的,可與核轉運受體(nuclear transport receptors, NTRs)產生疏水相互作用,但 FG 基序間隔區的存在可防止其相互聚集,有助于保持結構的無序性。雖然 NTR 每個結合口袋和 FG 基序之間的親和力較小,但由于相互作用位點和 FG 基序的多價性,可使它們的總體親和力增加 10³ 倍,使 FG-NTR 相互作用更加穩定。
3.1.3 細胞質絲和核籃
細胞質絲是由胞質環向細胞質延伸形成的絲狀結構,可以募集貨物運輸因子復合物并參與核 - 質運輸,協調信使核糖核蛋白顆粒的輸出和重塑,為翻譯做準備。對于細胞質絲的研究主要關注了組成細胞質絲的核孔蛋白,及其在神經退行性疾病、心臟疾病和癌癥等病理過程中的相關機制。
核籃與 NPC 支架相連接,是由核環側延伸出的纖維絲相互匯集形成的魚籠狀結構。在物質的核 - 質穿梭過程中,被轉運的物質必須通過核籃,因此這一結構在核 - 質運輸過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在高等真核生物中,核籃主要由三種核孔蛋白組成:位于籃狀結構底部的 Nup153、Nup50 以及包含四個卷曲螺旋結構域的 Tpr。
其中 Tpr 是纖維絲的主要組成部分,由跨越超過 1500 個殘基的巨大卷曲螺旋區域組成,這些殘基可以同源寡聚化,其次是一個高度酸性的 C 端區域,該區域大部分是無序的,而 NPC 靶向區域位于 N 端卷曲螺旋區域。Nup50 包含一個 N 端區域,一個中間的 FG 重復區域,以及一個 C 端 Ran 結合域,其中 N 端區域能夠介導與 Nup153 和入核轉運蛋白(Importin)-α 的相互作用。Nup153 包含一個 C 端的 FG 重復區域,以及 4 個與 Nup358 同源的 Ran 結合鋅指結構域,人類 Nup153 對于 Tpr 和 Nup50 在 NPC 中的定位是必需的,這表明 Nup153 將其他核籃組分錨定到 NPC 上。
3.2 NPC 介導的物質核 - 質轉運過程
構成 NPC 的多種核孔蛋白共同調節生物大分子的核 - 質轉運,參與染色質的組裝和基因表達的調控。一般而言,物質進出細胞核主要通過被動擴散和主動運輸兩種方式。分子量小于 40 kDa 的小分子可以通過被動擴散通過 NPC;隨著分子量增加,被動擴散逐漸減弱,大分子需要依賴于核定位或核輸出序列與特定 NTR 的結合而實現主動轉運。
NTR 核 - 質主動轉運由 Ran GTP 酶和 Ran 梯度維持。在細胞質中,Ran-GAP1 將 Ran-GTP 水解為 Ran-GDP,而在細胞核中,染色質凝聚調節因子 1 將 Ran-GDP 轉換為 Ran-GTP。這一過程形成了細胞核中高濃度 Ran-GTP 和細胞質中高濃度 Ran-GDP 的濃度梯度,從而為特定方向的主動運輸提供能量來源。
目前研究最多的是依賴 NLS 和入核轉運蛋白的蛋白質入核過程。在細胞質中,入核轉運蛋白 α 識別蛋白質的 NLS 進而與入核轉運蛋白 β 結合形成三聚體復合物,該復合物通過入核轉運蛋白 β 與 NPC 中央通道的 FG 基序相互作用通過 NPC。在細胞核中,Ran-GTP 與入核轉運蛋白 β 結合形成復合物,促進入核轉運蛋白 α、入核轉運蛋白 β 與含 NLS 的蛋白質分子解離。
蛋白質分子在細胞核內釋放后,入核轉運蛋白 β-Ran-GTP 復合體被重新輸出到細胞質;入核轉運蛋白 α 則需要在其它蛋白(如 CAS 蛋白)的輔助下被輸出到細胞質中,再用于下一周期的分子運輸。此外,有研究工作顯示部分蛋白質存在僅依賴入核轉運蛋白 α 或僅依賴入核轉運蛋白 β、甚至不依賴入核轉運蛋白的轉運機制,這些特殊方式往往與蛋白質特殊結構相關,其機理仍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
3.3 NPC 與機械信號轉導
3.3.1 NPC 的力學響應
Wolf 和 Mofrad 于 2009 年首次提出 NPC 結構和功能變化直接參與機械信號轉導過程。作為核膜上的分子轉運通道,NPC 促進響應機械信號的轉錄因子或轉錄調控相關因子的細胞核 - 質轉運,如心肌素相關轉錄因子(myocardin-related transcription factor, MRTFs)、Yes 相關蛋白(yes-associated protein, YAP)和細胞外信號調節激酶等。
目前關于機械力如何促進轉錄相關因子入核的機制主要分為兩類:一是在機械力的作用下 NPC 中央通道孔徑增加,從而降低了物質轉運的壁壘阻礙;二是由機械力引發的生化級聯信號改變了轉錄因子的構象,使得轉錄因子與 NTR 間的親和力增強,促進其入核輸運。
Elosegui-Artola 等提供了關于 NPC 拉伸與細胞核機械信號轉導相關的實驗證據。該團隊使用帶有 20 μm 球形尖端的 AFM 對細胞核直接施加 1.5 nN 的恒定力,誘導 YAP 易位到細胞核內,該過程的發生獨立于生化信號的調控,而核膜高張力引起的 NPC 孔徑擴張是 YAP 轉運效率提高的關鍵。
其它研究小組對 NPC 構象的觀測也支持了這一觀點。NPC 在收縮和擴張時顯示出不同的構象,收縮時 NPC 中央通道的直徑約在 40~50 nm,而擴張時其中央通道約為 55~70 nm。NPC 收縮和擴張構象的改變主要基于 NPC 內環的動態變化,而外環的結構幾乎不變。Zimmerli 等在單細胞中觀察到 NPC 在收縮和擴張狀態之間的轉變,并且證明 NPCs 在能量損耗或細胞外高滲環境下收縮,這兩種情況都會降低核膜張力。
在 NPC 參與的機械信號轉導過程中,除了內環的動態響應外,核籃的構象也隨機械信號的傳遞發生變化。研究表明,鈣離子濃度在靜電作用驅動下可以調整核籃結構和狀態,以實現遠端環狀結構的打開或關閉。此外,對細胞直接施加的機械力也會影響核籃構象。由于細胞核骨架蛋白 SUN1/2 與核孔蛋白 Nup153 的相互作用,機械刺激可通過 SUN1/2 傳遞給 Nup153,進而拉伸 Tpr 蛋白,誘導核籃結構的重組。有研究小組通過計算模擬揭示,在生理條件下,核籃的構象狀態可作為分子開關,將靜電作用和機械拉伸耦合。
3.3.2 機械響應信號分子的核 - 質定位
YAP 作為一種響應機械信號的轉錄激活因子,可在機械力的作用下實現核 - 質穿梭,但其通過 NPC 的具體機制仍存在大量未知。首先,YAP 的氨基酸序列中并沒有發現典型的 NLS 序列,而 YAP 的分子直徑(~65 kDa)大于 NPC 允許被動擴散尺寸的閾值,因此當細胞核膜上的 NPC 在機械力作用下擴張時,可能會引發 YAP 蛋白的被動擴散入核。
YAP 也可能通過非典型 NLS 序列與 NTR 結合,進而完成其核 - 質穿梭過程,然而這一假設仍需要更多的實驗數據支撐。此外,YAP 作為 Hippo 信號通路的下游信號分子,可以發生磷酸化、乙酰化、甲基化等多種翻譯后修飾,其自身構象的變化也會影響其通過 NPC 的動力學過程,但 YAP 不同翻譯后修飾與 NPC 互作的具體模式目前仍不清楚。
另一個決定 YAP 細胞核 - 質定位的重要因素是其與 Angiomotin(AMOT)家族蛋白的結合。AMOT 可競爭性結合 YAP 或 F-actin,當細胞受到機械力刺激時,細胞質中的 F-actin 濃度升高,招募 AMOT 并使 YAP 從 YAP-AMOT 復合物中釋放,隨后 YAP 進入核內。然而 AMOT 在 YAP 向核內運輸過程中的具體調控體制仍不清楚。
與 YAP 類似,MRTF-A 的核 - 質穿梭也受到細胞骨架的影響。MRTF-A 中的精氨酸、脯氨酸、谷氨酸和亮氨酸(RPEL)保守結構域含有 NLS,可通過與入核轉運蛋白 α 和轉運蛋白 β 結合通過 NPC,該結構域同時也是 G-actin 的結合位點。因此入核轉運蛋白和 G-actin 競爭性結合 MRTF-A 中的 RPEL 結構域。在無機械力刺激的條件下,細胞質中的 G-actin 與 MRTF-A 結合,而當機械刺激促進細胞骨架聚合從而使 G-actin 的濃度降低時,MRTF-A 可與入核轉運蛋白結合進入細胞核。
綜上,對于機械信號引起的物質跨核膜轉運過程,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 NPC 自身構象改變和機械力引發的生化信號兩方面。一方面機械力調控 NPC 自身結構和功能變化,另一方面,機械信號通過磷酸化修飾等方式調控轉錄因子和轉錄調控相關因子經 NPC 的核 - 質定位,最終影響核內基因表達。結合實驗數據和模型預測進一步深入探究 NPC 選擇性物質轉運的分子機制,有助于我們更好的理解 NPC 如何介導物質核 - 質轉運以及 NPC 在機械信號轉導過程中的作用。
4 染色質與生物力學
染色質作為遺傳信息的分子存儲裝置已被廣泛關注。細胞核內,染色質與細胞核骨架之間存在廣泛的物理連接,上述結構不僅維持著細胞核的結構穩定性,還調控著基因表達過程。近年來研究發現,染色質不僅是機械信號通過級聯生化反應調控基因轉錄的細胞核內執行單元,應力 / 應變還可以直接調控染色質構型在機械信號響應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本章從染色質的基本結構出發,介紹量化染色質物理構象的方法,進而探討染色質在細胞機械信號轉導過程中的關鍵作用。
4.1 染色質的基本結構與物理狀態
4.1.1 染色質的基本結構
在真核生物中,DNA 并非裸露存在的,而是纏繞在由核心組蛋白 H2A、H2B、H3 和 H4 組成的八聚體上形成核小體。核小體長度約為 1.9Å,由 147 個堿基對的 DNA 分子以左旋超螺旋纏繞組蛋白八聚體約 1.7 圈,核小體核心結構分子量約 225 kDa。核小體被進一步壓縮、凝聚成 30 nm 的染色質纖維,再進一步折疊形成染色質高階結構。
根據染色質的折疊程度與轉錄活性分為常染色質和異染色質。與常染色質相比,異染色質的堆積更為密集、轉錄活性更低且傾向于分布在細胞核周圍。在結構上,LADs 將核骨架蛋白組分核纖層與染色質聯系起來,細胞外機械刺激可通過 LINC 復合體傳遞至核纖層,進而通過 LADs 傳至染色質,影響染色質空間狀態和基因表達。除此之外,由于染色質是一種帶負電荷的聚合物,因此可以根據周圍環境的離子條件動態的改變局部結構,從而直接影響基因組在細胞核中的讀取方式。
4.1.2 染色質的物理狀態
不同課題組從不同尺度對染色質的構象和物理狀態進行了研究,得到了染色質的不同物理狀態,如液態、固態和凝膠態。染色質的物理狀態由自身固有性質(核小體組成、組蛋白修飾)和環境因素共同決定。
Gibson 等研究發現,直徑 100~200 nm 的染色質凝聚體表現為液滴狀,液滴之間可迅速融合,光漂白后熒光恢復實驗顯示熒光標記的核小體陣列在液滴中自由擴散,提示凝聚體中核小體可能通過液 - 液相分離的過程自組裝。Strickfaden 等的體外和體內研究表明,染色質進一步壓縮到 μm 尺度時以固體狀態存在,其特性可以抵抗外力并形成彈性凝膠,為染色質結合蛋白的液 - 液相分離過程提供支架。上述研究提示染色質凝聚物在不同尺度范圍的表現形式不同,在 nm 范圍內表現出液體特征,而在 μm 尺度上顯示出固體特征。
近年來,直接對染色質施加力并測量其物理性質的技術不斷發展,豐富了我們對染色質力學特性的理解。通過使用磁性顆粒,研究者對活細胞中染色質的納米力學性質進行了直接觀察,結果表明細胞周期間期的染色質為凝膠態。最近,Keizer 等構建了一種在活細胞核內用可控磁力主動操縱基因組位點的方法。該方法通過帶有四環素阻遏蛋白(TetR)的磁性納米顆粒與基因組四環素抗性操縱子結合,檢測到在接近 pN 力的作用下染色質出現的超過 μm 范圍的黏彈性位移,首次評估了活細胞內染色質對外力的響應情況。
通過這項技術發現染色質并非凝膠態,而是以液態形式存在。這一技術為未來從染色體力學到基因組功能領域的研究開辟了途徑,然而該工作是基于已知的基因組陣列實現的,對于基因組不同操作位點(異染色質或常染色質)的選擇可能會影響染色質狀態。因此,未來在不影響細胞核內基因組環境的基礎上,在不同細胞類型中評估染色質物理狀態非常重要。
4.2 染色質對力學刺激的響應
研究表明,細胞外的力學刺激可在幾毫秒內從細胞黏附位點傳遞到細胞核導致染色質 “拉伸”,并且力學刺激可激活細胞膜上 Piezo 1/2 等機械敏感離子通道觸發下游生化信號轉導。因此,染色質的力學響應是機械信號轉導調控基因轉錄的一個重要層面,其中,受到廣泛關注的是細胞外力學刺激通過 “細胞局部黏著斑 - 細胞骨架 - LINC 復合體” 直接將力學刺激傳遞至細胞核,進而引起染色質拉伸、調控基因轉錄。
汪寧教授團隊的研究提供了染色質對力學刺激響應的直接證據。例如,該團隊應用三維細胞磁力扭轉系統,通過精氨酸 - 甘氨酸 - 天冬氨酸包被的磁珠,對細胞表面施加局部應力。為實現活細胞中染色質拉伸的可視化,團隊使用了一種含有細菌人工染色體和穩定表達 EGFP-Lac 阻遏物(GFP-LacI)的中國倉鼠卵巢 DG44 細胞系,應用 GFP-LacI 與 LacO 的高親和力標記二氫葉酸還原酶基因(dihydrofolate reductase, DHFR),研究發現應力經由整合素、細胞骨架和 LINC 復合體傳遞至核纖層,隨后在 BAF 和 HP1 蛋白的作用下造成染色質的拉伸,并促進了 RNA 聚合酶 II 和轉錄因子的結合,最終上調了 DHFR 的基因表達。
在該團隊的另一項工作中,同樣使用三維細胞磁力扭曲系統對活細胞施加了大小為 15 Pa、加載頻率為 0.3 Hz 的應力。通過對 GFP 標記的 DHFR 基因所在的染色質結構域的形變程度量化以及有限元擬理論模型分析發現,細胞對大小相同但模式不同的應力(沿細胞長軸、短軸、長軸和短軸的平分線的應力)響應有所差異。應力沿細胞長軸施加而引起的染色質拉伸程度最低(5%),而沿短軸施加而引起的染色質拉伸程度最高(25%),沿平分線施加而引起的染色質拉伸程度中等(10%)。同時,DHFR 的基因表達水平與染色質拉伸程度呈正相關關系。上述研究工作提示,作用在細胞膜的力學刺激直接拉伸染色質、調控基因轉錄。
目前,染色質對力學刺激響應的大多數研究工作中,染色質的力學加載依賴于細胞骨架和 LINC 復合體的呈遞。由于缺乏在活細胞對染色質直接施加和測量力工具,限制了對染色質直接力學響應的深入研究,而前文 4.1.2 中提及的在活細胞核內用可控磁力主動操縱基因組位點的方法,實現了對細胞核內特定染色體和基因的力學測量,未來可能可以作為量化染色質力學響應的工具,進一步拓寬對染色質生物力學響應過程和機理的理解。
4.2.1 染色質對基底剛度的響應
眾所周知,基底剛度可以通過控制干細胞的基因表達模式調節細胞命運。間充質干細胞通過增加核膜張力響應細胞外基質剛度增加過程,通過抑制組蛋白去乙酰化酶上調組蛋白乙酰化,實現成骨細胞的命運決定。而另一項研究提示,基底剛度的升高導致組蛋白去乙酰化酶活性升高并誘導染色質的濃縮,使成纖維細胞轉化為肌成纖維細胞。這提示我們,在不同類型的細胞中基底剛度對染色質的調控方式有所不同。
在細胞感知基底剛度的過程中,人們普遍認為肌球蛋白 II(Myosin II)和 F-actin 在其中起重要作用。剛性基底可激活肌球蛋白 II,從而在細胞質中產生更大的細胞骨架應力,通過 LINC 復合體傳遞至細胞核,進而對染色質結構產生影響。Rabineau 等研究了上皮細胞的染色質在不同剛度基底上行為和狀態,染色質在 100~200 kPa 的基底上主要以常染色質的形式存在,當基底楊氏模量降至 50 kPa 時,部分常染色質向異染色質轉變。當細胞在軟基底(<10 kPa)上時常發生細胞溶解現象,導致染色質從細胞核中釋放,細胞死亡。進一步通過添加藥物抑制組蛋白去乙酰化酶,可以保持乙酰化組蛋白,從而維持常染色質的形式和保持完整的核膜及核周細胞骨架網絡。
基底剛度是影響細胞表型可塑性和染色質穩定性的關鍵環境因素,在調節表型變化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機械刺激被移除后這些表型變化仍持續存在一段時間,這種現象被稱之為機械記憶(mechanomemory)。染色質中組蛋白乙酰化程度參與機械記憶過程,在基底軟化后根據細胞在剛性基底上生長的持續時間表現出可逆或不可逆性。
不僅如此,當基底由硬向軟轉換時,干細胞通過轉錄因子產生對剛性基底的機械記憶。例如,在軟的聚乙二醇水凝膠上培養的間充質干細胞中,YAP/TAZ 和 RUNX2 的活性取決于之前在聚苯乙烯培養皿上的培養時間。此外,非編碼 RNA 也參與干細胞機械記憶機制。例如 miRNA21 在硬基底培養的間充質干細胞中積累,抑制 MRTF-A 表達,在轉移到軟基底 14 天后,miRNA21 依舊保持較高水平。當干細胞分化或成熟細胞被重編程為未分化細胞時,染色質結構和細胞核結構的長期變化也可能參與機械記憶。
最近的研究關注了組蛋白修飾誘導染色質重塑過程中的細胞機械記憶機制。Scott 等的工作表明,當軟骨細胞培養在高剛度基底上時,H3K9me3 定位于軟骨細胞的核膜附近,當軟骨細胞轉移到柔軟的 3D 培養環境時,核膜附近 H3K9me3 標記的染色質重塑會被保留,去甲基化酶 KDM4 可以部分破壞 H3K9me3 對于高剛度基底的機械記憶。
除基底剛度的刺激外,其它的力學加載方式也會引起染色質的機械記憶。例如,Rashid 等應用三維細胞磁力扭曲系統對活細胞局部分別施加大小為 15 Pa、持續時間為 2 min 或 10 min 的應力,撤銷外力后的幾十分鐘時間內,GFP 標記的染色質能夠保持被拉伸的狀態,并且這一機械記憶現象的維持時間與應力施加的持續時間成正比。深入的機制研究表明,通過整合素施加的局部應力可使染色質去致密化,并增加細胞核內染色質相關蛋白的遷移速率。有趣的是,使用 NPC 激活劑 Pitstop 2 可以消除這一機械記憶現象,而 NPC 抑制劑小麥胚芽凝集素阻斷 NPC 的運輸延長了機械記憶的持續時間,提示染色質的機械記憶與 NPC 的通透性有關。
染色質對力學刺激的響應過程以及染色質結構的變化在疾病發生發展過程中具有重要影響。例如,由基質剛度誘導的細胞核機械信號轉導驅動染色質重塑,因此,主動脈瓣狹窄患者的肌成纖維細胞的染色質比健康者的肌成纖維細胞的染色質具有更濃縮的結構。由于細胞外力學微環境是一個復雜體系,所以基底對細胞命運和行為的影響不僅涉及基底剛度,也包含基底的黏彈性、應力松弛等性質,這對體外模擬實驗的材料設計與選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更好地在體外復現體內生理、病理過程。
4.2.2 染色質對基底微拓撲結構的響應
基底微拓撲結構或微圖案通常被認為是不同于基底剛度的力學作用。基底微拓撲結構通過細胞幾何形狀影響染色質結構和功能,其潛在機制包括細胞骨架分布和排列的改變以及肌動蛋白依賴的應力各向異性。
研究人員使用具有微拓撲結構的基底改變細胞幾何形狀,通過全轉錄組測序揭示了細胞幾何形狀與基因表達的關系,細胞增大增加了基質合成相關基因的表達,而細胞與基底接觸面積的減少使參與細胞穩態的基因上調。有趣的是,在不同拓撲結構的基底上,細胞組蛋白去乙酰化酶 3 的核 - 質分布以肌動球蛋白依賴的方式調節組蛋白乙酰化。
微槽基底可誘導染色體在細胞核內的重新定位。在形態學水平上,1 號染色體從細胞核的中心位置向核周區域移動,表明 1 號染色體從常染色質狀態向異染色質方向變化。在基因表達水平上,在微槽基底上培養的細胞中,1 號染色體有最多的基因差異表達和最多的轉錄本下調。相反,18 號染色體的基因表達變化最少,19 號染色體上調的基因最多。
同樣使用微槽基底,Downing 等的研究表明,通過微槽基底可降低組蛋白去乙酰化酶活性和上調組蛋白 H3 甲基轉移酶的亞單位 WD 重復結構域 5(WDR5)的表達,導致組蛋白 H3 乙酰化和甲基化增加,促進成纖維細胞向間質上皮的轉變。另外,Morez 等使用平行的微槽基底來增強心臟祖細胞向心肌細胞的定向分化。在這項研究中,微槽基底能夠引起組蛋白 H3 乙酰化的增加,允許通過 “干性” 因子進行細胞重編程,并且微槽基底促進了心肌素泛素化,進而影響該轉錄共激活因子的翻譯后修飾過程。上述實驗表明,基底微拓撲結構通過改變染色質來調節細胞的命運和功能。
5 機械信號轉導過程中細胞核各組分的相互作用
細胞通過局部黏著斑與細胞外基質錨定,并將外部機械刺激通過細胞骨架 - LINC 復合體傳遞到細胞核。此外,在細胞外力學刺激作用下細胞骨架重新排列,通過 LINC 復合體將機械力傳遞到核纖層或 NPC 結構,從而影響染色質和 NPC 的結構。由此可見,在機械信號轉導過程中,細胞核內各組分并非單獨存在或發揮功能,而是以核纖層蛋白為核心各組分相輔相成、共同協作。在此,從核骨架與染色質、核骨架與 NPC、NPC 與染色質 3 個方面的相互作用對細胞核機械信號響應過程進行進一步解讀。
5.1 核骨架蛋白與染色質的相互作用
染色質結構和核內空間分布對基因轉錄的激活或抑制至關重要。一般而言,結構疏松、轉錄活躍的常染色質多位于細胞核中心,而結構緊密、轉錄抑制的異染色質則位于核周核纖層附近。異染色質的核周定位與 LADs 和核纖層的互作密切相關。LADs 富含抑制性組蛋白修飾,如 H3K9me2、H3K9me3 和 H3K27me3,一般不含活性染色質標記,如 H3K4me。
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核骨架蛋白調控染色質結構和核內定位以響應力學刺激,此外,核骨架和染色質之間的相互作用還可以調節細胞核的穩定性。本節介紹核骨架蛋白與染色質之間的相互作用,重點關注其對細胞核力學特性、染色質空間分布和基因轉錄的影響。
5.1.1 互作調控細胞核力學特性
染色質本身對細胞核剛度的貢獻有別于核纖層。染色質主要調節應變小于 30% 時的核變形,而這些小變形過程中核纖層發生結構和翻譯后修飾等改變,使得細胞核變硬以抵抗較大的核變形。
Lamins 蛋白在細胞核骨架與染色質互作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可以調節染色質流動性進而對細胞核的剛度產生顯著影響。Schreiner 等使用光鑷發現,INM 栓系因子(tethering factor)缺失使細胞核剛度變小,并且細胞核內染色質的遷移率和流動性增加。Progerin 蛋白(突變的 Lamin A 蛋白)累積導致細胞核外周異染色質和核骨架之間的連接缺陷,異染色質含量減少,細胞核剛度降低;同樣,Lamin B 的缺失也會減少異染色質的數量,從而使細胞核變軟。此外,核質中游離的 Lamin A 通過直接與 DNA 結合或通過 H2A/H2B 核心組蛋白與染色質交聯,從而限制染色質在細胞核內的擴散和移動。
5.1.2 互作影響染色質空間分布
雖然哺乳動物 Lamin B1/B2 和 Lamin A/C 在亞微米尺度上形成不同的交織纖維網絡,但是 Lamin B1/B2 和 Lamin A 的(未檢測 Lamin C)DNA腺嘌呤甲基轉移酶識別位點在全基因組范圍內非常相似。然而,對 HeLa 細胞中微球菌核酸酶(只降解核小體連接區 DNA 的核酸酶)消化的染色質進行染色質免疫共沉淀結合測序分析(ChIP-seq)發現,Lamin A/C 和 Lamin B 具有各自特定的 LADs 區域。上述兩種情況共同表明,不同 Lamins 蛋白可能與相同的 LADs 相互作用,但其作用頻率不同。
Gesson 等通過對富含常染色質和異染色質的樣品進行 ChIP-seq 測定發現,Lamin B1 主要存在于核外周與異染色質互作,而 Lamin A/C 分布于整個細胞核,也可與常染色質相互作用,并與染色質結合蛋白 LAP 2α 結合。
Lamins 蛋白的缺失可導致染色質重組和異染色質從細胞核骨架上脫離,Zheng 等結合高通量染色體構象捕獲(high-throughput chromosome conformation capture, Hi-C)與熒光原位雜交,揭示 Lamins 蛋白缺失導致小鼠胚胎干細胞中特異性 LADs 與核骨架脫離,脫離的 LADs 破壞了 LADs 和細胞核內部染色質的相互作用。總之,上述研究提示 Lamins 蛋白在染色質組裝和基因表達調控中發揮核心作用。
5.1.3 互作影響基因轉錄
應力誘導的基因表達變化可能是由染色質結構改變介導的,包括染色質可及性、組蛋白的拓撲結構和翻譯后修飾。機械刺激調控 Lamins 與 LADs 互作引起異染色質從細胞核外圍移至細胞核內部、增加 DNA 的可及性,通過調節染色質結構影響基因轉錄過程。例如,5 pN 的機械載荷在不到 30 s 的時間內可以誘導染色質發生解聚,從而導致被拉伸區域的轉錄增加。值得注意的是,持續機械負荷的效應反映了一種具有基因沉默效應的機械適應過程,這可能是一種負反饋機制。
數據表明,力對染色質的影響是時間、大小和細胞類型依賴性的。對培養的人類表皮干細胞施加 5%~40% 的周期性單軸拉伸 30 min,異染色質標志分子組蛋白 H3K9me3 水平下降,這種翻譯后修飾與異染色質濃縮和基因轉錄抑制有關,而異染色質的減少有助于細胞核軟化,通過核軟化的形式有效耗散機械能防止 DNA 損傷。如果這種機械拉伸持續數小時,細胞會垂直于拉伸方向排列,從而將細胞核的應變降至最低,使細胞恢復穩態。有趣的是,如果拉伸是雙軸的,細胞無法重新排列以降低應變,則 H3K9me3 水平降低,但另一種異染色質標記物 H3K27me3 代償增加。
從細胞黏附處傳遞到細胞核的機械力已被證明可在施力后數秒內立即導致染色質拉伸,而當這一機械力持續施加 1 h 后,染色質拉伸與機械敏感基因表達的激活相關。
作用在染色質上的力學刺激如何實現只激活某些特定基因的表達,這仍是一個未解決的關鍵問題,而核骨架蛋白與染色質互作調控的基因在細胞核內定位可能起到重要作用。例如,表皮分化復合體基因簇在未分化的表皮干細胞中沒有活性,此時基因座靠近核纖層的位置;在干細胞分化過程中,該基因座被證明更集中于細胞核內部,并激活相關基因表達。
通過 LINC 復合體對核纖層施加張力,對維持染色質的壓實和相關基因的沉默至關重要。在小鼠中,LINC 復合體中 SUN 蛋白的缺失導致細胞核的張力降低,增加了染色質的可及性引起表皮干細胞提前終末分化。此外,核骨架蛋白參與的細胞核剛度可能在應變引起的細胞特異性異染色質變化中發揮作用。例如,人腫瘤細胞系的 Lamin A 含量較低,因此核硬度和核膜張力也較低,它們對力誘導的異染色質標記分子 H3K9me3 消耗具有耐受性。
核內 actin 參與的染色質結構調控也影響基因的轉錄活性和表達水平。核內 actin 可能通過多種途徑調控基因表達:a. 核內 actin 存在于染色質重構復合物中;b. 核內 actin 與三種 RNA 聚合酶都有相互作用且影響 RNA 聚合酶的轉錄活性;c. 核內 actin 調控轉錄輔助因子 MAL 的活性;d. 核內 actin 影響長程染色質組織結構和 DNA 損傷修復。
此外,NPC 通過對 G-actin 的轉運將細胞核和細胞質的肌動蛋白動力學聯系在一起。研究發現,細胞內總 actin 約有 20% 分布于細胞核內,為維持 actin 在細胞質和細胞核之間的平衡,G-actin 不斷通過 NPC 穿梭于核 - 質之間,其中 Importin 9 和 Exportin 6 蛋白介導的細胞核主動轉運過程發揮了關鍵作用。胞質中的 F-actin 聚合可降低核內 G-actin 水平,進而導致 RNA 聚合酶 II 轉錄延長的減少,隨后 H3K27me3 在啟動子處積累導致基因沉默。
總之,細胞核內結構在基因調控中扮演著關鍵角色,通過影響細胞核的形態以及染色質的結構,參與應力 / 應變調控的細胞核功能和基因表達。然而,機械信號轉導過程中核內成分互作調控基因轉錄的具體機制和調控網絡仍不清楚,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5.2 核骨架蛋白與 NPC 的相互作用
細胞在高基質剛度的環境中,通過黏著斑 - 細胞骨架 - LINC 復合體的傳遞導致細胞核扁平化,從而拉伸 NPC,降低其對分子運輸的機械阻力,并增加小分子蛋白的被動核轉運和 YAP 的核輸入。然而,對于 NPC 的 3D 建模顯示,擴張或收縮構型的 NPC 均為圓形且顯示出相似的中央通道面積,似乎排除了中央通道在分子核 - 質轉運調節中的主要作用,并將 NPC 輸運能力的變化歸因于核籃的重排。基于這些證據,有研究提出基于 NPC 機械激活的新模型:細胞外機械刺激通過 SUN1 傳遞給核籃蛋白 Nup153,Nup153 拉伸另一核籃蛋白 Tpr,誘導核籃結構重組,而核籃結構的開啟或關閉引起物質進出細胞核更高或更低的通量。
細胞外機械應力調控的核籃構型變化受到 LINC 復合體的影響,其中 SUN1 和 Nup153 之間的相互作用在細胞的生理病理行為中起作用。Pull-down 實驗表明,SUN1 蛋白的 N 端和 C 端都參與了與 Nup153 相互作用,這一結果得到了免疫熒光的支持,GFP 標記的 SUN1 與 Nup153 顯示出共定位。進一步的研究發現,RNA 干擾 SUN1 或過表達 SUN1 突變體的細胞表現出 NPC 的聚集,這意味著 SUN1 是維持 NPC 在細胞核表面均勻分布的重要因素,而在 Nup153 缺失的細胞中,SUN1 的位置也發生了改變,進一步驗證了 SUN1 和 Nup153 的相互作用關系。
NPC 也可與核骨架蛋白中的核纖層蛋白質網絡結構相互作用。Nup153 的 N 端和 C 端都存在核纖層蛋白結合結構域,這些結構域具有與 Lamin A 和 Lamin B 的 Ig 折疊結構域結合的潛力。在人乳腺癌 MDA-MB-231 細胞中敲除 Nup153 使細胞核形態出現內陷,且 Lamin A/C 的熒光圖像呈點狀分布。進一步研究發現,Nup153 的敲除導致了細胞的極化缺陷且顯著降低了細胞的定向遷移速度。
NPC 還可以通過胞質絲 Nup358 介導有絲分裂中期微管 - 著絲粒的附著過程,在細胞間期 Nup358 通過其 N 末端區域與細胞骨架蛋白微管相互作用。過表達 Nup358 的細胞顯示出顯著的微管結構改變,包括微管的聚集和穩定性增加。NPC 與核內 actin 之間存在相互作用。核內 actin 可以調節 NPC 的通透性,影響細胞核內大分子物質的轉運和交換;同時,NPC 通過對 G-actin 的細胞核 - 質轉運調控核內 actin 含量。除此之外,NPC 還具有染色質結合區,通過與染色質結合發揮重要的染色質空間定位和基因轉錄調控作用。
5.3 NPC 與染色質的相互作用
除傳統的核 - 質轉運功能外,NPC 還通過與染色質的物理相互作用參與基因組調控,在癌癥和神經退行性病變等多種疾病過程中起重要作用。早期的細胞學觀察顯示,核內濃縮的異染色質主要分布于 INM 下層,但分布并不連續而是被部分疏松的染色質所中斷,而這些中斷位置與 NPCs 密切相關。酵母、果蠅、人類等多種生物中的全基因組測序揭示了核孔蛋白在基因調控中的作用。本節討論 NPC 與染色質中啟動子、增強子和其它結構的互作方式。
5.3.1 NPC 與啟動子互作
果蠅和哺乳動物細胞中的研究表明,核孔蛋白 Nup98 和 Nup153 與轉錄活躍的染色質區域相互作用,靶向一些活躍的啟動子,調控基因表達。例如,Nup98 與甲基相關結合域 2、Trithorax 反應元件和 WD40 結構域蛋白共同占據基因 Hph 和 CG10851 的啟動子區域,促進基因表達。游離的核孔蛋白還可以在整個細胞核空間中與染色質結合,并且這類互作主要發生在具有轉錄活性的開放染色質區域。
有趣的是,刪除 GAL2 的開放閱讀框并不影響活性 GAL2 與 NPC 的關聯。GAL1 基因與 NPC 的物理相互作用集中在啟動子上,這一相互作用需要 Gal4 激活,但不需要 SAGA 組蛋白乙酰化酶復合物,也不受 RNA 聚合酶 II 失活的影響。上述研究提示,NPC 與染色質的啟動子互作是由 DNA 元件引導的,不依賴活性轉錄。
5.3.2 NPC 與增強子互作
除了啟動子外,多個研究小組發現核孔蛋白還可以與增強子相互作用,尤其是 H3K27 乙酰化水平增高和多轉錄因子結合的超級增強子。例如 Nup153、Nup133 和 Elys 等多個核孔蛋白,在結腸癌細胞的連接增強子和致癌超級增強子中富集以促進基因轉錄。
基于 dCas9 的蛋白質組學方法也鑒定了核孔蛋白對增強子的靶向性,該方法通過 CRISPR/Cas9 系統分離 CRE 調節蛋白和遠程 DNA 的相互作用,結合 dCas9 捕獲和染色質相互作用分析表征了紅系細胞中與特定成簇增強子結合的蛋白質,除了已知的增強子功能調節因子外,還檢測到了高豐度的 Nup98、Nup153 和 Nup214。
在細胞分化過程中,核孔蛋白與增強子的相互作用也被證實是細胞命運調控的重要環節。對于神經祖細胞的全基因組分析表明,Nup153 和 Sox2 結合并共同調控數百個基因。Nup153 與基因啟動子或轉錄末端位點的結合分別與基因表達的增加或減少相關,而抑制 Nup153 表達可以改變染色質的開放構型,破壞 Sox2 的基因組定位,體外和體內均可調控膠質細胞命運。
5.3.3 NPC 與其它染色質結構互作
對于 NPC 相關的染色質結構和功能研究主要關注特定核孔蛋白對特定基因轉錄的調控作用。在酵母中進行的一項早期全基因組研究中,Nup2、Nup60 和 Nup145 等特定核孔蛋白表現出與 GAL1、GAL2、HXK1、INO1 等具有高轉錄活性基因的相關性,基因被激活后優先定位于核外周區域。
通過乳糖操縱子系統檢測核孔蛋白 Sec13 和 Nup62 與緊密折疊異染色質區域的靶向互作,發現核孔蛋白 Sec13 和 Nup62 導致凝結染色質解壓縮,這一實驗為核孔蛋白誘導染色質開放提供了重要證據。從機理上講,核孔蛋白誘導的染色質開放依賴核孔蛋白 Elys,并且需要依賴 ATP 的染色質重塑 BRM 復合物。線蟲中進行的研究確定了 Elys 的同源物 MEL-28 與 SWI/SNF 染色質重塑復合體之間的相互作用。少突膠質細胞中 Sec13 結構同源物 Seh1 也被發現與 Brd7 等染色質重塑因子的互作關系。Seh1 的缺失會誘導染色質的壓實,導致染色質可及性降低。另有研究發現,Nup98 與修飾 H3K4 的組蛋白甲基轉移酶之間存在相互作用。
核孔蛋白與染色質相互作用在轉錄記憶的分子機制中具有重要作用。通過轉錄記憶過程,之前激活的基因在經過一段時間的抑制后,在后續激活時會做出更強的反應。Nup98 同源物是不同物種特定基因的轉錄記憶和動態再激活所必需的,包括酵母中肌醇誘導的 INO1 基因和人體細胞中干擾素 -γ 誘導的基因。被干擾素 γ 誘導的基因再次受到干擾素 γ 誘導時表現出更強烈的反應,這種 “記憶” 效果可在細胞分裂 4~7 次后仍持續存在,且這一過程與 H3K4me2 和 RNA 聚合酶 II 的穩定結合相關,并需要與核孔蛋白 Nup98 的物理相互作用。
6 細胞核生物力學研究技術的進展
多種工具和平臺已被開發用于細胞核生物力學研究,如 AFM、微流控平臺、圖像處理算法輔助的細胞力測量技術、微 / 納米尺度操作的技術等。新技術和新方法的不斷突破為應力 / 應變的精準加載、細胞核力學特性的表征以及細胞核機械信號轉導過程的定量化描述提供了重要支撐,為全面理解細胞核生物力學機制提供了重要的平臺。
6.1 細胞核生物力學的主要檢測技術
6.1.1 AFM
1986 年,Binning 等為在原子分辨率下對非導體材料表面進行成像,在掃描隧道顯微鏡的基礎上發明了 AFM。AFM 的工作原理是基于激光測量懸臂偏轉實現對探針和樣品表面之間的作用力檢測,其基本裝置包括帶探針的微懸臂、懸臂偏轉傳感器、壓電定位器以及傳感器和定位器之間的電反饋機制。在力譜模式下,探針以可控的方式趨近樣品并退回,懸臂偏轉和懸臂位移被轉換成力與距離或時間曲線。
由于 AFM 對材料成像、探測和操作的靈活性,使其成為納米科學中常用的儀器。最初的 AFM 是在真空中運行的,Marti 等實現了 AFM 在液體環境和環境溫度下工作,推動了 AFM 向生物學的發展,并促進了生物分子和細胞在納米分辨率下的檢測和分析。
使用化學修飾的 AFM 探針對生物分子之間黏附力進行的測量,為生物系統的生化特性描述開創了重要技術平臺。AFM 探針可以探測非特異性或特異性的生物分子相互作用,包括生物大分子或受體和配體之間的相互作用。在單分子水平上,這種相互作用可以理解為多個協同作用的非共價相互作用的總和(如氫鍵、范德華力),并可以確定其穩定性和壽命。
基于 AFM 的單分子力光譜技術是目前測量分子內和分子間力的理想方法,具有高空間分辨率和力靈敏度(1 pN 到 100 nN),其優勢在于可以與高分辨顯微技術、拉曼光譜技術等先進技術結合,直接觀察和記錄單個分子的行為。例如,通過單分子力光譜技術追蹤單分子解離事件可以提供有關生物大分子(如蛋白質和核酸)之間相互作用的信息,從而增加我們對生物過程的認識。
AFM 對細胞核力學特性的表征由懸臂壓陷細胞實現。例如有研究使用帶有 6 μm 微球的懸臂對貼壁乳腺癌細胞的細胞核和細胞骨架進行了剛度測量,在 5 nN 條件下,人乳腺癌細胞 MDA-MB-231 細胞核的剛度為 157.7±78.55 Pa,明顯高于細胞骨架剛度(103.42±89.45 Pa)。Krause 等將 AFM 和共聚焦顯微鏡進行組合,在測量細胞核剛度的同時可視化了懸臂與核接觸的過程,并且對比了針形探針和球形探針的測量效果。與針形探針相比,球形探針的測量結果可重復性更強,該研究進一步使用 10 μm 球形探針在 0~1.5 nN 的條件下測得人纖維肉瘤細胞 HT1080 細胞核剛度在 270 Pa~2.29 kPa 范圍內。
然而,上述基于 AFM 的方法都是在細胞整體水平上對細胞核進行的測量,無法排除細胞膜或細胞骨架的影響。為解決此問題,Liu H 等使用聚焦離子束對 AFM 進行了改良,在不同基底上使用尖銳的針形探針穿透瓣膜間質細胞胞膜對細胞核力學特性進行原位表征,根據 AFM 壓痕曲線上的兩個不同節段確定細胞質和細胞核的剛度,并與共聚焦顯微鏡圖像同時重建進行相關性分析。其結果表明,軟基底(11 kPa)上的細胞核剛度(26.54±3.41 kPa)低于硬基底(聚苯乙烯)上的細胞核剛度(84.36±16.16 kPa),并且體外分離的細胞核剛度(9.29±1.80 kPa)明顯低于前文所述的細胞內原位細胞核剛度。
AFM 技術也用于探測染色質構象,可以實現對核小體尺寸和動力學的測量。Yamini Dalal 團隊在體外液體環境中重建了組蛋白 H3 的變體−著絲粒蛋白 A(Centromere protein A, CENP-A)核小體和 H3 核小體,AFM 結果顯示測量,CENP-A 核小體與 H3 核小體具有相似的尺寸,分別為 3.8±0.3 nm 和 3.7±0.3 nm。該團隊進而測量了核小體在 67.5 mM Na⁺,2 mM Mg²⁺條件下的彈性模量,該條件接近生理滲透壓和離子濃度。結果顯示單個 CENP-A 核小體的彈性模量為 18.5±15.6 MPa,是 H3 核小體(35.4±13.9 MPa)的一半;同時 CENP-A 和 H3 單核小體具有均勻的彈性模量分布,為均質圓柱體。此外,高速 AFM 用于可視化 CENP-A 核小體的自發動力學,觀察 CENP-A 核小體自發且可逆的構象改變。通過將 AFM 和光鑷結合,已發現 HMGB 蛋白能破壞 DNA 的穩定性并將其從 H2A-H2B 二聚體上解離,從而調節染色質的可及性。
總之,AFM 是測量細胞力學特性和細胞核力學特性的經典方法。AFM 的使用通常結合赫茲接觸理論、指數方程等一些數學理論等來綜合描述全細胞力學特性。隨著基于 AFM 方法的進一步發展,特別是在通量提高和多參數測量方面的發展,將有助于實現在微納尺度原位研究生物結構、力學特性及生理功能三者之間的關聯。
6.1.2 微流控技術
微流控技術是一種通過微孔道精確控制微尺度流體的技術,可在樣本量很少的情況下進行高靈敏度的檢測和分析。微流控技術最初應用于化學分析領域,起源于氣相色譜、高壓液相色譜和毛細管電泳的小型化和集成化。科學家們在此基礎上開發新的、更密集的、更通用的微尺度分析方法并尋求此類方法在生物和化學領域的應用。之后,PDMS 軟光刻技術、在軟光刻工藝的基礎上開發的氣動閥門以及基因組學快速發展,為微流控技術的發展提供了更精密的硬件支持和更廣闊的應用范圍。微流控技術已開始應用于蛋白質結晶條件篩選、藥物開發中的高通量篩選、細胞操作等領域,本節主要關注微流控技術在細胞核力學特性檢測方面的應用。
如前文所述,AFM 受限于研究通量低,無法在大樣本中快速檢測細胞核的力學特性。微流控技術的發展使研究人員能夠集成和開發用于細胞和細胞核力學測量的新型高通量系統,包括微陣列技術、微通道諧振器和細胞形變測量法。微流控技術為研究結構和機械約束條件下的細胞核力學響應提供了獨特平臺。
Anselme 等檢驗了表面拓撲和三維結構對細胞核的影響。不同類型的細胞在平整基底上培養時,其細胞核分布沒有明顯差異,而在微柱上培養的腫瘤細胞表現出特殊的可塑性,細胞核向下變形為 μm 級凹槽,并形成不同的凹面和突起。Nagayama 等基于聚二甲基硅氧烷微柱陣列的研究表明,正常的血管平滑肌細胞 Lamin A/C 的表達量升高,增加了細胞核硬度,增強了細胞核對細胞外微柱的機械抵抗能力也抑制了細胞的增殖。而 Hela 細胞的細胞核變形能力較強,微柱對 Hela 細胞的增殖抑制作用不明顯。該結果提示細胞變形能力與細胞核剛度相關,并且在不同的細胞類型中存在差異,因此核參數有可能作為疾病狀態評估的生物標志物或預測指標。此外,微流控裝置可以模擬生理環境中細胞外基質的孔徑尺寸以探測細胞通過組織和間隙的能力,通過與成像設備的結合對細胞遷移過程中細胞核形變程度進行定量測量。
微流控技術具有樣本量要求小、靈活性強、通量高、時空控制精確等突出優勢,已成為細胞核生物力學研究的重要工具。總體而言,它主要從三個方面支持細胞核生物力學的研究:(1)為培養的細胞提供明確的幾何約束、空間限制或納米形貌;(2)通過流動腔對培養細胞施加流體剪切力、液壓、拉伸力或膜張力;(3)通過設計特定的功能模塊形成集成平臺,在實現活細胞培養和機械加載的同時對其進行分子檢測和信號讀取。
微流控技術可以與抗光學漂白的半導體量子點相結合,開發基于量子點的活體熒光成像平臺,用于快速追蹤疾病標志物和分析復雜生物過程。另外,基于蛋白質檢測的微流控芯片顯示了其在基于體液的疾病診斷中的潛力。
6.1.3 微吸管
1954 年,Mitchison 和 Swann 開發出微吸管技術研究海膽卵膜的力學特性。該方法通過施加負壓將細胞的部分區域吸進微管,測量吸入微管的細胞形狀,并使用適當的數學模型來確定細胞的力學性能。通過對負壓的控制,細胞變形及其幾何參數變化可被具體量化以確定彈性或黏彈性特性。其中,表征不同細胞組分的力學性能需要不同大小的壓力,小尺度的延伸可提供細胞表面的力學參數,大尺度的延伸可對細胞骨架和細胞質成分進行測量,例如測量細胞膜和細胞骨架時分別需要 1 Pa 和 1 kPa 的閾值壓力。
采用微吸管技術,Rand 和 Burton 將紅細胞膨脹成球形,測量膜的彈性模量,Waugh 和 Evans 在紅細胞的自然狀態下測量紅細胞膜的剪切彈性模量。在微吸管研究活細胞力學行為時,Hochmuth 結合基本連續體模型對測量結果進行了解釋,從而得到細胞的彈性和黏性等參數。其中,中性粒細胞表現為液體性質,其表面張力約為 30 pN/μm,黏度約為 100 Pa・s,而軟骨細胞和內皮細胞表現為固體性質,彈性模量約為 500 pN/μm²(0.5 kPa)。
微吸管也可應用于細胞核力學特性的測量,研究分離細胞核的流變性質、特定核膜蛋白對細胞核力學性質的影響、干細胞分化不同階段的細胞核變形等。Rowat 等通過熒光標記了染色質和核仁成分,并通過微吸管抽吸核膜以研究細胞核的物理性質。在抽吸過程中細胞核體積減少了 60%~70%,并且 Emerin 蛋白缺失的細胞核中面積擴張與剪切模量的比值顯著降低。
Pajerowski 等使用微吸管研究了人胚胎干細胞分化過程中的細胞核力學特征變化,將細胞核形變與細胞膜形變的比值(Lnuc/Lcell)作為衡量標準,結果發現細胞核在分化過程中高度變形,Lnuc/Lcell 比值由 > 0.8 降至 0.15,硬化 6 倍左右。未分化干細胞和 Lamin A/C 敲低細胞的細胞核也表現出更多的流動性,而在持續的應力作用下,細胞核表現出更像固體的弱冪律流變學。
微吸管技術為細胞或細胞核的流變學特性測量提供了重要方法,該技術的吸力范圍從 10 pN 到 100 nN,其測量范圍是其他技術無法比擬的。微吸管技術可以測量非常軟的物質的彈性和黏性,以及不同細胞器和整個細胞的機械性能,其準確性與 AFM 相當。未來,微吸管技術可能與微流控技術集成,實現相對高通量的測量,并降低儀器和測量程序的復雜性。
6.1.4 布里淵光譜法
布里淵于 1922 年首次報道了聲誘導的非彈性光散射,而自發布里淵散射是光在晶體中遇到聲學聲子時的非彈性散射,可以確定聲子的能量,從而確定與散射材料的黏彈性密切相關的原子間勢。布里淵光譜法是一種基于自發布里淵散射的研究手段。與超聲等檢測不同,布里淵光譜不需要施加外力,可以非接觸地直接讀取材料的黏彈性特性,被廣泛用于材料表征、結構監測和環境感知。
2008 年,Giuliano Scarcelli 和 Seok Hyun Yun 展示了一種基于完全平行光譜儀的共聚焦布里淵顯微鏡,比以往方法的檢測效率提高了近 100 倍,促進了布里淵顯微鏡在生物醫學和生物材料科學中的多種應用。利用 3D 布里淵光譜顯微鏡在亞 μm 分辨率下研究細胞內的異常相變,已揭示了神經退行性疾病肌萎縮側索硬化的致病機制。作為互補的技術,基于接觸的 AFM 和非接觸的布里淵顯微鏡被用于確定反芻動物視網膜的機械特性。此外,還建立了光學相干斷層掃描引導的布里淵顯微鏡,用于繪制小鼠胚胎組織顱內神經管閉合過程中的原位生物力學圖譜。因此,布里淵光譜顯微鏡可以滿足從亞細胞水平到組織水平的多尺度生物組織力學表征。
布里淵顯微成像光譜儀(如 VIPA)的光譜分辨率約為 500 MHz,利用受激布里淵效應,可將之前的光譜分辨率提升至 100 MHz,但這種方式使用的連續激光照明沒有充分利用受激過程的非線性效應,而且所需的高照明功率為 265 mW,限制了在長時間內用于敏感樣品的實時成像,這可能阻礙了其在生命科學中的更廣泛應用。最近多個合作團隊提出利用脈沖的泵浦探測方案將受激布里淵顯微技術所需照明光功率降低 10 倍。脈沖照明方案降低了受激布里淵顯微鏡的光毒性,并可對線蟲胚胎、斑馬魚幼體和類器官等生物樣品的力學特性進行成像。在細胞核生物力學研究方面,已有研究將布里淵光譜技術與微流控技術相結合,利用光散射作為測量核力學特性的參數,提供了一種非接觸和高靈敏度的檢測細胞核剛度的方法。
6.1.5 光鑷、磁鑷技術
Ashkin 通過理論計算推測聚焦的激光能推動 μm 級的粒子,并成功使用激光束將懸浮在水中的 μm 級乳膠球沿著光軸方向推動。Ashkin 等首次證明了單光束光鑷,即只需要一束高度聚焦的激光,就可以形成穩定的能量阱能將微粒穩定捕獲。在隨后的研究中,光鑷被證明可用于捕獲和操縱細菌及紅細胞,以及細胞內的細胞器。光鑷也產生位移的變化,伴隨產生的力和力矩對感興趣的生物大分子進行檢測,如 DNA、肌動蛋白、微管和分子馬達。
磁鑷的工作原理與光鑷類似,也是基于外力操縱微粒而來,兩者的不同在于磁鑷是通過磁力作用于磁珠實現力的施加,并且磁鑷可以避免光鑷引起的光損傷。Crick 和 Hughes 通過磁力拖動、扭轉和刺激細胞內的磁性粒子,首次展示了磁鑷的作用。此后 Smith 等使用磁鑷對單個 DNA 分子進行了單分子操作,他們將 DNA 分子的一端鍵合到玻璃表面,另一端連接到磁珠上,通過磁場調節磁珠的位置,在磁力已知的條件下獲得了力與單個 DNA 分子伸長的曲線。之后該技術被廣泛使用,并被稱為單分子磁鑷。
在磁鑷使用過程中,通常選擇 μm 級別的超順磁珠,并將 DNA、RNA 或核小體纖維連接在磁珠上,通過外部磁鐵的定位和旋轉拉伸和卷曲分子。磁鑷的使用大大拓寬了科學家對 DNA 力學特性的認識,也加深了我們對聚合酶、解旋酶、拓撲異構酶等活性分子的理解。此外,由于在細胞轉錄、復制和重組的多個過程中存在扭矩,并且細胞有復雜的機制來調節 DNA 的超螺旋,因此磁鑷在解決上述生物過程相關的問題中是一個有力的工具。
在使用光鑷和磁鑷技術對細胞表面施加力學刺激時,通常需要對微粒進行精氨酸 - 甘氨酸 - 天冬氨酸序列的修飾,使其與細胞整合素等細胞黏附受體結合,進而通過光或磁力調控微粒,對細胞表面施加應力。此外,光鑷和磁鑷技術在表征細胞核力學特性中也有廣泛應用。通過光或磁力捕獲和操縱微球等裝置對細胞核或核內分子在 nm 級精度和 pN 分辨率下精確地施加拉伸或擾動。
Meijering 等使用光鑷以 0.2 μm/s 的速度拉伸染色體,同時記錄了力 - 伸展曲線。在 10~50 pN 的作用力下,單個染色體表現出近似線性的伸展,而在強作用力下染色體表現出明顯的非線性硬化。相比于 AFM,光鑷或磁鑷可以直接對細胞核進行探測,而不會激活細胞膜介導的機械轉導。例如,有研究小組將 1 μm 乳膠珠注射到受精卵中,并通過光鑷實現了對細胞核流變性的測量。
磁鑷可被用來探測重組染色質纖維的結構,通過對力延伸數據擬合統計力學模型,可以推斷出不同染色質纖維的高階結構。另外,有研究使用磁鑷追蹤有無 NFIB 的單核小體的結構轉變,以研究 NFIB 如何影響核小體動力學。在實驗中,單核小體被重組到含有單一 Widom 601 序列的 409 bp DNA 片段上,分別將 DNA 的兩端與蓋玻片和順磁珠特異性連接,之后持續施加張力直至 30 pN,并記錄單個核小體的實時軌跡。在 NFIB 存在的情況下,核小體在大約 5 pN 的力下被完全分解,并在磁鑷的重復拉伸測量中保持展開狀態,而在沒有 NFIB 的情況下,核小體顯示出不可逆的兩步展開動力學,這與之前的報道一致。
一項同時運用光鑷和磁鑷的研究從拓撲學的角度探究了 DNA 復制過程,發現染色質纖維如何纏繞決定著染色質獨特的機械性能。這類精細化的機械力加載平臺對于細胞核及染色質的機械信號轉導的研究具有巨大潛力。
光鑷和磁鑷可以在不直接接觸細胞的情況下測量細胞的力學性能,并能夠與微流控等技術結合,實現對單個細胞的高精度和相對高通量的操作和測量。因此,它們在發展單細胞培養、操作的自動化平臺方面顯示出巨大的潛力。然而,加載在光鑷和磁鑷上的力學范圍過小,限制了其進一步應用,仍需要進一步改良。此外,改良的技術可用于測量軟材料在非線性狀態下的局部黏彈性響應,并用于研究活細胞的力學特性。隨著磁珠控制技術的進步,該技術可以更全面地實現細胞力學表征,如同時測量細胞表面和細胞內部的力學特性。
綜上所述,AFM、微流控技術、微吸管、布里淵光譜和光鑷、磁鑷等技術在包括細胞核在內的細胞組分力學性能測定中具有重要的應用。不僅如此,上述方法還是細胞生物力學研究中重要的力學加載手段,可用于對細胞整體或不同亞細胞結構施加精準、可控的機械刺激,在整個生物力學研究領域內具有廣泛用途。例如,AFM 通過在納米尺度上探測物體表面的力和位移,并且可以以非侵入的方式精準施加應力,在細胞表面和細胞整體尺度上測量細胞的形變和力學特性;同樣,AFM 也可以在聚焦離子束的輔助下穿透細胞膜,直接對細胞內部組分(如細胞核)的力學特性進行測量。另外,光 / 磁鑷等技術應用光學力 / 磁場對細胞整體施加應力,并根據力與位移關系對細胞的力學性質進行量化;而通過顯微注射的方式將納米微粒注入細胞,在光 / 磁力的控制下可以精確地操控和拉伸微小的細胞內結構,對細胞內部組分進行力學性能研究。這些力學加載技術平臺提供了多種手段來施加精確、可控的力學刺激,為深入理解細胞的力學行為和相關生物學過程提供了有力支持。
6.2 基于顯微成像的檢測技術
顯微鏡是細胞生物學相關研究不可或缺的工具,可以在單細胞水平實現不同時空分辨率的形態和結構檢測。在細胞核生物力學相關研究中,不同分辨率的顯微鏡常用來顯示染色質的結構和核內分布。
6.2.1 顯微成像技術概述
早期普通光學顯微鏡被用于哺乳動物的細胞核成像,在醋酸洋紅等堿性染料的結合下顯示出不同細胞周期的染色體形態。然而,由于阿貝極限(水平極限約為 200~300 nm,垂直極限約 600 nm)的存在,光學顯微鏡的分辨率約為 250 nm,因此在顯示精細結構時受到限制,而先進顯微成像技術的發展為進一步解析染色質的高階結構提供了可能。
電子顯微鏡是基于電子光學的原理,以電子束替代光束作為照明源,通過電子對樣品進行透射或反射來產生樣品表面的圖像。Robinson 等通過電子顯微鏡顯示了由組蛋白 H1 連接的串珠狀結構,以及核小體陣列纏繞形成的更濃縮的染色質纖維。另外,對于 30 nm 的染色質纖維結構的觀察通常通過掃描電子顯微鏡、透射電子顯微鏡或冷凍電鏡。
電子顯微鏡原位雜交(Electron microscopy in situ hybridization, EMISH)將電子顯微鏡技術與核酸原位雜交技術結合,可以在高分辨率下定位具體的核酸序列。例如,通過 EM-ISH 使用生物素標記的 DNA 探針結合二氨基苯丙胺染色已被用于細胞核中染色體 DNA 的成像。
另外,X 射線晶體學方法也可以用于 DNA 的結構解析,其基于電子對 X 射線的散射作用,獲得晶體中電子密度的分布情況,再從中分析獲得原子的位置信息。2002 年,Davey 等通過 X 射線晶體學在 1.9Å 的分辨率下確定了含有組蛋白和 147 bp DNA 的核小體核心顆粒的結構。
6.2.2 超分辨顯微成像技術
自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科學家們一直在尋求突破傳統光學顯微技術限制的方法,直到 2009 年逐步形成了成熟的超分辨熒光顯微成像技術,并獲得 2014 年諾貝爾化學獎。由于超分辨成像技術種類較多,本節結合細胞核和染色質方面的應用,只選取了 2 種具有代表性的技術對其成像原理進行介紹,具體為 Gustafsson 于 2005 年發明的結構光照明顯微鏡(structured illumination microscopy, SIM)和 Hell 于 1994 年發明的受激發射損耗顯微技術(stimulated emission depletion, STED)。
SIM 通過使用結構化光模式照亮樣品從而超越衍射極限,在莫爾效應的影響下,SIM 將傳統熒光顯微鏡丟失的高頻信息移入到可被檢測的低頻區域,而后通過后續的算法優化和處理將其中的高頻信息進行恢復,重建圖像中準確的細節從而提高成像的分辨率。
劉中乾;齊穎新,上海交通大學生命科學技術學院力學生物學研究所,202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