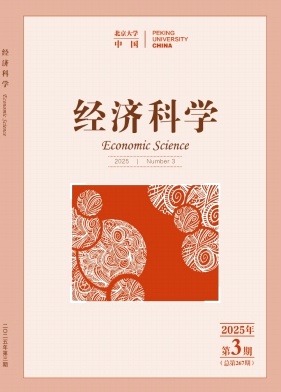經濟科學雜志投稿格式參考范文:輪船航運與市場整合來自晚清中國的證據
時間:
一、引言
19 世紀以來,輪船、鐵路、電報等現代交通和通信工具的發明和引進,大大降低了交通和信息成本,推動了國內外的貿易和專業化,既提高了國內市場整合程度,也成為經濟全球化的重要推動力量。作為這一潮流的重要組成部分,清末中國的國內市場整合也隨著這些技術的引進和推廣大大改進了。其中,以蒸汽為主要動力的輪船大大提高了內河航運的效率。和傳統的木帆船運輸相比,輪船的載重量較大,運輸時間較短,且通航時間較少受到天氣和水文條件的限制,因此平均運費較低,從而大大降低了貿易成本。然而,關于輪船引進對市場整合影響的實證研究還付之闕如,一些重要的實證問題還有待回答,比如輪船影響的地理范圍有多大,其影響是否異質于不同的市場規模。此外,一個對因果識別的挑戰在于動力輪船的引進過程基本同步于通商口岸的開設,難以區分交通成本下降和制度成本下降所帶來的影響。相比而言,鐵路和電報的引進有一定的外生性,關于其對市場整合影響的實證研究較為充分。
本文利用 1872—1911 年長江中下游 5 個省 65 個府的上等米的月度價格數據,將清政府在《馬關條約》簽訂后開放輪船的內河航運作為外生沖擊,采用雙重差分法來分析長江支流輪船航運的開通對市場整合程度的影響。1895 年之前,帝國主義勢力通過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逐步獲得了輪船在長江中下游干流宜昌以下的航行權,但長江支流不允許輪船通航,使得原本在長江干流運營的木帆船被排擠進入支流運營。隨著 1895 年 4 月《馬關條約》的簽訂,清政府放開了輪船在內河通航的禁令,長江支流也允許輪船通航,且航行權不限于外國輪船和中國官辦輪船。很快,以本土私人資本為主的中小型輪船公司進入了長江支流的航運市場,成為糧食等大宗貨物運輸的重要力量。對于因果識別非常重要的一個事實是,《馬關條約》中長江支流各府并沒有新開通商口岸,因此這些地區可以被視為受到了純粹的航運技術沖擊,而并未受制度成本變化的影響。因此,我們的實證研究把長江支流上被同一條河流連接的府對視為實驗組,其他府對視為對照組。
我們發現,1895 年 4 月之后,長江支流輪船航運的開通令使得同一條支流上的府對之間市場整合程度上升,從而這些府對間的糧價差異降低了 4.65%,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這一時期長江支流實際糧價差異下降的 37.11%。我們通過平行事前趨勢檢驗、匹配更可比的對照組、控制其他貿易成本、更換對照組、更換市場整合程度的度量、更換輪船通航的度量、安慰劑檢驗以及排除通商口岸的影響等一系列檢驗證明了結論的穩健性。
我們進一步探討了輪船航運影響的機制和異質性。第一,輪船航運只對具備通航條件的長江支流起到促進市場整合的作用,且該效應在這些支流的下游府對和崎嶇度較低的府對更大。這一方面進一步證明了相對于其他地區長江支流市場整合的改進是來自航運技術引進帶來的貿易成本下降,另一方面也說明在這一時期的航運技術條件下,地理因素限制了輪船航運的輻射范圍。第二,長江支流輪船航運的開通對于運輸距離更長和貿易規模更大(人口規模較大和存在貿易互補)的府對影響更大。這表明輪船技術的應用存在固定成本和規模經濟,只有兩地之間的運輸航程和貿易規模足夠大,輪船的應用才是有利可圖的,才能夠促進貿易擴大和市場整合。
本文對兩支文獻做出了貢獻。第一支文獻是中國歷史上的市場整合。一系列研究不僅聚焦于現代交通和通信技術引進對信息成本和運輸成本的影響,而且還關注制度變革所引發的交易成本的變化。和既有文獻相比,本文聚焦于現代航運技術相對于傳統航運技術的影響,而非制度沖擊或貿易線路改變所帶來的影響。特別地,輪船和鐵路的比較豐富和深化了我們對技術變革影響市場發展的認識。本文的發現在數量上與顏色和徐萌(2015)類似。另一方面,從網絡外部性的角度來看,輪船的應用依賴現有的水運網絡,而鐵路則是從零開始,在其初始建設階段 “獨木難成林”。兩相抵消,使得兩者對市場整合的經濟效應類似。
另一支文獻是輪船運輸對貿易發展的影響。與上述研究相比,本文由于數據所限,并未直接估算輪船對貿易成本和貿易規模的直接影響,也沒有探討貿易航線和貿易格局的改變,而是估測了輪船在貿易路線給定的前提下對地區間市場整合的影響。此外,本文強調了地理通航條件和地區間潛在貿易規模的作用,論證了技術沖擊和上述條件具有互補性:只有在地理條件具備和兩地之間的貿易規模足夠大的前提下,輪船運輸才會對貿易和市場整合產生影響。
二、歷史背景
采用蒸汽機作為驅動設備的輪船發明于 1807 年。輪船第一次出現在中國領海的時間是 1830 年,當年 3 月一艘叫做 “福士號” 的輪船拖帶一艘三桅鴉片帆船 “杰母茜娜號” 從印度戴蒙德港啟航,于 4 月 19 日 “抵達珠江口外的伶仃洋”。在鴉片戰爭之前,西方國家就已經開始利用這一新式交通工具進行較大規模的貿易。與作為傳統航運工具的木船相比,輪船對于自然條件的依賴程度更低、運力更大、運速更快、成本更低、安全性更高。輪船的發明極大地便利了大規模產品的運輸,在潛在巨額利潤的驅使下,西方國家希望能夠在中國獲得更多的領海和內河航權以傾銷鴉片和工業品以及掠奪初級農業產品。貿易潛力大且水文條件優越的長江流域自然而然成為西方國家的重要目標,在他們直接和間接的推動下,輪船在長江流域的通航從干流展開并逐步擴展到支流。
(一)輪船在長江干流的展開:1860—1895 年
早在 1854 年,羅伯特・麥蓮(Robert McLane)的方案中就已經提出了對于長江通航的要求,但他們不能確定中國是否會開放長江航權、開放的河段及形式。借由廣西西林縣馬仲農神父被殺案,英法兩國強迫清政府承認 1858 年《天津條約》和《關稅協定》以及 1860 年的《北京條約》,并獲得了遠超期望的特權,其中包括在開放的通商口岸之間通行輪船。19 世紀 60 年代,長江一帶戰況激烈,外國輪船在通商口岸有著航行特權、武裝保護、船大航速、來去自由等優勢。1867 年之后,帝國主義擴張航權的野心日益膨脹,在《天津條約》的修約活動中提出了更多關于新增口岸、增加鄱陽湖行輪特權、增加川江行輪特權等要求,逐步獲得了長江干流(宜昌以下)的輪船通航權。此外,以輪船招商局(1872 年成立)為代表的中國的官辦輪船公司也加入了長江干流的航運市場。
長江流域的長距離貿易在清代已經發展到了相當高度,糧食、棉花、木材及其他土貨的貿易活動十分頻繁。在輪船尚未深入內河之時,木船是中國內河水運的主要工具。1858 年長江干流輪船通航以后,木船在大江中完全無法承受來自輪船競爭的沖擊,干流上原有的將近 16000 只大中型帆船有 “數千艘帆船被逐入支流”。到同治年間,已經發展到 “長江輪舶橫行,價賤行速,民船生意日稀,凋零日甚” 的地步。輪船逐漸取代了木船在糧食運輸中的地位,大大降低了長江流域的長距離貿易的運輸成本。不過,需要指出的是,這一時期長江干流上的輪船通航與長江干流的通商口岸開埠基本同步,很難厘清通商口岸帶來的市場整合效應有多大程度來自制度的改善,有多大程度來自港口等基礎設施的改善,有多大程度來自輪船帶來的運輸成本的下降。
一個可能會影響識別策略的問題是,在 1895 年以前中國本土私商已經在長江支流運營輪船運輸。太平天國戰爭期間,華商就觀察到輪船航運的利潤,因此向洋行投資或者自購輪船交由洋商代理。19 世紀 80 年代后,有些地區沖開部分政治缺口,創辦了一些內港小輪船航運企業,但仍不成規模。
(二)輪船進入長江支流:1895—1911 年
1895 年,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戰敗,被迫簽訂《馬關條約》,日本在輪船航運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特權,包括新開商埠和擴大輪船通航范圍,把外國侵奪的長江航行權從宜昌延長到重慶,而且打破了外國輪船不得駛入長江以外的內河的限制。日本獲得的新的內河航運特權,因 “利益均沾” 條款為各國侵略者所享受。同時,“公車上書” 中提出的立國自強之策要求準許商人在內河通航輪船,部分官員也提出要興辦各項近代實業。清政府迫于多方要求,電令各省督撫,準許 “內河行小輪以杜洋輪攘利”。自此,華商在內河通航輪船的禁令逐步松動,輪船可以自由進入內河航運市場。
長江流域河網稠密,絕大多數支流適合輪船通航。在內河通航輪船的禁令放開以后,輪船航運業迅速發展。從 1895 年到 1911 年,在中國注冊的本土輪船只數和噸位大幅上升。具備輪船通航條件的長江支流也出現了輪船取代木船的情形 —— 不僅在宜昌、漢口、九江、沙市等可以向支流通航的通商口岸出現,而且在尚未開埠的其他地區也有出現。
輪船航運深入大河支流的內河航運,降低了貿易成本,擴大了貿易規模,進一步推動了農產品的商品化和地區生產的專業化。
(三)輪船通航的先決條件:地理條件和貿易潛力
除政治條件外,輪船運輸的大規模采用還取決于兩個條件:一個是通航條件,比如長江支流的水文特征、河道形態等因素會影響輪船的航行安全、運輸效率和成本;另一個是市場條件(即府對之間的貿易潛力),比如地區間的人口規模和專業分工模式會影響貿易潛力,決定輪船航運的市場需求和發展空間,只有在貿易潛力大的地區之間經營輪船運輸業務才有利可圖。
就水文條件而言,長江不同支流的通航條件不盡相同。我們的樣本中包含烏江、沅江、資江、湘江和漢水五條支流,其中漢水的水文條件較好,便于輪船通航。我們從海關出版的《<內河行輪章程> 項下華洋輪船行駛內港名錄》獲取了關于湘江、沅江、資江的輪船通航條件的直接證據。近代長江流域輪船管理權長期由海關把持,海關將輪船行駛內港的具體地點和時間記錄在了《內港名錄》當中。我們整理了記載的湖南開放的行輪內港,發現湘資沅澧四大支流均有行輪內港開放,尤以湘江最多。這為湘江、沅江和資江適合輪船通航提供了證據。至于烏江,根據王軾剛(1993)的說明,烏江河段地質條件差、谷深水急,在 1877 年整修航道之后也僅能維持木船通航。
就市場條件而言,輪船航行活動在貿易潛力更大的城市之間更為頻繁。單次輪船航行有更高的固定成本,因此,輪船的起步運價較高,經營者會選擇在貿易規模較大的城市之間承攬運輸業務以降低單位商品的運輸成本。經營者更傾向于每次航行充分利用運力,這要求運行的航線連接的城市有著足夠的貿易規模。
三、數據來源、變量構造和識別策略
(一)數據來源
糧價數據
各府上等米的月度價格數據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整理的《清代道光至宣統間糧價表》。出于掌控糧食供需狀況以保持社會穩定和財政預算、考核和報銷的需要,清王朝建立了糧價奏報制度。這一制度自康熙朝開始,于乾隆朝定型。乾隆年間(1736—1795 年)逐步確定了糧食奏報的各項要求(包括奏報時間、奏報清單獨立、奏報內容、奏報程序等),統一地方奏報糧價單格式,此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朝覆亡前后(1911 年)。這一數據的數據質量已經得到了大量研究者的認可,因此我們得以利用各府逐月的上等米價格數據來測度府對之間的市場整合程度。
歷史地理信息
我們的地理數據主要來自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冊》和哈佛燕京學會提供的中國歷史地理信息系統(China Historic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CHGIS)。我們使用的清代行政區劃以 1820 年以來的行政區劃為基礎。我們根據 CHGIS 提供的 1820 年的府級行政區劃和河流數據來識別長江中下游流域內的府級單位與長江中下游流域內重要支流的地理位置關系。
樣本范圍
本文研究樣本的地理范圍包含了在長江中下游流域有糧價數據的 5 個省份 —— 湖北、湖南、貴州、安徽、江蘇的 65 個府(江西和浙江缺乏上等米價格數據)。選定這一區域作為樣本地理范圍主要是基于長江不同區域支流的輪船通航條件:長江幾條重要的一級支流主要分布在長江中下游,這些一級支流具備供輪船通航的水文條件;長江上游的干流和支流水流湍急、險灘眾多,不能為輪船通航提供便利。
本文選擇 1872—1911 年共 462 個月作為樣本期的原因是,本文的實證設計是以長江支流府對作為實驗組,長江干流府對作為部分對照組。為了保證了該對照組在樣本期內始終允許輪船通航,本文采用輪船招商局成立的 1872 年作為樣本起始年份,這標志著長江干流上的所有口岸之間都可以輪船通航。
(二)變量
其他交通方式(控制變量)
為了控制其他交通方式對市場整合程度的影響,我們收集了府對之間的驛路距離、電報建設和鐵路通車的數據。基于 CHGIS 提供的明王朝的驛路和驛站的地理信息計算了府對之間的驛路距離,我們根據府對間的驛路距離將其劃分為 5 組(1—5 分別代表距離從近到遠)。電報建設數據來自國民政府交通部鐵道部交通史編纂委員會于 1936 年編纂的《交通史:電政編》和樣本縣的地方志。鐵路通車數據來自《中國鐵路建筑編年簡史(1881—1981)》與《中國鐵道建設史略(1876—1949)》。
其他變量(機制分析)
為了探究不同通航條件以及貿易潛力對市場整合程度的影響,我們收集了不同支流的水文狀況和各府的人口數據。我們基于 SRTM90m 數字高程數據庫的方法計算了各府的地形崎嶇程度,并用其來衡量通航條件。同時,我們基于 CHGIS 定義了各府在所處支流的上下游位置。我們利用府對的上下游位置來衡量同一條支流內部不同河段的通航條件,總體而言下游的通航條件優于上游。基于江天鳳(1992)對于不同支流航道通航條件的記載,我們將支流劃分為兩組。我們從 Cao(2004)中獲得了 1820 年各府人口數據和 1910 年各府的城市化率數據以測度不同規模的府的貿易潛力。
描述性統計
在樣本 A 中我們匯報了各個府層面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包括上等米價格、干流支流地理信息、其他交通方式以及通航條件和貿易潛力等變量;在樣本 B 中我們匯報了府對層面的變量,包括府對是否被同一支流連接、市場整合程度和府對間的驛路通行距離的描述性統計。
四、基準回歸結果和穩健性
(一)基準回歸結果
第(1)列只控制了府對固定效應和年份固定效應;第(2)列控制了府對固定效應和年 — 季節固定效應;第(3)列控制了府對固定效應和年 — 月固定效應;第(4)列在第(3)列的基礎上控制了府與府的線性時間趨勢。回歸結果顯示,允許輪船在長江支流通航后,在同一條支流上的府對之間的市場整合程度有所上升,府對之間糧價之差降低了 4.65%。盡管第(4)列的回歸系數與前三列的回歸系數相比,絕對值降低了 8—10 個百分點,但它仍然在 1% 的水平上顯著為負值,表明在部分控制隨時間變化的府層面的變量,如各個府的經濟、人口狀況等混雜因素后,長江支流允許輪船通航依然顯著提升了被同一條支流連接的府對之間的市場整合程度。從實際數據我們可以看到,與其他府對相比,位于同一條長江支流上的府對的糧價差異下降了 12.53%。也就是說,在嚴格控制各種固定效應的情況下(第(4)列),長江支流輪船航運的開通解釋了上述變化的 37.11%(=4.65/12.53)。
(二)平行趨勢檢驗
本文在識別長江支流通航與上等米市場整合程度之間的因果關系時依賴一條重要假設,即位于同一支流的府對(實驗組)和其他府對(對照組)在《馬關條約》簽訂前的市場整合程度的時間趨勢一致。為了進行平行趨勢檢驗,我們估計了如下回歸方程,并將 β 的估計值及其置信區間展示在圖中。如圖所示,《馬關條約》簽訂前(虛線左側),β 的估計值均在 0 附近波動,且并不顯著;《馬關條約》簽訂后(虛線右側),β 的估計值從 0 左右逐漸變為顯著的負值,表明在《馬關條約》簽訂前,實驗組和對照組之間的市場整合程度的時間趨勢一致。
(三)穩健性檢驗
為了排除混雜因素的影響,我們進行了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包括匹配更可比的對照組、控制其他類型的貿易成本、更換對照組、更換市場整合的度量、更換輪船通航的度量、安慰劑檢驗和排除通商口岸的影響。
粗化精確匹配
在基準回歸中,我們的樣本在地理上囊括了長江中下游有糧價數據的五個省的府。盡管該樣本選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證其中的府在地理上具有相似的特征,但為了進一步保證對照組府對和實驗組府對的可比性,我們參考 Hao 等(2022),利用府對層面的特征,包括人口、是否為通商口岸、是否在長江干流、是否為地方沖要,進行粗化精確匹配(coarsened exact matching, CEM)。匹配結果表明,對照組和實驗組特征的均值差異并不顯著,表明基準結果中的控制組和實驗組相對可比且并無明顯差異。利用匹配得到的樣本進行回歸,結果表明長江支流允許輪船通航依然顯著提升了被同一條支流連接的府對之間的市場整合程度,證明了我們的結果是穩健的。
控制其他類型的貿易成本
除了輪船航運,其他交通工具運輸成本的變化和除運輸成本以外的貿易成本的變化也會影響各個府之間的市場整合程度。在我們的樣本期內,其他類型的技術變革也在改變貿易成本,為了排除這類混雜因素的影響,我們控制了府對之間運輸成本和信息成本的變化情況,具體而言,控制了驛路、鐵路(運輸成本)和電報(信息成本)三類貿易成本,回歸結果顯示控制其他貿易成本的估計結果與基準結果差異不大,證明了本文結果的穩健性。
更換對照組
在基準結果中,我們將位于同一支流上的府對以外的其他府對作為對照組。為了驗證結果的穩健性,我們將基準回歸中的對照組替換為如下四種:兩個府均不被河流穿過、兩個府均在長江干流、僅有一個府在長江干流、僅有一個府在長江支流,并分別進行了估計。結果顯示,長江支流輪船通航僅對在同一支流的府對產生了影響,對于不在同一支流的府對沒有明顯的溢出效應。
更換因變量的度量
為了加強結論的穩健性,我們從兩個維度分別重新構造了市場整合的度量。第一,參考 Federico(2012)和 Hao 等(2022),以各個府為圓心的一定地理范圍內所有府糧價的變異系數來構造反映府級市場整合程度的變量,結果表明長江支流允許輪船通航均能夠顯著降低特定地理范圍內府的糧價的變異系數,即能夠提升市場整合程度。第二,利用上等米的月度最高價格和最低價格來分別構造衡量市場整合程度的變量,重新估計回歸方程,結果顯示回歸系數均顯著為負,且系數大小與基準結果差異不大,表明我們估計結果是穩健的。
更換自變量的度量
基準結果的實驗組為位于長江同一支流上的府對,然而輪船技術沖擊有可能間接使對照組府對樣本受益,因此,我們將 Treat 連續化為兩府之間的支流距離,并重新進行了估計,結果表明府對之間的支流距離越遠,市場整合的提高程度越強,與我們的預期一致。此外,我們考慮長江下游更小的支流,將被這兩條河流連接的府對也作為實驗組,重新估計方程,結果顯示核心變量的回歸系數與基準結果相近。
安慰劑檢驗
為了加強結論的說服力,我們做了兩類安慰劑檢驗。首先,利用同時期黃河流域的糧價數據來檢驗允許輪船通航的政策是否降低了黃河同一支流上府對的市場整合程度,結果表明被黃河同一支流連通的府對之間的糧價差異并沒有顯著變化,表明我們的基準估計結果是穩健的。其次,將輪船通航這一變量隨機分配給各個府對,重復 500 次,結果顯示通過隨機過程得到的系數均分布在 0 左右,而基準回歸得到的系數遠在隨機過程得到的系數的分布之外,表明我們的結果并不是由市場整合程度和輪船通航這兩個變量中的某種共同的隨機趨勢主導的。
排除通商口岸的影響
樣本期內各府開埠通商可能會給市場整合帶來動態影響,為了進一步驗證結果的穩健性,我們從樣本中刪除了通商口岸以及鄰近通商口岸的府,并重新估計了方程,結果表明長江支流允許輪船通航依然顯著提升了被同一條支流連接的府對之間的市場整合程度,證明了我們主要結論的穩健性。
五、機制和異質性
前文結果表明,允許輪船在長江支流通航后,位于同一支流上的府對之間的市場整合程度得到顯著提高。為了進一步驗證支流的輪船航運是市場整合程度提高的直接原因,我們利用支流或河段的通航條件和貿易規模進行了兩類檢驗。第一,支流的航運條件決定了輪船能否行駛以及可通行的輪船數量,通航條件較好的支流或河段上的府對間市場整合程度提升更明顯。第二,運輸距離更遠、糧食貿易量更大的府對之間輪船運輸更具成本優勢,允許輪船通航對這類府對的市場整合程度的影響更大。
(一)通航條件
我們進一步檢驗支流或河段的航運條件在長江支流內河航運提高市場整合程度的過程中發揮的作用。首先,通過估計回歸方程檢驗允許輪船通航對樣本中包含的五條支流(烏江、沅江、資江、湘江、漢水)上的府對的市場整合程度的影響,結果顯示除了烏江,允許輪船通航后,位于其他支流的府對的糧價差異均顯著下降了,結果符合前文所述史料對于各個支流通航狀況的記載。其次,把不同支流按照通航條件分為兩類,結果顯示允許輪船通航使通航條件較好的支流上府對的糧價差異平均下降了 8.75%,是基準回歸結果的兩倍,表明輪船航運只對具備通航條件的長江支流起到了促進市場整合的作用。
除了研究不同支流的通航條件,同一支流內部不同河段的通航條件也不盡相同,一般而言,支流下游比支流上游更適合通航,結果顯示允許輪船通航使得支流下游府對的糧價差異平均多下降了 5.85%。最后,我們把各府分為崎嶇度高(崎嶇度高于中位數)和崎嶇度低(崎嶇度低于中位數)的府,考察輪船對市場整合影響是否異質于崎嶇度,結果表明對于地形不崎嶇的府對,回歸系數高于基準回歸結果的兩倍以上。
上述結果表明,通航條件的好壞是支流航運開放帶來的市場整合程度提升效果大小的決定因素,這為內河輪船航運是市場整合程度提升的重要渠道提供了證據,也說明在這一時期航運技術條件下,地理因素限制了輪船航運的輻射范圍。
(二)規模經濟
地區間的運輸距離和貿易潛力能夠決定輪船航運的市場需求和發展空間,由于輪船有較高的固定資本投資,經營者只有在距離遠、貿易潛力大的地區之間經營輪船運輸業務才有利可圖。在此部分,我們檢驗府對間的運輸距離和貿易潛力在長江支流輪船航運提高市場整合程度的過程中發揮的作用。首先,檢驗輪船通航對不同運輸距離的府對的市場整合程度的影響,結果表明當府對間距離高于其中位數時,允許輪船通航能夠顯著降低府對的糧價差異,表明允許輪船通航帶來的市場整合程度的提高主要來自遠距離運輸,證明輪船與木船相比,其成本優勢隨著貿易距離的增加而逐步放大。
其次,檢驗貿易潛力在長江支流輪船航運提高市場整合程度的過程中發揮的作用,我們采用了三種方式衡量府對之間的貿易潛力:第一,利用 1820 年各府人口來衡量各個府的總需求;第二,利用 1910 年各府城市化率度量各府的專業化分工模式;第三,利用水稻種植適宜度來衡量各個府的分工模式。回歸結果顯示,長江支流輪船航運的開通對于府對糧價差異的影響與糧食貿易量有正相關關系,糧食貿易量較大的府對的糧價差異受長江支流輪船航運的影響更大。
六、結論
輪船作為新式現代交通工具的應用提升了國內市場的整合程度。輪船航運規模的不斷擴大伴隨著晚清被迫對外開放的進程,技術采用和開放帶來的制度變革交織在一起,而本文利用一次兩者不交織的自然沖擊識別了技術的影響。實證結果表明,長江支流輪船航運的開通使得在同一條支流上的府對之間的市場整合程度有所提升。
進一步的機制分析表明:第一,輪船航運只對具備通航條件的長江支流起到了促進市場整合的作用,這一方面進一步證明了相對于其他地區,長江支流地區市場整合的改進是來自航運技術引進帶來的貿易成本下降;另一方面也說明在這一時期航運技術條件下,地理因素限制了輪船航運的輻射范圍。第二,長江支流輪船航運的開通對于運輸距離和貿易規模較大的府對影響更大,這表明輪船技術的應用存在固定成本和規模經濟,只有兩地之間的貿易規模足夠大,輪船的應用才是有利可圖的,才能夠促進貿易擴大和市場整合。
“火車一響,黃金萬兩;輪船一鳴,生意全贏。” 然而,對于近代中國而言,技術不是萬能的,其應用是有條件的;市場一體化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受制于制度、地理、市場規模等因素,呈現出曲折發展和時空局限的面貌。從歷史的后見之明來看,晚清國家本來可以做得更多。此外,1895 年長江支流開放輪船航運后,也沒有如當時某些官員預期出現的船工失業導致的社會動蕩,反而是航運企業家創造性地以蒸汽輪船拖帶沙船的方式節省了資本,吸納了廉價勞動力。總的來說,統治精英的保守和短視推遲和限制了現代技術的引進和采用,這是近代史提供給后世的深刻教訓。
制度建設的滯后進一步制約了航運技術進步的市場效益,由于民商法等私營資本投資的制度性保障不足,在允許自由市場準入之后,長江中下游新建的輪船公司以官紳合辦為主,不少民資船只仍然只能掛洋旗獲得保護。此外,財政拮據的地方政府投資于改善航道條件和碼頭設施的激勵和能力不足,這可能造成了長江航運發展的總體滯后和地區不均衡,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本文實證結果所顯示的經濟效應較小。總之,本文雖然發現輪船航運對于市場整合有積極作用,但這一作用可能受限于地方政府的 “掠奪” 之手太多(行政分割)和 “幫助” 之手太少(公共品提供不足)。因此,本文既為今天 “構建國內統一大市場” 戰略的實施提供了有益的歷史鏡鑒,也為進一步的研究提出了新的問題和思路。
郝 煜;王志強;張 喆,北京大學經濟學院,202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