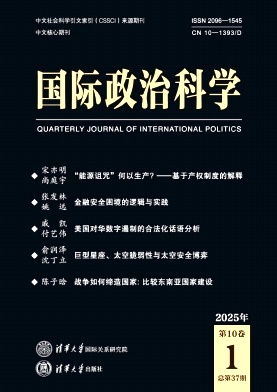國際政治科學雜志投稿格式參考范文:供應鏈安全的定義、測算和國際比較
時間:
供應鏈是指在商品的生產過程中,原材料、產品、資金、信息在生產、流通、消費等各個環節的運轉過程。二戰以后,隨著運輸成本下降和通訊技術發展,企業在全球布局生產,產品內分工取代產品間貿易成為國際貿易主要形式,全球供應鏈由此形成。自 20 世紀 90 年代起,全球供應鏈貿易蓬勃發展,目前占全球貿易比重約 50%。
隨著經濟全球化,各國卷入供應鏈、產業鏈和價值鏈,相互依賴度上升,國家安全概念拓展到經濟領域,供應鏈安全應運而生。特別是近年來,受公共衛生危機、地緣政治沖突等因素影響,全球供應鏈體系的敏感性和脆弱性暴露,供應鏈安全成為跨學科研究問題,但現有研究對其定義、測算方式及各國現狀等基礎問題未有效回應。
本文嘗試提出新框架:首先,討論供應鏈安全的定義,提出內向安全、外向安全和系統安全三個維度;其次,聚焦供應鏈安全面臨的客觀威脅,提出測算框架;最后,使用經合組織貿易增加值數據庫、聯合國大會投票數據,對 1995 - 2020 年間主要國家制造業供應鏈安全水平及其變化趨勢進行測算比較 。
一、文獻綜述
(一)供應鏈安全的概念提出及演變
供應鏈安全的概念從提出至今只有二十年左右的時間,含義卻發生了較大變化。2001 年 “9・11” 恐怖襲擊后,美國政策界和學術界開始關注,當時討論主要局限于物流領域。奧巴馬政府時期,將保障全球供應鏈安全提到國家戰略高度,但仍聚焦企業層面和傳統風險。2016 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后,供應鏈安全含義發生深刻變化,被政治化利用。拜登政府執政后,在供應鏈安全議題上延續特朗普時代模式,將供應鏈與意識形態掛鉤。近年來,受新冠疫情、俄烏沖突等影響,供應鏈安全問題受到眾多國家高度關注,保障供應鏈安全已成為各國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供應鏈安全的定義
“安全” 在學界存在廣泛爭論,供應鏈安全屬于非傳統安全,是安全化的產物。不同學科對供應鏈安全定義有明顯差異,經濟學學者從生產角度強調 “供應的安全”;管理學學者從企業管理角度強調 “鏈的安全”;政治學學者從國家安全角度強調 “關系的安全”。由于定義不一致,阻礙了學科間交流,給研究和政策討論帶來困擾。
(三)供應鏈安全的測算
當前學術界對供應鏈安全的研究以定性分析為主,定量研究缺乏從國家層面對供應鏈安全水平的系統測算。相關定量測算研究主要有三類:使用國際貿易數據測算行業和產品層面的供應鏈脆弱性;使用全球投入產出數據測算國家層面的供應鏈影響力和安全度;使用網絡建模分析方法模擬測算供應鏈網絡的韌性和風險傳播機制。缺乏系統測算導致對相關問題討論缺乏客觀標準,催生泛化供應鏈安全的傾向。
二、供應鏈安全的定義
供應鏈安全沒有單一的定義,在不同情境下呈現不同形式。本文認為供應鏈安全本質上是國家安全問題,其產生背景是各國參與全球供應鏈分工時國家安全范疇的拓展。基于此,將供應鏈安全定義為涉及一國在參與全球供應鏈體系中所面臨的內向安全、外向安全和系統安全三個維度。內向安全指一國供應鏈抵御外部沖擊的能力,衡量維度有敏感性和脆弱性,提升路徑包括提高國內供應鏈自主程度和拓展多元化供應鏈網絡。外向安全指一國通過供應鏈對他國施加影響的能力,與結構性權力緊密聯系,提升路徑有提升本國在供應鏈網絡中的中心性和降低其他國家的中心性。系統安全指整個供應鏈系統應對外部沖擊和維持內部穩定的能力,包含應對外部沖擊能力和維持內部穩定的能力兩個方面。這三個維度既各自獨立又相互作用影響,在政策實踐和學術研究中需關注其差異。
三、供應鏈安全的測算框架
(一)影響因素與數據來源
影響一國供應鏈安全水平的因素主要有經濟因素、政治因素、行業因素。經濟因素是基礎性因素,供應鏈本質是全球化生產分工,國家間中間品貿易往來構成供應鏈安全基礎,本文使用經合組織貿易增加值數據庫構造相互依賴網絡測算基準情形下的供應鏈安全水平。政治因素是決定性因素,只考慮經濟因素難以解釋全球政治格局演變對供應鏈安全的影響,本文基于全球中間品貿易網絡模型,增加兩國國際政治關系權重構造納入政治因素后的相互依賴網絡,國際政治關系指標使用聯合國大會投票數據測算。行業因素同樣影響供應鏈安全,本文在考慮經濟和政治因素測算方式基礎上,分別計算各國在 17 個制造業行業內的供應鏈安全水平。
(二)測算方法
內向安全度的測算:參考相關研究,使用中間品進口(出口)的依賴度作為敏感性測度指標,進口(出口)的集中度作為脆弱性測度指標構造測算方法。先給出純經濟因素下的測算方式,再進一步給出考慮政治和行業因素的測算方式。
外向安全度的測算:參考相關研究,將各國中間品貿易的有向加權網絡中的節點度中心性作為影響力測度指標構造測算方法。同樣先給出純經濟因素下的測算方式,再引入政治和行業因素。
系統安全度的測算:參考相關研究,使用復雜網絡分析方法,模擬供應鏈受到的不同強度沖擊,測算沖擊給供應鏈網絡帶來的性能損失程度構造測算方法。也是先給出純經濟因素下的測算方式,再引入政治和行業因素。
四、供應鏈安全的國際比較
(一)純經濟因素的供應鏈安全
計算 2020 年全球人口超 1000 萬人的 48 個主要國家制造業的內向、外向安全水平,發現只考慮經濟因素時,中國供應鏈安全水平最高;各國供應鏈安全水平分化明顯,中國、美國、德國是供應鏈安全水平最高的三個國家;內向安全和外向安全數值高度正相關。對中、美、德三國 1995 - 2020 年供應鏈安全水平演變測算比較,發現全球供應鏈安全格局發生深刻變化,中國重要性大幅上升,美國相對優勢下降,德國保持穩定。測算 1995 - 2020 年全球制造業供應鏈系統安全水平,發現其經歷了先降低、再上升、后下降三個階段。
(二)納入政治因素的供應鏈安全
考察國際關系因素的影響:使用聯合國大會投票數據測算各國投票理想點,將國家之間理想點距離作為雙邊政治關系代理變量,重新測算并比較各國供應鏈安全水平。結果顯示加入政治因素后,美國取代中國成為全球供應鏈安全水平最高的國家,德國供應鏈內向安全度明顯提升,美、中、德仍是對全球供應鏈安全產生重要影響的關鍵國家。
模擬聯盟因素的影響:聯盟因素對供應鏈安全的影響體現在改善本國供應鏈內向安全水平和提升聯盟國家供應鏈外向安全水平。模擬測算中、美加入不同聯盟的情形,發現美國加入現有聯盟對提升內向安全水平無明顯效果,但中美結成同盟可顯著提升雙方供應鏈安全水平;中國加強同日本、韓國的供應鏈合作對提升自身供應鏈安全水平效果明顯。
(三)不同行業的供應鏈安全
測算比較中、美兩國 2020 年在 17 個制造業行業內的供應鏈安全水平,發現美國在醫藥制造業等行業供應鏈安全水平顯著高于中國,中國則在紡織品和服裝制造業等行業具有較高供應鏈安全水平。測算不同行業 2020 年全球供應鏈系統安全水平,發現其他機械制造業等行業系統安全度水平最高,醫藥制造業等行業系統安全度處于較低水平。
五、總結
近年來,受多種因素影響,供應鏈安全成為重大課題。不同學科學者對供應鏈安全概念界定不一致,缺乏國家層面的系統測算。本文從國家安全視角構建新框架,定義供應鏈安全的三個維度,提出測算框架并對主要國家制造業供應鏈安全水平進行測算比較。研究發現,只考慮經濟因素時,中、美、德供應鏈安全水平最高,全球供應鏈安全體系呈現 “東升西降” 格局;加入國際關系因素后,美國成為全球供應鏈最安全的國家;模擬聯盟因素影響后,中美兩國供應鏈互補性極強,維護好中美關系對兩國供應鏈安全目標實現至關重要。
郎 昆;趙可金,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202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