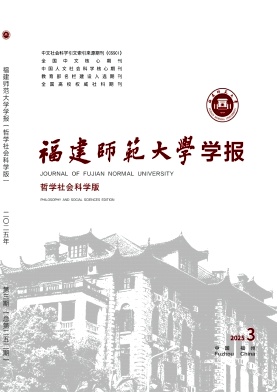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雜志投稿格式參考范文:《明實錄》對俞大猷的形象塑造及其意涵
時間:
俞大猷 (1503—1579),字志輔,號虛江,福建泉州衛前所籍,①謚號武襄。他戎馬一生 “四為參戎、七為總戎…… 一入坐府、一督京營”,②是明代中后期著名的將領。俞氏在抗倭戰爭中取得彪炳史冊的功績,成為民族英雄。正因為他在歷史上有著巨大的影響,學界歷來重視對其人其事的研究。③這些論著一方面大大豐富了我們對俞大猷及其相關歷史的認識和理解,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相關研究存在的某些問題。其中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大多數論著參考、引用《明實錄》中的相關史料,卻很少專門研究實錄中記載俞大猷事跡的史料,導致相關研究缺失明代當朝國史的視角。有鑒于此,本文擬以實錄中俞大猷的相關記載為主要分析文本,結合行狀、墓志銘、文集、民間私史、正史、方志等其他不同性質的文獻,考察《明實錄》對俞大猷事跡的記載情況,探討其對俞大猷形象的塑造及其背后的意涵,為相關研究提供明代當朝國史的認識維度和史料支撐。
一、《明實錄》對俞大猷事跡的記載
俞大猷出生于弘治十六年 (1503) 六月,嘉靖時期開始登上明代國家的歷史舞臺,卒于萬歷七年 (1579) 八月,影響延及后世。筆者從實錄文本中輯錄出有關俞氏的史料約 93 條,其中《明世宗實錄》67 條、《明穆宗實錄》15 條、《明神宗實錄》10 條、《明熹宗實錄》1 條。這些史料大致可以分為兩類:
一是較為集中地記載俞大猷生平事跡的傳記。這則傳記較為簡略,只有 115 字,簡述了俞氏的基本履歷,包括姓名、籍貫、求學和武科舉經歷、仕宦、辭官,卒世。傳記的重點在于評論,字數達 46 個,即 “大猷為人廉而好施,能折節下士,至剔歷東南大小百十余戰,所向無不剿滅,而況機持重,不期目睫功,有古大將風云”。它體現著明代官方對俞氏一生功業的肯定。
二是遵照編年體裁分散記載俞大猷某一事跡的史料。盡管它們散亂分立,但是指涉同一對象 —— 俞大猷,可以聯結成一個統一的文本。它們主要記載以下方面的內容:
其一,記載俞大猷官階、職任的遷轉。嘉靖二十七年八月,南贛巡撫都御史龔輝、福建巡按御史金城的奏章,提到 “武平、永定等處乃守備俞大猷信地”,這也是俞氏在實錄中的首次記載,彼時他任汀漳守備。嘉靖二十九年三月,經提督兩廣右侍郎歐陽必進的薦舉,俞氏從欽州守備、署都指揮使遷轉為瓊崖參將。嘉靖三十一年七月,他由瓊崖參將、署都指揮僉事調任溫臺寧紹等處參將。嘉靖三十五年三月,他又升任浙直鎮守總兵官。隆慶五年十一月,明朝廷 “命原任兩廣總兵、右都督俞大猷僉書南京右軍都督府事”。隆慶六年閏二月,他又調任總兵官,鎮守福建并浙江金溫等處。萬歷二年四月,明朝廷恢復俞大猷 “署都督僉事、后軍都督府僉書管事”。萬歷三年二月,他奉命督管京軍兵車營的操練。萬歷四年十二月,他又升署職一級。據初步統計,記載俞大猷官階、職任遷轉的實錄史料約計 21 條,這不包括記載戰功而升授官階、職任的史料,茲不再枚舉。
其二,記載俞大猷平定南方內亂的功業。嘉靖二十九年七月,嘉靖皇帝嘉獎官員時,記敘了俞氏平定 “廣東瓊州府五指諸山黎賊那燕等”。嘉靖四十一年十月,俞氏平定 “廣賊張璉”、剿平 “江西流賊”。隆慶元年五月,俞氏 “擒斬廣東賊首王西橋等”。隆慶二年四月,巡按廣東御史王同道在奏疏中論及俞氏參加 “廣東官兵剿英德等處山賊”,取得 “斬首一千四百九十三級” 的功績。隆慶三年八月,明朝廷 “錄平閩廣巨寇曾一本功”,俞氏 “與賊遇于柘林澳,三戰皆捷”。隆慶五年五月,明朝廷 “敘廣西古田平寇功”,俞氏又名列其中。據初步統計,實錄中此類史料約計 11 條,恕不逐條羅列。
其三,記載俞大猷在抗倭戰爭中的顯赫功績。嘉靖三十二年四月,浙江倭寇五百余人劫掠臨山衛、松楊等地,遭到知縣羅拱宸督促的處州明軍抵御,于是倭寇揚帆泛海而去。俞氏率領舟師追擊,取得 “斬首六十九級” 的功績。這是實錄首次記載俞氏的抗倭功績。嘉靖三十四年五月,俞氏參加王江涇大破倭寇的軍事行動,“諸軍共擒斬首功凡一千九百八十人有奇,溺水及走死者甚眾。余賊不及數百,奔歸柘林”,此役被實錄高度贊揚為 “自有倭患來,東南用兵,未有得志者,此其第一切云”。嘉靖四十二年四月,俞氏與戚繼光、劉顯在平海衛大破倭寇,“斬首二千二百余級,火焚刃傷及墮崖溺水死者無算”,解救被倭寇擄掠的百姓三千余人,繳獲被倭寇搶奪的衛所官印 15 顆,至此福州以南的倭寇都被平定。嘉靖四十三年六月,廣東明軍在惠州海豐縣大破倭寇,“賊遂大潰,擒斬千二百余人,各哨軍前后所得零賊又一千余人。于是,余倭無幾,不復能軍,散遁入山藪,各兵乃分道搜之”,俞氏參與其中。據初步統計,記載俞氏抗倭功績的實錄史料約計 31 條,茲不贅述。從數量上講,記載俞氏抗倭功績的史料最多,為實錄記載的重點內容。
其四,記載俞大猷的 “失事罪”。嘉靖三十二年八月,巡按御史趙炳然上疏究劾倭寇劫掠浙江期間官員們的罪責,俞氏被罰 “奪俸”,令其戴罪剿賊。這是實錄第一次記載俞氏的負面性。嘉靖三十三年三月,俞氏圍剿普陀山倭寇失利,“我軍半登,賊突出乘之,殺武舉火斌等三百余人”。嘉靖三十七年七月,明朝廷以 “浙江嶺港海寇未平” 為由,褫奪俞氏職級,并責令限期剿平,否則逮捕到京師問罪。隆慶二年七月,撫按奏報廣東曾一本劫掠省城,在赤灣等處擊敗官軍,聽調知縣劉師顏遇害。明朝廷據此追究俞氏等地方武將的罪責,暫停其俸祿,令其立功贖罪。隆慶五年七月,巡按廣西御史李良臣彈劾俞氏 “奸貪不法”,隆慶皇帝懲罰俞氏 “回籍聽用”。萬歷元年九月,因為福建海賊犯閭峽澳等處,俞氏被 “革任閑住”,戴罪立功。據初步統計,實錄中此類史料約計 21 條,難以逐一列舉。
其五,記載俞大猷其他方面的事宜。評論其才能,如嘉靖二十八年四月兩廣提督都御史歐陽必進等人稱贊俞氏 “諳習水軍,智勇素著”。嘉靖三十四年五月,兵部尚書楊博上奏御倭方略,建議讓俞氏 “專督水戰”。隆慶元年八月,兵部否定給事中吳時來調俞氏北上練兵的建議,認為俞氏的才能更適合留在南方,而不宜北調塞上,“往者常一試于北,不效”。隆慶二年九月,總督兩廣軍務侍郎張翰和巡撫廣東都御史熊桴在一份報告中皆認為 “俞大猷長于水戰”。萬歷五年正月,兵部在回復巡視京營兵科左給事中林景旸等人奏疏中,稱贊 “短兵諸法,惟都督俞大猷獨得其傳”。萬歷十九年九月、萬歷四十年閏十一月,官員們在奏疏中皆視俞氏為武將的楷模。記載其抵御韃靼蒙古的功績,嘉靖三十九年七月,大同總兵劉漢、巡撫李文進與俞氏共謀襲擊韃靼蒙古的板升城,取得大捷。奏請為其重新贈謚,天啟元年十二月大學士葉向高認為俞大猷等人的謚號 “公論雖符,謚典尚靳”,最終天啟皇帝同意 “都與他謚,稱朕憫念勞臣至意”。
可見,《明實錄》通過記載俞大猷的生平事跡、時人的評論,在當朝國史中塑造出體現明代官方意志的歷史人物形象。
二、《明實錄》塑造的俞大猷形象與特點
前文梳理和分析《明實錄》中記載俞大猷事跡的相關史料,可以看出實錄對俞大猷形象進行了塑造。那么,實錄塑造出俞大猷什么樣的形象呢?
實錄塑造出的俞大猷形象,乃是遷轉多地而奔波勞苦、在平定南方內亂和抗倭戰爭中功績顯赫、多次獲罪被罰的武將形象。一是遷轉多地而奔波勞苦的形象。根據實錄的記載,可知俞氏在福建、廣東、浙江、南直隸、山西、廣西等多地任職,南疆海域和北疆邊塞都留下其征戰的身影。二是功績顯赫的形象。據初步統計,實錄大約有 40 余條史料記載俞氏在內外戰爭中取得的勝利,盡管存在少量的重復記載 (即不同史料記載同一次勝利),但是數量依然相當可觀。特別是實錄花費很多篇幅記載其在抗倭戰爭的功績,重點塑造出其抗倭名將的形象。三是多次獲罪被罰的形象。如前文所述,實錄中有大約 20 余條史料記載俞氏獲罪被罰,雖然也存在少量的重復記載,可是依然反映出俞氏宦海的艱難曲折。
《明實錄》塑造的俞大猷形象,具有怎樣的特點呢?結合行狀、墓志銘、文集、民間私史、正史、方志等其他性質文獻的記載,筆者認為實錄塑造的俞大猷形象至少具有以下特點:
其一,凸顯 “武” 的面相,卻沒有著墨其 “文” 的面相。然而,這并不等于說俞氏的個人歷史沒有 “文” 的面相。相反,在其他文獻中俞氏既是一位沖鋒陷陣、功績顯赫的武將,也是一位文儒。這至少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俞氏早年的儒學經歷。據文獻記載,俞氏曾向王宣、林福、趙本等人學《易》,又是郡邑庠生 (即地方儒學的生員),實乃一位真正的文人儒士。二是俞氏為邊疆的長治久安提出了自己的邊防思想。對此,有文獻概括云:“公儒者也,于安南、瓊黎、東倭、北虜、三苗、五嶺,皆有善后之策,可百世因之…… 所謂立馬讀《易》者,信載!” 盡管 “可百世因之” 云云,不免夸張,但是流傳至今的俞氏《正氣堂集》收錄有《上兩廣軍門東堂毛公平安南書》《論處黎長久之策》《防倭議》《兵略對》等書信、奏疏,可見其確有自己的邊防思想。三是俞氏在治理地方的實踐中,也非常重視運用文治的策略。如任職福建金門時,地方 “軍民囂訟難治”,俞氏 “用儒飭治,讀法、賑饑,囂俗為之一變”;又如任職福建武平時,俞氏 “作讀《易》軒,與博士弟子為文會”。可見,無論是早年的儒學經歷,或是邊防思想,還是治理地方的實踐,它們都表現出俞氏個人歷史中 “文” 和 “儒” 的面相。
其二,重點體現抗倭戰爭和平定南方內亂,而較為忽略平定安南入侵、抵御韃靼蒙古。但是,這并不代表俞氏在平定安南入侵、抵御韃靼蒙古兩個方面沒有功績或者功績不大。事實上,它們是嘉靖時期重要的軍事勝利,也是俞氏生平中非常顯赫的功績。首先,評述俞氏平定安南入侵的功績。當時安南逃亡之臣范子儀想要篡奪幼主莫宏瀷的王位。于是,范子儀以匡復為號召,擁立莫正中,擁兵三萬,時常入侵廣東的欽州、廉州等地。俞氏臨危受命,前往抗敵。到達前線后,俞氏對敵軍進行招降安撫,敵軍一萬余人自行解散。范子儀不甘心失敗,逃往欽州。俞氏率軍追擊,“前后兩戰,俘斬千余” 擊敗敵軍。范子儀敗退安南,俞氏率軍追至海東云屯。后來范子儀被莫宏瀷抓捕斬首,其首級被送至明軍。至此,安南范子儀入侵之亂被平定。這也是俞氏生平中非常顯赫的功績,時人有 “匡夷尊夏,功足多焉” 的贊譽。其次,評論俞氏抵御韃靼蒙古的功績。前文已述,實錄雖然有記載嘉靖三十九年七月俞氏參與謀劃襲擊韃靼蒙古板升城的大捷,但是在隆慶元年八月的記載中,實錄借兵部的說辭 “大猷才宜于南,往者常一試于北,不效” 否定俞氏在北疆邊塞的功績。關于俞氏此次抵御韃靼蒙古的功績,行狀、正史等文獻有著較為詳細的記載。結合各種文獻,可知俞氏此次的功績主要有三:一是制造兵車,“獨木為輪,用人推挽,翼以步卒,佐以游騎”,后來巡撫李文進據此奏請明朝廷設置兵車營。史書中 “京營有兵車,自此始也” 云云,可見其影響之大。二是在安銀堡大敗韃靼蒙古軍,“以所練兵車百輛、步騎三千縱擊虜萬計,追奔逐北數百里”。有研究者認為這是明代歷史明確記載的唯一一次車兵作戰的勝利。三是參與襲擊板升城的大捷,即實錄所載嘉靖三十九年七月的史事。以此觀之,俞氏在大同抵御韃靼蒙古的功績并非像實錄所載那樣平淡無奇、無足輕重,更非 “不效” 二字所能掩蓋、抹殺。
其三,凸顯其在各地征戰,卻沒有涉及當地民眾對俞氏的態度。當我們將視線轉移到行狀、墓志銘、文集、民間私史、正史、方志等文獻時,不難發現各地民眾對俞氏的態度。總體而言,俞氏深受民眾愛戴。如當俞氏調離金門時,當地民眾流淚挽留,建立生祠奉祀,曾向他學習《易》的秀士追隨而來,向他學習劍法的丁壯 “給役其家”,不肯離去。又如當俞氏調離新興、恩平時,兩邑民眾強行挽留,“新、恩人遮道留者數千,父老皓發皤髯奪公肩輿之以歸,數日不得發”,以至于俞氏只得半夜獨自騎馬從小路方才離去。再如俞氏在瓊州時,黎民爭先拿出牛酒慰勞,將他的畫像放在佛寺中奉祀,并稱呼為俞佛。另如,在浙江抗倭時,俞氏軍紀嚴明、秋毫無犯,“士民弦誦耕織如故,浙東西底寧”,民眾非常感念他的恩德,請留下其衣冠數十襲,建立生祠奉祀。清修正史《明史》、乾隆《晉江縣志》也載有 “武平、崖州、饒平皆為祠祀” 云云。在當時,建立生祠,對還活著的人立祠奉祀,是民眾表達內心感戴和欽敬之意的重要形式。當然,事情的另一面是福建興化府民眾對俞氏卻有著怨恨之情。原來,俞氏在興化府征戰時,沒有安營扎寨的竹木,于是他下令 “發殘屋為營”;又因興化、泉州二府沒有糧食可以供養征戰的軍士,而明朝廷運輸的軍糧也多日未到,于是他下令軍士就地 “采麥食之”。換言之,俞氏已有縱容軍士強征或搶掠民財的行徑。因此,“興化人多怨公”。俞氏自己也說:“吾為將三十年,不擾民一草一木,今乃種孽于父母之邦耶?” 這一記載出自以歌頌俞氏功績為主要撰述意圖的《都督同知俞公大猷功行紀》,應不是厚誣,當屬事實。盡管此類記載應為少數 (僅見此例),卻也反映出當地民眾對俞氏的別樣態度。
此外,實錄塑造的俞大猷形象并非單向度的,而是功績與過失共存。實錄塑造出俞氏遷轉多地而奔波勞苦、在平定南方內亂和抗倭戰爭中功績顯赫的形象,同時也塑造出俞氏多次獲罪被罰的形象。與實錄塑造的俞氏形象不同,行狀、墓志銘、方志乃至正史,它們都主要記載俞氏的功績,較少提及過失,故而塑造出單向度的歷史人物形象。相比之下,實錄塑造的多向度俞氏形象更顯嚴肅性、客觀性、可信性。因為世上本不存在只有功績卻沒有過失的人,俞大猷也不能例外。總體而言,《明實錄》塑造的俞大猷形象是正面的,這表明明代官方對俞氏一生功績的肯定。
三、《明實錄》塑造俞大猷形象的背后意涵
結合行狀、墓志銘、文集、民間私史、正史、方志等文獻進行綜合辨析,可知實錄塑造的俞大猷形象基本符合歷史事實。因此,實錄之所以如此塑造俞氏形象,主要是由歷史事實決定的。但是,這并不是說歷史人物形象的塑造就是純粹的客觀行為。相反,史官在塑造俞氏形象的過程中有歷史書寫的行為,這蘊含著豐富的歷史意涵。
實錄中俞大猷是功績與過失并存的形象,然而它卻折射出史官乃至明代官方對俞氏一生功績的肯定。大書特書俞氏在平定南方內亂和抗倭戰爭的功績,自然是史官乃至明代官方對其功績的肯定。同時,實錄對俞氏過失的同情、回護、辯解,也是對其功績進行的肯定的特殊表現。前文已述,實錄中有 21 條史料記載俞氏 “失事罪”。其中,6 條史料中有 “諸臣罪狀”“官軍御倭失事狀”“諸臣功罪” 等字詞,9 條史料記載俞氏只是獲罪被罰者之一,它們共同表明作戰失利應是當地文官、武將共同的罪責,并非只針對俞氏一人。可見,實錄在字里行間已降低俞氏的負面性。另外,實錄也有明確為俞氏獲罪被罰進行辯解,如嘉靖三十八年三月,俞氏因總督浙直福建都御史胡宗憲彈劾而被逮捕到京師治罪,實錄就辯解道:“柯梅倭之出海,宗憲實陰縱之,故不督諸將要擊。及倭既出舟山,即駕帆南泛,泊于浯嶼,焚掠居民…… 故諉罪大猷,以自掩飾如此。”
實錄中俞大猷形象的塑造遮蔽了其 “文” 的面相,這折射出明代彼時的文武關系。俞氏是武將,其形象塑造凸顯其 “武” 的面相,本無可厚非。可是,俞氏《正氣堂集》中的多份奏疏,實錄中卻沒有任何的收錄,這與實錄塑造文官形象時收錄其奏疏相比,真可謂是 “文武有別”。這種明顯的區別對待,表明在實錄的編撰過程中武將多時是 “失語” 的群體,他們的歷史生命是由以史官為代表的文官來決定。在歷史話語權的掌控上,明代的文武關系十分不對等。又,據研究明代中后期 “文人尚武與武將尚文風氣” 形成并勃興,也即武將 “好文” 成為一時風尚。事實上,多數武將可能只是附庸風雅,沒有多少真正 “文” 的實質。或許正是在這種大背景下,史官帶著固有偏見看待俞氏 “文” 的面相,誤認為那也只是附庸風雅卻無實質的 “虛像”。所以,在嚴肅的當朝國史編修中,他們自然不會正視那些被視為 “虛像” 的武將好文之風。
實錄中俞大猷形象的塑造較為忽略平定安南入侵和抵御韃靼蒙古,這可能與明人掩遏其功績和俺答封貢的現實需求等因素有關。前文已述,俞氏平定安南入侵本是非常重要的功績。然而,明朝廷當時的內閣首輔嚴嵩對此事不悅,“降內批責諸臣防御無狀,今日之功差足掩過”,致使俞氏這次的功績受到掩遏。同樣的,俞氏抵御韃靼蒙古的功績也被明人掩遏,如前文所引,時人在奏疏中多次強調俞氏善于水戰、不宜北調,甚至說俞氏在北疆邊塞任職時沒有成效,皆是明證。又如譚綸曾在信中評價俞氏:“節制精明,公不如綸。信賞必罰,公不如戚。精悍馳騁,公不如劉。然此皆小知,而公則堪大受。” 有研究者指出:“這句話可能也起了潛移默化的影響。調度有方,紀律嚴明,英勇作戰,是衡量一個高級指揮官素質的基本條件。如果這三方面不如他人…… 也不能算是一位出色的將領。” 平心而論,譚綸是當時較為熟悉俞氏的友人,為人正直,他對俞氏的評價即便客觀上起了消極影響也應不是出自惡意,更多的是沒能真正了解俞氏。所以,俞氏另一位好友李杜曾言:“今天下人人知公之所為矣,而猶未知其所以為,則以公特異于今之為將者耳!” 也即李杜認為俞氏被歷史埋沒的原因是不被世人所真正了解。當然這也是俞氏功績被掩遏的重要原因。再者,《明世宗實錄》編修于隆慶元年六月到萬歷五年八月,俞氏抵御韃靼蒙古的事跡便記載于此書。結合相關知識,可知先后主導世宗實錄編修的高拱、張居正也是俺答封貢的倡導者、組織者,同時也是隆慶時期、萬歷初年的重要主政者。維持明朝廷與蒙古之間的和平,自然是當時主政者的意愿。然而,俞氏在嘉靖三十九年七月抵御的蒙古部落正是俺答的韃靼部。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淡化明朝廷與韃靼蒙古之間過往的矛盾沖突自然是最好的選擇。因此,俞氏抵御韃靼蒙古的功績也就不宜大書特寫,相反只能作模糊化處理。
實錄體史書的體例要求、性質訴求、獨特的關注視角是促使史官在塑造俞大猷形象時忽視各地民眾態度的重要原因。實錄體史書是以已故皇帝及其朝政為主要記載對象,因此實錄的內容取舍也是以皇帝為中心,圍繞著皇帝來組織材料,以皇帝的一生活動為線索,將省府州縣等事件按照由上到下、由內到外的次序加以記載。顯然,民眾對于當地文臣武將的態度不太符合實錄內容的采摘標準。因此,史官忽視相關內容的記載也就很好理解了。這也反映出當朝國史和民間私史的關注視角迥異,能夠進入各自記載視野的事件也不一樣。
綜上所述,實錄中俞大猷形象的塑造不只是對個體歷史的簡單記載、被動呈現,它既體現出明代官方的國家意志,也投射出史書編撰時代的各種社會情形,乃是對個體歷史的有意書寫、主動呈現。
四、結語
俞大猷是明代中后期著名的將領,其在《明實錄》中的相關記載具有獨特價值。梳理、分析實錄中記載俞大猷事跡的史料,可以發現實錄塑造出俞氏功績與過失并存的形象。總體而言,實錄塑造的俞氏形象是正面的,這表明明代官方對俞氏一生功績的肯定。
對比行狀、墓志銘、文集、民間私史、正史、方志等文獻,可知實錄塑造的俞氏形象基本符合歷史事實,但是也存在遮蔽其他形象的問題。實錄遮蔽的那些形象,不可一概而論,更不可都將之視為史官的曲筆。當朝國史有著自己的體例要求、性質訴求,故而有著獨特的關注視角,不能也不必無所不包,它凸顯的是歷史人物最主要的特點、裁定其功過是非。以本文的議題而言,俞氏是武將,那么實錄塑造的人物形象理應將重點放在凸顯其武將的特點,裁定其為明朝廷征戰的功績和過失。依此而言,實錄遮蔽俞氏 “文” 的面相、沒有涉及當地民眾對俞氏的態度等,自然無可厚非。不可否認,在俞氏平定安南入侵、抵御韃靼蒙古的功績問題上,實錄似有掩遏其功績的嫌疑。可見,實錄對歷史人物的形象塑造,既是對個體歷史的簡單記載、被動呈現,也是對個體歷史的有意書寫、主動呈現。
目之所及,探討《明實錄》具體歷史人物的形象塑造或歷史書寫,多以皇帝、后妃、文官為主,較少涉及武將。本文是武將形象塑造的個案研究,為相關研究增添一個新的例證,這對于認識和理解實錄中具體歷史人物的形象塑造或歷史書寫應有一定的價值。另外,本文梳理、分析實錄中記載俞大猷事跡的史料,揭示其特性,為相關研究提供明代當朝國史的認識維度和史料支撐,這對于深化俞大猷研究也具有一定的作用。
劉小龍,廣東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202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