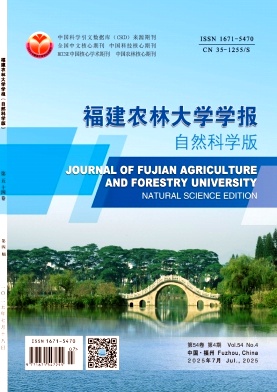福建農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雜志投稿格式參考范文:泉州灣濕地碳庫生態安全評價及其障礙因素研究
時間:
濱海濕地是海洋與陸地交界處的復雜生態系統,具有高效的固碳能力,是重要的碳庫之一,在全球碳循環中起著重要作用,對維持當地生態平衡及區域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通過有效管理濱海濕地,可以提高其固碳等多種生態價值。隨著經濟快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加快,濱海濕地生態系統承受的壓力日益增大。一旦這些生態系統遭到破壞,不僅會導致水土流失和生物多樣性減少,還會嚴重影響其固碳能力,使其從 “碳匯” 變為 “碳源”, 對周圍地區的生態安全造成負面影響。在 “雙碳” 戰略的大背景下,如何有效評價濱海濕地 “碳庫” 的生態安全狀況已成為亟需解決的問題。
近年來,濱海濕地生態安全監測和評價問題備受關注。例如:陸續有學者在構建生態安全評價指標的基礎上,對青島市濕地、海南島濕地、杭州灣濱海濕地、黃河三角洲地區濱海濕地、盤錦濕地、臺灣高美濕地、遼河口濕地等的生態安全狀況進行長期監測并開展相關研究。然而,這些研究大多僅限于某個單獨年份或不連續年份的生態安全評價,忽略了濕地碳儲量供給與人類活動碳排放需求之間的關系。因此,至今尚未形成成熟的濱海濕地碳庫生態安全評價技術。
泉州灣河口濕地是我國亞熱帶河口濕地的典型代表,具有巨大的生態價值。目前,關于其生態安全監測與評價的研究較為稀少。僅有周錚雯等運用層次分析法和加權綜合指數法對泉州灣濕地的生態安全進行了評價。然而,該研究在指標選取上不全面,時間點選取不連續,且無法反映生態安全各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缺乏對障礙因子的分析。本研究以泉州灣濕地為研究對象,采用 DPSIR 模型,通過專家判斷法和熵權法確定指標權重,基于遙感影像、野外實測數據以及官方統計數據,首次綜合評價 2012—2021 年泉州灣濕地 “碳庫” 的生態安全狀況。研究旨在掌握泉州灣濕地及周邊地區長期生態安全情況及演變規律,為促進泉州灣濕地及周邊地區生態環境保護、經濟建設及環境管理之間的協調有序發展提供參考。
1 研究區域概況
泉州灣河口濕地自然保護區是中國重要濕地之一,也是亞熱帶河口灘涂濕地的典型代表,涉及泉州地區的惠安縣、洛江區、豐澤區、晉江市、石獅市。保護區范圍東至秀涂內側與石湖內側連線以內水域,西至晉江大橋,南至蚶江水頭,北至惠安陳壩村,總面積 7045.88hm², 其中:核心區面積 1278.62hm²,占總面積的 18.14%;緩沖區面積 798.92hm²,占總面積的 11.34%;試驗區面積 4968.34hm², 占總面積的 70.51%。地理坐標為:24°47′21″—24°59′50″N,118°37′44″—118°42′46″E。泉州灣河口濕地自然保護區的主要保護對象是灘涂濕地、紅樹林及其自然生態系統,以及中華白海豚 (Sousachinensis)、中華鱘 (Acipensersinensis)、黃嘴白鷺 (Egrettaeulophotes)、黑嘴鷗 (Larussaundersi) 等一系列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和中日、中澳候鳥保護協定的鳥類。
2 材料與方法
2.1 數據收集及處理
收集 2012—2021 年的遙感數據:2012—2015 年的數據采用 Landsat8 衛星測定,空間分辨率為 30m;2016—2021 年的數據采用 Sentinel⁃2 高光譜衛星測定,空間分辨率為 10m。這些數據分別從美國地質調查局官網和歐空局哥白尼數據中心免費下載。使用 ENVI5.3 和 SNAP 軟件對原始影像進行輻射定標、大氣校正、重采樣以及裁剪等預處理。
研究對象僅限于紅樹林生境碳儲量,其空間連續分布及儲量通過遙感因子結合樣地數據反演得到。景觀指數基于土地覆蓋數據,采用 Fragstats4.2 軟件計算得到。文教科研發文數量來源于中國知網 (https://www.cnki.net) 及核心期刊引文索引數據庫 (https://www.webofscience.com); 其余數據均來源于官方公布的 2012—2021 年泉州統計年鑒。
2.2 研究方法
2.2.1 DPSIR 模型
DPSIR 模型最早由歐洲環境署提出,是一種在環境系統中廣泛使用的評價指標體系概念模型。該模型從驅動力、壓力、狀態、影響和響應 5 個相互影響的方面,輔助揭示和剖析人與環境之間的因果關系。DPSIR 模型兼具 DSR (驅動力 — 狀態 — 響應) 和 PSR (狀態 — 影響 — 響應) 的特點,近年來在國內濕地生態系統研究中逐漸受到關注并被廣泛應用。可見,基于該模型評價濕地生態安全是合適的。
模型中的 “驅動力” 包括自然和人為因素,這些因素直接或間接影響濕地生態系統的結構及功能,主要分析自然、經濟、人口和社會等因素;“壓力” 是 “驅動力” 產生的作用,表現為災害、人類活動和污染 3 個方面。“狀態” 在 “壓力” 作用下,直接反映濕地的生態健康狀況,通過二氧化碳排放量和一系列景觀指數進行分析。在 “驅動力”“壓力” 和 “狀態” 的共同作用下,濕地對其本身及周邊地區產生 “影響”, 通過供給服務和水資源兩個角度進行分析。“響應” 一方面與 “影響” 相互作用,通過人為干預提升濕地的正面影響,減少負面影響;另一方面又作用于 “驅動力”, 使 DPSIR 模型形成一個封閉的相互影響的有機整體。“響應” 反映當地政府和社會為維護及改善濕地生態系統狀態而采取的措施,如資金投入和污染治理,即從治理、投入和文化服務等角度進行分析。
2.2.2 指標體系構建
指標體系設計是生態安全評價的基礎。為保證評價結果的準確性,在充分考慮指標選取的適合性、數據的易得性和模型的合理性基礎上,建立了指標體系框架。該框架將評價指標分為 3 個層次:第 1 層為目標層,設定為泉州灣濕地碳庫生態安全值;第 2 層為準則層,包括驅動力、壓力、狀態、影響、響應;第 3 層為指標層。考慮泉州灣濕地生態系統的特點,并參考李楠等對濱海濕地生態安全評價的研究,同時兼顧數據的可獲取性,選取了包括人均 GDP、自然增長率、年均溫度等 32 個指標。由于濕地碳儲量供給與人類活動碳排放需求之間的平衡關系,將單位 GDP 電耗、二氧化碳排放量、固碳 (碳儲量) 納入指標體系。
2.2.3 組合方法
基于主客觀判斷相結合的理念,將專家判斷法與功效系數法、熵權法相結合。
(1) 專家判斷法:為提高權重數值的權威性及減少一致性檢驗的工作,采用分別向 3 名權威專家發放指標權重打分表的方式,獲得專家提供的指標權重后取算術平均值,得到各指標的專家判斷權重值。
(2) 功效系數法:采用功效系數法對計量單位不同的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
2.2.4 評價標準確定
基于泉州灣濕地實際情況,通過借鑒文獻 [9-10], 將該研究區域的生態安全等級分為等間距的 5 個等級,從高到低依次為:優秀、安全、較安全、較危險、危險。
2.2.5 障礙因素診斷模型
為制定泉州灣濕地碳庫生態安全水平提升的策略,有必要評估各項指標的障礙作用,找出阻礙泉州灣濕地碳庫生態安全水平提升的主要因素。參考呂添貴等使用的障礙因素診斷模型,利用在線 SPSS 軟件 (https://www.spssau.com), 選取 2012、2016、2021 年作為典型年份進行研究。
3 結果與分析
3.1 濕地碳儲量變化特征
2012—2021 年,泉州灣濕地碳儲量雖然有波動,但總體呈上升趨勢,僅在 2016、2021 年出現下降。其中 2012 年的碳儲量最低為 168221×10⁶t,2020 年碳儲量最高,為 654463×10⁶t。這與泉州灣河口濕地自然保護區采取的保護紅樹林和增加紅樹林面積等有效措施有關。2021 年碳儲量明顯下降,可能與藍色海灣綜合整治行動有關。2021 年是該行動的第 1 年,初期的清理工作和新種植的紅樹林尚未成熟,可能導致碳儲量短期內下降。
3.2 指標權重確定
依據熵權法和專家判斷法,將兩種方法的評價結果進行算術平均,得到各項指標的權重。通過準則層分析,可知權重占比最大的是驅動力指標,平均權重達到 0.2852, 共有 9 個指標,是指標體系中數量最多的一類。之后依次為壓力指標、狀態指標、響應指標和影響指標。準則層權重高低與其對應的指標數量呈正相關。
專家法權重最高的指標有 5 個:最大日降水量、單位 GDP 電耗、二氧化碳排放量、碳儲量、平均溫度,它們權重均為 0.442。其中,平均溫度和最大日降水量是植物光合作用的重要影響因素,單位 GDP 電耗是實現碳中和的關鍵,二氧化碳排放量、碳儲量是特色指標。權重最低的是文教科研,其值為 0.154。
專家法權重與熵權法權重之間差距最大的是 “第三產業產值占比”。在熵權法中,該指標權重最高,而在專家法中權重較低。可能的原因是第三產業主要提供服務,其單位產值消耗的能源相對較少,而制造業、建筑業和交通運輸業則需要大量能源,因此,專家判斷權重值較低。盡管近年來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有所增加,但其碳排放量相對于第一、第二產業依然有限。這表明專家法通過有效調節指標,盡量與現實情況相接近。而專家法權重與熵權法權重之間差距最小的是地表水資源量,差距僅為 0.0004。這意味著專家的主觀判斷與客觀評價在此項指標上可能較為一致。
平均權重最高的前 5 個項目依次為:第三產業產值占比 (0.0466)、人均耕地面積 (0.0456)、廢氣治理能力 (0.0411)、人均水資源量 (0.0392)、碳儲量 (0.0384), 這 5 個項目變化均對泉州灣濕地生態安全的影響均較大。平均權重最低的 5 個項目依次為:景觀均勻度指標 (0.0187)、文教科研 (0.0194)、垃圾無害化處理率 (0.0217)、景觀優勢度指標 (0.0225)、空氣質量達標率 (0.0252), 這 5 個項目對泉州灣濕地生態安全的影響均較小。
3.3 生態安全評價
通過試驗數據處理,可得 2012—2021 年泉州灣 WESI 及變化趨勢。泉州灣濕地在這 10 年間的生態安全狀態均為較安全 (0.4~0.6)。根據 DPSIR 模型準則層間的相互關系,狀態指標的變化會促使影響指標發生變化,影響指標則激勵響應指標發揮作用,響應指標又促使狀態指標恢復與提高,從而提升驅動力指標。在各因素相互作用下,2021 年驅動力指標及泉州灣濕地生態安全值均達到 10 年間的最高值。生態安全值最低年份為 2012 年,最高年份為 2021 年,2021 年生態安全值比 2020 年高 0.04, 總體呈遞增趨勢,這與泉州灣河口濕地省級自然保護區長期有效的保護措施有關。然而,泉州灣濕地生態安全評價在較安全區間內存在波動,人類對濕地的利用與保護之間的矛盾,以及濕地本身的脆弱性,可能是目前泉州灣濕地生態安全狀況長年波動的主要驅動因素。
對于正相關的準則層:驅動力指標數值呈逐年遞增趨勢,可能原因是泉州相關管理部門通過優化第一、二、三產業占比,降低了泉州灣濕地所承受的生態壓力,促使驅動力指標數值持續提高;狀態指標數值相對不高,其變化規律以 2015 年為分界點,先增加后減少,主要原因是泉州灣地區的碳排放量(負向指標)以 2015 年為分界點,先減少后增加;影響指標數值總體呈上升趨勢但存在波動,上升的原因主要在于碳儲量及漁業產值的逐年增加,而波動原因與泉州灣地區地表水資源量有關。對于負相關指標:壓力指標數值呈逐年遞增趨勢,濕地面積的增加及人均耕地面積減少是壓力指標提升的主要原因;響應指標數值亦呈逐年遞增趨勢,對應指標層各子指標數值均呈現上升趨勢,具體包括污水集中處理率、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環境保護治理投資、空氣質量達標率等。這表明人為和自然的保護措施在過去 10 年內取得了正向效果。
不同時期泉州灣濕地生態安全的主要影響因素各不相同。2018—2020 年生態安全值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人均耕地面積的持續減少,以及污水集中處理率和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等的持續增加;而 2013—2014 年生態安全值下降的主要原因則是人口自然增長率上升和 GDP 增長率下降。這表明,未來泉州灣濕地生態安全保護工作需要與時俱進,不斷調整保護措施,以適應經濟和環境發展變化的需求。
3.4 生態安全障礙度測定
2012、2016、2021 年指標層各因素障礙度從高到低排序(前 5 名),共涉及 12 項指標。
雖各觀察年間障礙因子的變化較大,但可概括為 6 類指標:氣(廢氣治理能力),水(污水集中處理率、人均用水量、人均水資源量、地表水資源量、工業廢水排放量),碳(碳儲量、碳排放量),產業占比(第一產業產值、第三產業產值),土地要素(人均耕地面積)及能耗(單位 GDP 電耗),這些指標均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
2012、2016 年的主要障礙因子較相似,相同的包括:第三產業產值占比、廢氣治理能力、人均水資源量。2012 年以前,泉州灣地區生態安全保護意識較弱,存在犧牲環境發展經濟的現象,對第三產業的發展重視不足,廢水、廢氣(包括二氧化碳排放)的處理不夠到位。2012 年后,經過多年的治理,生態安全狀況逐步改善,主要障礙因子也隨之發生變化,到 2021 年,人均耕地面積成為最關鍵的障礙因子。耕地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在執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政策的背景下,泉州灣地區由于土地供給不足,可能存在退濕還耕的現象。因此,需要加強泉州灣濕地動態監測與安全評價,逐步優化國土利用空間格局,科學劃定濕地和耕地保護紅線,權衡濕地與耕地的比例關系和布局,在保障糧食安全的基礎上,統籌兼顧濕地保護。
與碳相關的障礙因子(碳儲量、碳排放量)在 2012、2016 年均位于前 5,這可能與 “雙碳” 意識的提高以及相關舉措的落實有關。在 2021 年,這兩項障礙因子的障礙度排名分別下降到第 15 和 21 位(并列),它們對泉州灣濕地生態安全水平提升的制約能力已大幅減弱。
4 討論
2012—2021 年泉州灣濕地碳儲量總體呈現逐年遞增趨勢,存在波動變化現象,與路春燕等關于泉州灣紅樹林濕地面積的研究結果基本一致。
泉州灣濕地碳庫生態總體處于較安全狀態,但也存在波動變化。這可能與濕地利用和保護之間的長期博弈及濕地本身的脆弱性有關。近 10 年來,泉州地區城市經濟快速發展,海灣經濟開發強度大,人口和經濟快速增長,以及配套基礎設施建設,導致泉州灣生態系統的某些服務功能逐步退化。為此,泉州市實施了一系列整治和修復泉州灣濕地生態的措施:積極開展宣傳教育,加大科研監測力度,實施紅樹林人工種植,推動違法違規問題整治,開展藍色海灣綜合整治行動等。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利用與保護之間的矛盾。然而,保護舉措常跟不上破壞的步伐,自然環境的不斷變化也可能促使泉州灣生態安全長期處于波動狀態。因此,不斷監測和探討泉州灣濱海濕地生態安全問題將是一項長期的工作。
近年來,人均耕地面積、地表水資源量、單位 GDP 電耗、工業廢水排放量和第一產業產值是制約泉州灣濕地生態安全水平提升的重要因素。針對這 5 個方面進行正向干預,可以最大化提升性價比。具體措施為:加強泉州灣濕地碳庫生態安全情況的實時有效監測,繼續優化三大產業比重,適當發展旅游業等第三產業;根據泉州灣濕地、耕地保護的實際情況,出臺合理的濕地和耕地保護措施;減少電力生產環節中的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的排放,依靠新技術提高發電效率;合理規劃漁業用地和配套設施;加強對互花米草的治理等。通過以上措施,實現發展與保護的統籌兼顧,提升泉州灣濕地碳庫生態安全狀態。
在測算碳儲量和碳排放量時,沒有考慮甲烷等重要的溫室氣體。在指標選擇中,人均 GDP 和 GDP 增長率、人均水資源量和人均用水量存在一定類別重疊,應盡可能選擇區分度明顯的指標,以反映問題的不同側面。對于碳儲量、廢氣治理能力、二氧化碳排放等重要影響指標,僅進行了定性分析,沒有提供其影響能力及閾值。因此,盡管 DPSIR 模型被廣泛應用于濕地生態系統評價,但在指標覆蓋面和評價維度方面仍有進一步優化的空間。
陳 實;陳麗捷;洪 宇;劉金福;闕 翔;李意敏;何東進;趙婧雯,福建農林大學林學院;福建省經緯數字科技有限公司;福建農林大學計算機與信息學院;福建省高校生態與資源統計重點實驗室;自然資源部東南生態脆弱區監測修復工程技術創新中心;泉州灣河口濕地自然保護區發展中心,202405